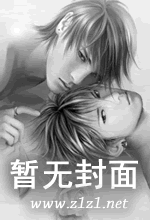凤难为-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帝倒是有些奇怪——这个儿子胆子就和老鼠似的,素来都是能躲就躲,上回为着裕王妃的事来了一趟已经算是难得,这回居然又来了。隔了一层珠帘,他沉吟片刻才开口问道:“今日怎么来了?”
裕王已经做了好些准备,这时候顶着皇帝老爹针刺一眼的目光还是觉得有些气虚。他想了想李清漪的话和宁安公主,终于还是咬牙应声道:“儿臣今日是想问一问宁安的婚事。”
听到这话,皇帝倒是越发奇怪起来了,他瞥了眼站在那里的裕王,终于还是道:“先坐下吧。”
边上早有伶俐的太监,搬了绣墩上来,扶着裕王坐下——皇帝跟前还有位置,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裕王一贯都不得宠,这时候免不了有些尴尬,但还是恭敬的坐了下来。
等他坐下了,皇帝这才恍若无意的问道:“怎么,宁安和你说什么了?”
裕王心知皇帝这是怀疑自己窥探内宫,心中暗叹,口上却只作不知的道:“宁安是女孩家,向来面薄又不能轻易出宫,哪里会和儿臣说这个?只是儿臣到底是做哥哥的,眼见着宁安这般年纪,心里自然也是是念着她的婚事的。少不了要来问父皇一句。”
皇帝握着拂尘的手紧了紧,若有所思:“你这个做哥哥的倒是有心。”似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又叹气,“如今想来,当年永淳的事,确实是朕这个做哥哥的不小心。”
别看皇帝对后宫、子女都是一贯的冷淡,但他对着父母、姐妹却又格外的有感情。当年为着认亲爹和亲妈,大礼仪闹得天翻地覆,直到如今都犹有余声。永淳公主乃是皇帝的同母幼妹,皇帝心里自是疼得很。当初选驸马的时候,礼部先是挑了个陈钊,结果后来又有传言说是陈钊家世有问题,皇帝这般爱面子的最后为着妹妹的幸福也反悔重新再选。当然,最后选出来的驸马谢诏也很不得皇帝欢心,不过谢诏是慈孝献皇后亲自选出来的,皇帝顾着亲娘不好反悔,但也深觉愧对妹妹。
裕王知道这桩旧事却也不好点头应是——当爹的可以说自己不是,当儿子的怎好附和?他勉强劝道:“父皇这是哪里的话?儿臣听说,姑姑和谢驸马如今关系极好,伉俪情深,外头都说这是天赐的好姻缘呢,还是父皇好眼光。”
皇帝一辈子不知听了多少马屁,听着儿子这干巴巴的恭维话实在不得劲,索性转开话题:“你既然来了,可有什么打算?”
裕王悄悄抬眼,隔着珠帘去看皇帝漠然的脸色,小心道:“儿子是想,于情于理,这事还是要由礼部来办。但好歹也是宁安自己过日子,是她一辈子的大事,还是要她亲眼见一见才好。”
这话虽是有理却也有些出格,皇帝沉吟片刻,并没有立刻应下。
裕王只得再接再厉:“再者,陈钊之事决不能再演,驸马家世必然需要谨慎调查。若是可以,还请父皇让陆都督派些人手放手去查才是。”查人这种事,自然是锦衣卫出马来得好。
皇帝听到这里,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你这做哥哥的,想得倒也多。”
裕王早前就得了李清漪的指点,听到皇帝这话起身伏地而拜,顿首低声道:“宁安是儿臣的亲妹,想得再多也是应该的。儿臣自幼长在宫里,最亲近的不过是父皇、母妃还有几个兄弟姐妹,皆是血脉至亲,再亲没有。而今,大哥、二哥、常安、思柔、归善都已经走了,就连母妃也都……儿臣实在是……“
说到伤心之处,裕王伏地而哭,几乎喘不过气来。本来,依着李清漪当初的话,裕王这时候最好扑过去抱一抱皇帝的大腿,借着这大好机会把自己这些年的委屈说个遍。但是裕王最怕的就是皇帝老爹,哭到一半忘了词,只得伏在地上装哭不说话。不过,提及早逝的母妃,他的眼泪立时就真的下来了,怎么也止不住。
这几句话也确实是勾起了皇帝的伤心之处——他自幼体弱多病,好容易求神拜佛才生了几个子女,那么几个儿女对于后宫三千人的皇帝来说真不算多。偏偏,如今剩下的也不过是两子两女,想起早逝的哀冲太子和庄敬太子,皇帝那冷冷硬硬的心也软了下来。
看着裕王哭得厉害,想起杜康妃是年初走的,这儿子又是自己仅剩下的两个儿子之一,皇帝到底起了点慈心,对着左右呵斥道:“都干站着做什么?!没见着裕王哭得厉害吗?还不赶紧去把人扶起来?!”
边上伺候的黄锦连忙跑上去,亲自扶了裕王起来,心里暗道:裕王这一哭倒是颇有魏文帝的风范啊。多日不见,连这般老实的裕王都学会争宠了,真是不得了啊。
当初魏文帝为父亲曹操送行之时就是大哭了一通,生生的把做的一手锦绣好文章的弟弟给比了下去。虽说这里头的讲究很有些不一样,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裕王这一哭可不就把父子间的生疏隔阂哭去了大半,都勾起了皇帝那一点怜惜之心了。
裕王起身重新坐了回去,面上还是通红的,仿佛很不好意思的用袖子遮了遮脸:“叫父皇见笑了。”
皇帝被他这作态逗得一笑,随即又笑叹道:“唉,你也是个有心的,着实难得。”说罢念及宁安公主和她生母曹端妃,心头一叹,摆摆手道,“就依你所言,此事交由礼部,待人选出来了再让锦衣卫查上一查,也让宁安亲自掌眼瞧瞧。”
裕王大喜,连忙抹了抹脸,躬身礼道:“儿臣代宁安谢父皇恩典。”
皇帝没叫起,长眉一扬,居高临下的看他,意味深长的道:“行了,你也别替她谢恩了,过几日还有的你谢呢。”
这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裕王素来是跟不上神经病老爹的思路,他索性再三拜了拜,然后才道:“儿臣想入宫把此事告知宁安,好叫她也放心。”
皇帝点头应下,见他毕恭毕敬的模样又觉得有些兴味索然,摆摆手道:“好了好了,你也退下,莫要在这碍眼。朕也到时候打坐修炼了。”
皇帝的喜怒无常,裕王早就有了准备,轻声道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礼了礼,然后才缓步退了出去。
黄锦把人送到门口,悄悄和他说话:“殿下再等几日,怕是要追封荣淑康妃呢。”皇帝不喜康妃,不仅不许裕王服丧还刻意降低杜康妃的丧仪,甚至只加了“荣淑”二字谥号。比起前头那几个皇贵妃,杜康妃的待遇也太差了一点,低得几乎称得上是羞辱了——要知道,杜康妃可是给皇帝生了个儿子。
裕王听到这话,联系起皇帝那句莫名其妙的“过几日还有的你谢呢”,几乎是欣喜若狂。他连忙扯下腰间系着明黄套子的玉佩塞给黄锦,小声道:“多谢公公指点。”
黄锦惯常是个会做人的,收了玉佩笑了笑,小心谨慎的送了裕王离开。
裕王出了门,心情越发得好,只不过还是惦记着宁安公主一事,勉强沉下心往宫里去——他这头才得了皇帝的旨意,要趁机进宫和宁安说一声才好。
他适才在皇帝哪里说的几句话确实有几句是真心话,虽说景王这种弟弟实在惹人恨但宁安公主这个妹妹也确实是招人疼,他与宁安公主自小就关系极好。做哥哥的难得能替妹妹做些事,心里也很有些得意。
入了宫,他自是依礼先去见沈贵妃,禀明此事。
沈贵妃膝下只养了宁安公主一个,虽是养女却胜过亲生。她心里本就正忧心此事,琢磨着如何去和皇帝说,听到裕王的话,免不了露出笑容来:“还是三郎你这个做哥哥的尽心。”她水眸波光一闪,神态温柔可亲,“是宁安的福气呢。”
裕王连忙躬身:“娘娘言重了,这是做哥哥的该做的。”
沈贵妃却摇摇头:“你觉得这是做哥哥应做的,有些人却不这么想呢。”按理,沈贵妃的城府是不会当着人说出这般几近于明示的话来,但是现今裕王这事实在入了她的心,她自是要稍稍表个态。
裕王受宠若惊,只得连连谦辞。
沈贵妃笑着和他说了几句,这才道:“宁安在偏殿呢,你替我把这碟子茯苓糕端去给她,兄妹两个也正好说说话。”
裕王连声应下,起身往偏殿走去。
至于那碟茯苓糕,无需裕王亲自去端,自有宫人代劳。
宁安公主虽是人在偏殿却早已得了消息,她独自等在门口,见了裕王不由得便扑上来行礼,面上笑靥明艳,犹如明珠般熠熠生辉:“三哥……”既喜且羞,垂下眼揉着衣角,压低了声音道谢,“多谢三哥费心,我,我都记在心上呢。”
第25章 蛋黄粽
大约也是裕王的运气来了,宁安公主选驸马这事还没出结果,皇帝那头已经下了旨,追封杜康妃为荣淑贵妃。
裕王虽然因着黄锦的话已有准备依旧是欢喜难言,当面接了旨,回了房忍不住喜极而泣,大哭了一通。待得痛快哭过,他连忙让人备了酒,打算去白云观找李清漪一起喝酒庆祝。
李清漪正好也得了家里捎来的信,知道自家大姐李清闻给自己添了个外甥,想着长姐多年不易,如今总算熬出头了,很替她高兴。她和裕王两个对坐喝了一大壶的酒,要不是顾忌着是道观,她如今又是这般身份,说不得就真喝出事了。
追封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朝中大臣倒也没几个注意到,知道些内情的严家父子倒是颇有些想法。
皇帝先是给杜康妃追封,十二月时还特地赐了几碗腊八粥给裕王府,连高拱、陈以勤这几个裕王府讲官都跟着沾光……
旁人看着没什么,但严家父子侍奉皇帝好些年,简直是皇帝一撅屁股就知道他要拉什么了。他们心里也十分清楚:这代表着圣心开始偏向裕王了。景王论齿序不及裕王,所占得不过是圣宠。若是皇帝现下偏向裕王,那还有什么争头?
严世蕃咬咬牙,到底还是先把事情放下了:“不急,依着咱们这位陛下的心思,不到最后是绝不会立储的,笑到最后才是赢家。现今要紧的是江南那边,我记得文华写了折子?”
浙直总督张经并非严党之人,反倒更加偏向于次辅徐阶。所以,提他为总督对于严党来说实在是情非得已:当时江南局势危急,倭寇来势汹汹,需要个能压得住场面的人去处理乱局。张经此人也是进士出身,虽然比不得杨博出名但他也是一路凭着战功走过来的,还曾做过兵部尚书,两广之地声名极盛。严家手下确实人多但要找个比张经更好的却是难了,故而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着张经就任。
如今,眼见着张经马上就要摘下胜利的果实,严世蕃和严嵩心里都不太乐意——张经不胜还好,若是胜了这总督的位置就轻易动不得了。叫这么一个和严党有嫌隙的人做着总督的位置,实在是太打脸了。
严嵩年纪渐长,记性也不及当年,听儿子说起这个还要动脑想一想然后才摇头道:“我把文华的折子扣下了,如今张经正得用,据前头战报,这回说不得能打个胜战。正所谓‘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文华这折子不仅告不倒人家还要反被皇上疑心呢。”
严世蕃若有所思,眼珠子一转反倒问:“折子呢?”他一笑,“我看看。”
严嵩转身在案牍上翻了翻,把折子递给儿子。
这赵文华旁的本事不在行,逢迎上意、栽赃陷害、倒打一耙的功夫却是本朝前列,乃是严党不可或缺的重要狗腿人物。
严世蕃只看了几眼,立刻就把里头的实情摸了个清楚,他把折子一丢,问道:“爹,你说这次能打胜战?”
严嵩微微阖眼,点点头:“八/九不离十了。自张经上任以来已经有多少弹劾折子了?他憋着不出声,拖到现在也没回音,怕也是等着打个大胜战来证明自己呢。我已听人说,南边练兵已有成效,还招揽了狼兵,就等时机了,大胜想来已是不远。”
严世蕃面上笑容越加冷漠,他讥诮的道:“时机?”随即冷笑道,“他这战要是打赢了,那才是死定了呢。”
严嵩闻言一顿,睁眼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很快又重新闭了眼,漫不经心的样子:“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抓紧点,把文华的折子改一改,赶在张经捷报之前递过去。”
对这个儿子,严嵩还是很放心的,他已年过七十,精力是一日不如一日。许多事都是交给儿子来办,故而底下的都叫严世蕃为“小阁老”,气焰不可一世。
严家自有门路,消息灵通。等到五月张经捷报传来前,严世蕃帮赵文华修改后的折子已经上了御案。
严世蕃早已摸透了皇帝的心思:江南乃大明赋税重地,这些年因倭寇肆虐,国库吃紧,皇帝心里早就憋着火,这次任命张经为总督主管六省军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剿寇,最好是“马上”就“荡平倭寇”。
所以,他不提张经为这场大捷辛苦练兵、调兵遣将、费心筹谋,更不提石塘湾之胜,只咬死了张经“养寇失机”这一点——经过严世蕃修改后的折子,字字犹如刀剑,正戳在皇帝敏感的心上。他把张经等待援兵以保万全之举称作是“治兵无法,畏贼如虎”又说张经是“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倭报功”。
洋洋洒洒一篇锦绣文章,大意便是:张经贪污军饷并且残害百姓,使得民怨迭起,全军上下敢怒而不敢言。张经畏惧倭寇而不敢战,屡屡拖延时间,还假借等待援军之名放纵倭寇,等倭寇抢掠逃跑之后他又割人头来报功,欺瞒君上,臣赵文华不敢不怒,不敢不报。
皇帝最厌恶的两个字就是“欺君”,当初圣眷优渥连严嵩都比不上的仇鸾也正是败在这两个字上面,哪怕是人死了都不解皇帝心头之恨,还要拖出来鞭尸。看完折子,皇帝已是气急,好险还稳着口气,找人把首辅严嵩叫过来,把折子扔过去,问道:“此事,你怎么看?”
严嵩早有准备,接过折子装模作样看了几眼,口上道:“此事臣亦是有所耳闻,张经上任以来,屡屡拖延不战,拥兵自重,百姓多受倭寇之害,家离子散,恨其欲死,”说到这,严阁老也跟着掉了几点眼泪,“若是再留他在东南,人心不平,军心难安,臣以为——不若下旨让他回京一问。”
皇帝早有此念,听得严嵩此言深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