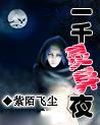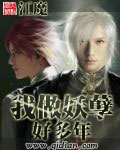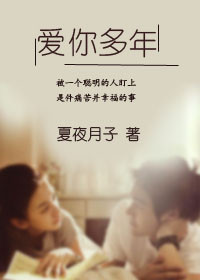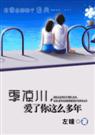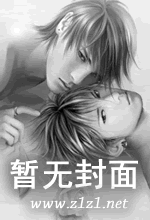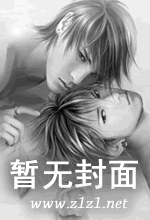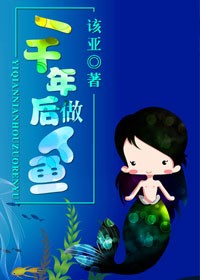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
赵匡胤还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有了皇帝的关注,事情就好办多了。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赵匡胤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品的运输、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往往都在称颂宋代文化的发达,其实要是没有赵匡胤打好的基础,宋代的发达是不可想象的。
以仁厚著称的赵匡胤,银子是他最拿手的武器,无论是对大臣还是小民,都无一例外地诱之以利。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实际上以银子来引导比用刀子来威逼好得多,试问一下,两样摆在你面前,你是喜欢银子还是刀子?赵匡胤用银子解除了兵权,又用银子刺激农民垦荒。那是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赵匡胤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
这样一来,荒芜的土地很快就被开发出来,可种些什么?当然粮食和桑树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你想破头都猜不出,就是枣树和榆树!赵匡胤曾发布种树令:每县将农民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一百棵,第二等种八十棵,依次递减。如果是种植桑枣,只要达到半数,即可完成任务。
为什么鼓励种植榆树和枣树,那是因为枣、榆可帮助人们度过凶荒之年,不饿死人可是天大的善果。为此,赵匡胤明令严禁砍伐:“凡剥三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为首者减死配役,从犯徙三年。”要说“工”可能现在的人不清楚,其实“工”是宋代的一个计量单位,宋时四百一十二尺即为一“工”,“三工”合计就是一千二百三十六尺,换算一下就是四百一十二米。
“凡剥三工”就是指毁树三工,毁掉维系老百姓生计的四百一十二米的树木,仁厚的赵匡胤就要开杀戒,可见老百姓的死活在他心中的分量。
赵匡胤的仁厚来自他宽阔的心胸,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投奔王彦超想混口饭吃,但备受冷落。等他当了皇帝,就找了个机会和王彦超说事,那个王彦超还真会说话:“为臣我当时那洼浅水,怎么能容下您这位真龙,假使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就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
话虽好听,可王彦超势利小人的嘴脸也暴露无遗。面对这种小人,不要说是睚眦必报的皇上,就是心胸稍差的人,也会二话不说就把他弄到大牢或刑场上去。可赵匡胤淡淡一笑,居然以后再也没有和他计较过。就连当初大摆架子、专给赵匡胤穿小鞋的那个董遵诲,他也照样任用。
要说赵匡胤和王彦超、董遵诲毕竟是私人恩怨,可是在涉及那时很在乎的“正统”和“篡逆”的大原则上,赵匡胤的心胸也无人可及。那是在一次宴会上,翰林学士王著几杯小酒下肚,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哭哭啼啼个不休,这可是大失礼的事,追究起来也是可大可小,赵匡胤倒没怎么在意,还命人扶他回去。可这位王著,就是不走,趴到屏风上抹开了鼻涕,深切怀念起旧主子柴世宗来了,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就算杀他的头一点儿都不冤。
可赵匡胤挥挥手:“他就是个酒徒,没啥大出息,我早就知道,况且一个书生哭两声旧主,能翻什么大浪,算了吧。”就这么轻易地把王著放了。要是碰上朱棣或雍正这样的主,诛九族不一定,诛个七族八族的是不在话下。
和这件事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赵匡胤曾想让天雄军节度使、周世宗及皇弟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统领禁军,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赵匡胤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这简直是当着和尚骂贼秃,揭了老赵的老底,换了个皇帝早就挂不住脸面,不暴跳如雷也会拂袖而去,可赵匡胤竟默然无语,此事也就此作罢。
都说真龙天子有“逆鳞”,触犯不得,可在赵匡胤的身上,健全的人格和严格的自律,使他的宽容达到了历代皇帝中少见的高度。
赵匡胤武将出身,穿上了黄袍很少有上马抡刀的机会,就和小鸟较上了劲,没事时喜欢到后园去弹鸟雀。一次,大理寺的主官雷德让有个问题拿不准了,想请示皇帝赵匡胤,可他正打鸟玩得兴起,把雷德让晾在了一边。雷德让不干了,说有紧急国事求见,赵匡胤马上接见了他,可一看奏章不过是很平常的小事,就生气地责备他说谎。谁知道雷德让也是个犟种,说再小的事也比弹鸟雀要紧,这话可够冲的,赵匡胤怒了,抡起不离手的玉柱斧打落了这位雷先生的两颗牙。
雷先生没叫没喊,慢条斯理地把牙捡起来放到怀中。赵匡胤怒问道:“你拾起牙齿放好,是想去告我?”雷德让回答说:“臣无权告陛下,自有史官会将今天的事记载下来。”赵匡胤一听,这可了不得,立马命令赐赏他,以示褒扬。这还不是孤立的事件,《读书镜》中记载,赵匡胤一日罢朝,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对内侍说:“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由此可见赵匡胤的自律。
在封建社会,皇帝有绝对权力,“心有所畏”的皇帝是极其难得的,“心有所畏”,权力才不会被滥用。
可赵匡胤也太过仁厚,甚至到了“滥仁”的地步,且不说在对付辽国的方略上,首先准备的就是“赎买”幽云十六州,不行再动武——这可以说是后来宋朝岁币的雏形,就说他的小舅子王继勋,大吃人肉也仅仅被外放到洛阳了事。
第三章 无法战胜的强邻
残山剩水入囊中(1)
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大雪飞扬,浓重的夜色,似乎是要隐藏尽所有的秘密。
就在这样寒冷诡异的夜晚里,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忽然驾崩,年仅五十岁。
当天赵匡胤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入宫后,赵匡胤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赵匡胤手持玉柱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
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赵匡胤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赵匡胤解衣就寝。然而,到了凌晨,他就驾崩了。
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介布衣起于行伍,凭借浴血军功升任高官,终成一代铁胆天子、矫枉过正的帝王、创业重统之君,结束了血腥残暴的五代动乱,恢复了人性的光辉,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太宗。
此后,大宋王朝又有了一个新的主角。
这就是千古谜团“烛影斧声”,是个至今也无定论的死结。
宋太宗赵光义刚一开始的名字叫匡义,赵匡胤称帝后赐名光义,登上帝位后改名炅。赵匡胤对这个弟弟很好,这是没有异议的,一直让他以亲王的身份兼任开封府尹,按照五代的惯例这就意味着他是皇储。
但实际上,赵匡胤在大局稳定下来后,还是想搞“子承父业”的,他想把都城迁到洛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内里何尝没有要从赵光义的势力已经盘根错节的开封抽身的意思呢?如果说迁都之议还是推测,那么在对待启蒙老师陈先生这件事上,就可以明显看出赵匡胤很在意弟弟势力的扩张。
赵光义知开封以后,就把仍在当“民办教师”的陈先生请来做自己的幕僚,陈先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成了他手下重要的谋士,“人言开封之政,皆出于陈”。赵匡胤得知,很是恼怒,赵光义听说皇帝哥哥生气了,慌忙给陈先生一些银两,让他自谋生路去了。
可陈先生实在倒霉,半路上被强盗打了劫,弄得囊空如洗,学生也招收不上来,只好在驿馆里住着,生活很是窘迫。有一天被请,饥一顿饱一顿的陈先生吃得饱醉而归,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这件事,表面看似赵匡胤记恨当初陈先生经常训斥自己,实际上却是对赵光义坐大的不放心!
赵匡胤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这一要职长达十五年之久,闷声不响地发展起的势力实在惊人,且不说晋王幕府六十多幕僚,就连赵匡胤的旧部楚昭辅、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也和赵光义眉来眼去。
历史惊人地相似,赵匡胤在当初,不也是这样扩张自己势力的吗?
中国人喜欢讲天道循环,从理论上很难得到证明,可实际的例证确实是太多太多了。
尽管历史上对赵光义“兄终弟及”的继位是见仁见智,但他毕竟是坐上了龙椅,宋朝在他的掌控下,继续着自己的历史航程。
赵光义打破新君继位后沿用上一任皇帝年号、过了年再改元的惯例,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这一方面固然是表明自己要“致太平,兴家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想建立功业、提高自己声望、巩固统治地位的迫切心情。
大功业,莫过于开疆拓土。
此时,最弱的当属割据泉、漳一带的陈洪进。当初在宋刚建立不久,泉州节度使留从效就上表臣服,他病死后,统军使陈洪进以接替节度使职位的留从效的侄子曾准备投降吴越钱氏为名,废除了这个“接班人”,推举年老昏聩的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躲在幕后操控着泉、漳的实际大权。
第二年张汉思和陈洪进摩擦频生,张汉思想效仿鸿门宴除掉这个“太上皇”不成,只好“严兵备洪进”,把自己家弄得像兵营似的,这样还整天忐忑不安,怕陈洪进领兵杀过来。
陈洪进还真来了,不过他没有顶盔贯甲,而是穿着平时的衣服,衣袖里藏了把大锁头,串门般来见张汉思,院子里的军兵被他赶走(估计这些军兵也害了怕,巴不得早点儿躲开呢)。张汉思藏在屋子里,被陈洪进拿出锁头锁上了门,成了瓮中之鳖,连跑路都没了可能。
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张汉思,陈洪进快人快语,也不掩饰自己的意思,说:“军士们都认为您年纪大了,不方便执掌这么大的权力,请我陈洪进来领头,众情不可违。现在,请您把大印交给我吧。”张汉思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什么说的,只好乖乖把印绶从门缝里递了出来。陈洪进拿到了象征权力的大印,就召集众人,宣布:“张汉思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地方,就让贤给我了。”
“众情不可违”,这是郭威、赵匡胤都玩过的手段,陈洪进也潇洒地玩了一把。
历史上,这种强奸民意的事,真是数不胜数!
陈洪进夺权成功,便把张汉思软禁起来,这位张老爷,好歹算是没有把脑袋弄丢。陈洪进向南唐称臣,南唐也顺水推舟,委任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授以节钺。陈洪进拥有了泉、南两州。
他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对宋和南唐是刀切豆腐两面光,谁也不得罪。赵匡胤当时正在平灭荆湖,对东南采取安抚政策,乐得平安无事,对陈洪进的归附表示欢迎。
乾德二年(964)正月,宋朝把清源军改称平清军,“任命”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其实人家早就自己走马上任了),不过赵匡胤会送空头人情,把陈洪进的两个儿子一个任命为节度副使,一个任命为南州刺史,正式确定了这两人的官衔,虽然管辖的地盘还是那一块,可总算是得到了宋朝的承认,名正言顺了。
陈洪进对宋朝毕恭毕敬,每年都搜刮地皮给宋献上丰厚的贡礼,来讨好宋朝,加上赵匡胤正忙着平后蜀、灭南汉、取南唐,无暇东顾,陈洪进算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但苟安永远也不是真正的太平,到了赵光义继位,陈洪进漳泉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吴越王钱俶画像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赵光义在崇德殿招待他,表面上礼遇有加,客客气气,还赏赐给“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但半年多也不放他回去,实际上就是在暗示他:你是不是该结束独霸一方了?
陈洪进见赵光义已下定了消灭割据的决心,就和幕僚商议,如若武力抵抗,兵微将寡的漳泉根本不是敌手,他便采纳了幕僚刘昌言的主意,不等赵光义再说什么,就主动献上漳泉两州十四县,这就是历史上的“泉漳纳土”。
赵光义表现得很有风度,任命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位列“使相”。他的两个儿子,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陈文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只是陈洪进被留在京城,不任实职。
漳泉纳土之后,偏安东南的吴越越发地形单影只,纳土归朝已经迫在眉睫。
吴越钱氏,和宋朝的关系绝对不是一般的铁,可谓是大宋的铁杆附庸。赵匡胤刚刚称帝,吴越就最先上表祝贺,表示归顺,以后和大宋也来往频繁,吴越王钱派儿子来朝纳贡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钱不仅对大宋朝廷贡献不绝,对掌实权的大臣也都时常送上厚礼。一次,赵匡胤微服到赵普家,看到廊檐下有钱送来的十瓶“海物”,就让人打开瓶子看一看,结果是十瓶金瓜子,赵匡胤也没上纲上线地追究行贿受贿的罪责,只是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