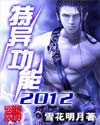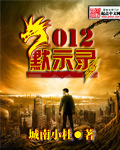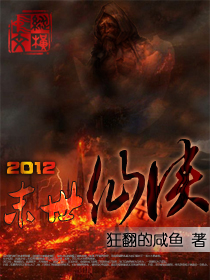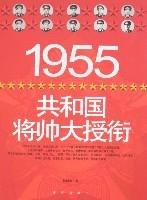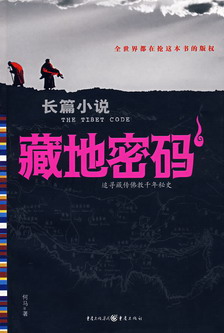1255再铸鼎-第3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研究,当他把拼音与反切法联系起来,又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练习,终于也是掌握了这件工具。不过毕竟华亭方言与东海人用的那种奇怪官话有不少差异,偶尔还是会弄错,在不断的纠错过程中,口音不免被带偏了一点。
翻着翻着,陈维纲来到了“hui”音目下,这里同音字很多,每个字又有不少异体字、不同字号,密密麻麻列了一堆。他皱着眉头看了一下,突然在“辉”字目下停了下来,拨了一下,然后对子弟们说道:“往后此目只余辉一型字即可,除非特别指定,煇之类的异体便不需用了,省得这么多字找起来麻烦。哦,对了,以后,一字有多个字形的时候,尽量用简单的那个,既省油墨,看上去也清爽。”
长辈兼老板要求,子弟们哪敢反对,于是纷纷点头称是。好嘛,若是以往他们这么写了别字,非得惹先生一顿训斥不可,结果在黑心资本家的利润驱使下,居然搞起了字形简化,真是数典忘祖啊!
收拾完新来的铅字,陈维纲刚回到天井中,正要继续检阅刚才的格致新知,门口处就来了生意,于是他赶紧迎了出去。
来客是一个年轻书生,手里捧着一叠稿子。陈维纲一看就心里有数,八成又是哪家的秀才写了一堆诗词杂文想印成册子送给友人,这事多见得很。于是他笑呵呵地迎了上去,问道:“这位客官,可是有文字要付梓?”
书生点头道:“正是。东家,你们这边印起来是什么价钱?”
陈维纲娴熟地说道:“您是想制版还是活字呢?前者要贵些,一尺的版九百文一版,后者论字计价,要便宜不少。不知客官印的是何等文字?若需珍藏,那还是制版的好,但若只是一般的文字,那活字还是要划算些。我家用的可是东国的铅字印刷机,品质亦不差于寻常的雕版”
书生摆摆手:“没甚珍藏的,活字便可。总共约莫五千余字,最好能印于一面大纸上,字尽量大些,需印五百份,这要多少费用?”
陈维纲一愣,这是要自印报么?但也难不倒他,于是顺口报道:“活字排版费千字两贯,五千字便算十贯。这么多字,用寻常报纸幅面的二开纸即可,每份纸墨共耗十九文,五百份便是近万钱了,我便让个价,算作十二贯好了。若需留版,还需每月二贯。”
“留版?”书生对前面没什么意见,只对最后这项有些疑问,“那是什么?”
“哦,就是把排好的字板保留一段时间,以防加印。以往经常有些客人印了书报回去,隔些日子又要加印,这便要再次排版,还得虚耗版费。若是把排好的字板留一阵子,就省了功夫了。只是小店铅字有限,留版就不免耽误一些活计,因此得收一定的费用。如果客官确实要长留,还可用灰泥模翻成硬版,只需五贯钱,比每月付合算些。”
“原来如此。”书生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需留版,就按刚才所说的价格印吧。”
陈维纲满挂着笑容道:“承蒙惠顾,客官先付一半定钱,我给开个定书,过后凭书来取货。”
“也好。”说着,书生把手上的稿子递给陈维纲,又开始从怀中掏钱,先是摸了一大堆会子出来,又依依不舍地掂了两块银元放在了柜台上。“什么时候能印制完毕?”
陈维纲看了一眼柜台上的纸钞和银元后者如今在江南也不罕见了,由于成色足、份量统一,认可度很高;而前者随着公田法的实行进一步发生了贬值,虽然是轻飘飘的纸,但是要攒到足够的市值,也未必会比后者便携数额似乎没什么问题,就翻了一下手中的稿子,随口说道:“十五日可取,今日是初九,那便是廿皇天在上,客官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
也难怪他吓了一跳,这篇稿子写的居然不是什么风花雪月,而是一篇声讨当朝宰相贾似道的檄文!
1255再铸鼎
第542章 觉醒
1266年,10月8日,华亭县,浸香书坊。
“祸出于上?”
陈维纲咀嚼着这个新概念,发出了一些疑问。
对面的纪铭点了点头他就是刚才那个书生,由于要印刷的东西太过骇人,陈维纲不得不把他请入后院详谈。
“正是祸出于上。想当年,汉唐之时,华夏之民北征大漠,西拓西域,是何等的快意风光?可我大宋自立国以来,便屡屡被异族欺辱,哪里还有什么上国气度?究其根底,难道是我汉人不行么?可同样是汉人兵卒,到了金国、蒙国、东海国手下,便能征善战了起来,这不是说明根子不在下而在上吗?”
陈维纲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读史,听了他的话思索了一会儿,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你的意思是,是朝廷无能,方使得国家羸弱?”
纪铭点点头,又摇摇头:“朝廷自然是无能的若是十年前,我也是仅限于此,骂骂无能便罢了。但最近我读了些新书,又与友人互相探讨过,这才醒悟过来。这朝廷无能,不是因为某个大臣某个宰相无能,而是在根子上就出了弊病,也就是朝廷形成的体制有了问题,才导致谁上来都是无能的,才导致国力日弱、任人欺凌!”
陈维纲惊了一下:“此言何出?”
纪铭先是抱拳朝西北方向敬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朝上承五代乱世,为防武人乱政之局重演,自开初之日起便讲究以文治武,又讲究强干弱枝,收兵权于中枢。道理确实没错,然而过犹不及,抑得实在是太过了些。科举大兴,使得世人只知埋头苦读,荒废了武艺;强干弱枝,使得地方无兵无卒,纵使想要拱卫中央也无法。便如靖康之时,各地多少勤王军,被金军一冲即破唉。
但是把财权军事集于一身,禁军就真的强了么?反而朽坏得不成样子了!保家卫国根本指望不上他们,欺压百姓反倒是一把好手这便又是祸出于上了,为了供养禁军,得从地方抽来钱粮方可;为了收地方的钱粮,便得有兵力作为凭恃,还得削弱民间的武力才行。如此弱民,官家的位置倒是稳固了,但是国民日弱,失却了武德,因此便只能沦为奴仆!便不是胡虏的奴仆,也是一家一姓之奴仆!”
陈维纲脸色一下子变了,看了一眼身后,确定周围没人后,小声而急切地说道:“容肃,你这是大不敬之言啊!”
宋朝在言路上一向相当开放,针砭时弊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骂骂贪官庸吏什么的无所谓,可把矛头直指皇权本身,那就大有问题了。
过了一会儿,看着纪铭不屑的表情,陈维纲又说道:“或许如此吧。但是,现在朝廷对北已经占了攻势,又在组建新军,配属火器,听说已经造出了糜烂数十里的万斤大炮,外围还有齐滕蔡巴东海诸国拱卫,总归是无虞的。”
纪铭又“哼”一声,说道:“说来说去,改的还是用,而体还是老一套。新军愈强,耗费的钱粮也就越多,不还是要从民人身上出?看看奸相近年搞的那一套,为了挖钱都要疯了,把民人的田强征了去又分给党羽,会钞印个不停都成纸了,这是要掘社稷的根基啊!”
陈维纲叹了一口气,纪铭说的好像都对,但他陈家受公田法的连累并不多,反而这几年各项产业做得颇为红火,因此实在不想折腾什么。“容肃,你这些都是如何学来的?”
纪铭也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瞒陈东家,我前几年曾经去东海国学医。”
陈维纲一愣:“学医?听说东海医术确有独到之处,不知与国医有何异同?”
纪铭淡淡一笑,说道:“确实很有独到之处,但其实说白了关窍也就一点,那便是谨防外邪入体。”
“外邪?”
“是啊,东海医学称之为微生物,又分了若干种,总之大部分疾病都是因之引发了。东海医学就是围绕外邪展开的,一是保持卫生环境的洁净,用水煮火烤烈酒等方式消去毒物,平日也要勤扫勤洗;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用微量的微生物去感染活人,使人得小病后因此产生免疫力,以后便不会得大病了。”
“原来如此,确实精妙,而且听来颇合医理”
“不过,这只是医人之术,更让我佩服的,是他们的医国之术。”
“医国?此又何解?”
纪铭喝了一口茶,深沉地说道:“东海国官府在各地普设医院、学校,前者救人,后者宣传防病知识。又遍请各地名医,组成医师协会,交流医术,将各类古方、医法去伪存真。又派了医疗队下到各村镇,教导乡民治伤、养病、接生诸常识。如此,不但有无数生灵因此而得活,还因为得病的人少了,传染源便少了,使得剩下的人更为安全这便是医国之术啊!
推而化之,不仅医术如此,教书育人、设厂经商、募兵保国不都是如此?但同是唐人,为何东海国就能做到这样呢?
后来我细细探究,才发现根子出在东海国的构成上东海国并非一家一姓之国,而是多家共同经营的共和之国。家兴便国兴,有国方有家,可以说是真正家国荣辱与共,因此才能人人奋力,将国家经营得风风火火,以一隅之地对抗势不可当的蒙鞑。
再发散看来,当年契丹、女真、蒙古诸部崛起之时,不也是这样?可是一旦进了中原,把部众共和变成了家姓独传,那便失了锐气,只能被后来者取而代之了。再看看史书上的历朝历代,勃兴之时,无不是众人齐心协力才做成一番事业,可一旦归于一家独大,便不可避免地衰败了下去。
一旦想通了这点,我便仿佛发现了一个新世界,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大宋的出路,不在什么新军和火器,而在于根基,在于朝堂,在于每一个士人!所以我便决定弃医南归,以文字激发国人的意志,毕竟,医术再好也救不了一国之人啊!”
10月12日,华亭县,新汀镇。
“抓到了,抓到了!”
“就是这个恶妇!”
“真是可恶,打死她,打死她!”
新汀镇是紧邻着华亭县城的一个镇,由于靠近一条主河道,很是繁华。镇上有一个“济慈堂”,据说是百年前本地出过的一个大官给家乡捐建的,用于收容孤儿寡母什么的。以前这院子一直破破烂烂的,镇上人也不太在意,不过前阵子不知道怎么兴旺起来了,经常有大车进进出出。直到近日才爆了出来,原来是经营这座善堂的郑母强迫院里的孤儿和寡妇们织布出去卖,每月能出上百匹,差不多是日进斗金了。这就激起了镇民们的众怒,他们在本地士绅的带领下,纠结了本地报纸的记者和县城来的衙役,将济慈堂团团围住,把郑母揪了出来,准备给她施以正义的审判。
郑母瘦瘦小小的,此刻被抓散了头发盖住脸面,也看不出岁数,跪在街面上不住磕着头。而周遭的围观群众则不被她所迷惑,依然在不停地朝她扔着土石。在她身后,不少镇民已经急不可耐地冲到了济慈堂内,把里面的罪证,例如尚未售出的布匹、织机还有桌椅瓢盆之类的物什搬回家去妥善地保存了起来。搬着搬着,几个人居然撕扯着扭打了起来。
院门口,十多个或高或矮或老或小但无一例外都又黑又瘦的善堂住民一脸茫然地看着这副场景。啊,他们虽然不用再被逼着织布了,但以后他们该怎么生活呢?
看着从院里逐渐搬出来的几台织机,刘员外有些后怕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对身旁的纪铭说道:“这黑心善堂着实可恶,还好有善心人士举报,不然放任他们这么做下去,遗祸无穷啊!”
当然遗祸无穷了,这种不用给工钱的作坊,得把布价压到多低?刘员外自家的生意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说严重点,这可是动摇了国本啊!
本来他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是经过了一个族侄引荐的好友纪铭点拨,才发现了这件事,拿起算盘来一划拉,才发现问题有些严峻,于是组织乡邻发动群众把这家善堂给砸了。现在看来,还好砸得早,不然过上一阵子,得产多少布匹出来?一地每年能卖出去的布就那么多,她多卖一点就是自己少卖一点啊!
想到这里,他赶紧又对纪铭做了个揖:“容肃忧国忧民,实乃世人楷模啊。”
纪铭回了一礼,说道:“没什么,不过是尽些绵薄之力罢了。对了,刘兄,你家书香门第,又有偌大家业,可曾有办份报纸的意图?”
听到“书香门第”的称赞,刘员外脸上一红,他家连能过发解试的都没几个,哪里配得上这个称呼?不过被人夸了心里总归是舒服的,于是他回道:“报纸?那不都是大家大户办的么?我也能办得?”
纪铭说道:“自然办得。我前日去与浸香书坊的陈东家谈过,一份报纸印来也不过是十余文的耗费,转手卖出去就能赚一倍还多,只需招人写些文章、采访一点时事即可。若是办了报,对刘兄的名望也是大有助益的事”他指了指旁边那个嘉兴旬报的记者,“你瞧,若是以往,官府对这种事会襄助吗?但现在有了记者在场,他们就不敢不闻不问了。为何?不就是怕报纸对他们批驳一通坏了官声吗?若是刘家也有一份报纸护身,那么以后行事自然也要方便不少。”
纪铭前天跟陈维纲聊了半天,在给陈维纲灌输了一堆异端思想的同时,也被陈维纲说服,决定不一下子搞什么激进的檄文,而是先办一份小报,逐渐把自己的思想介绍出去,由浅入深,养出名望来再说。但是他家也不算什么大户,办报有些困难,于是就想起刘员外这么个土豪来了。
刘员外被他一忽悠,颇为意动,不管能赚多少,既然赔不了,那总归是个能提升刘家气质的好东西:“甚好,不过此事还请容肃多帮忙”
1255再铸鼎
第543章 授时
1266年,10月27日,广东南部海域。
“修正航向角,南偏西67度20分;航行里程,12450海里。”
巡航舰“暴雨”号的舰桥内部,实习军官石尔茂读出了仪器上的记录数据,另一名实习军官赵启明将它们记录了下来。他们先是把数值记录在本子上,然后两人各自趴到了桌子上,拿出尺笔,在各自的坐标纸上记录下这段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