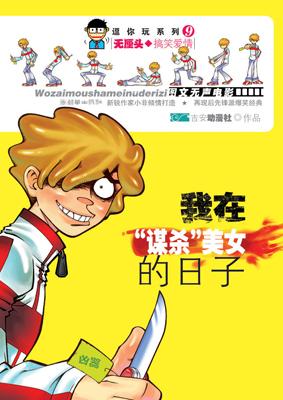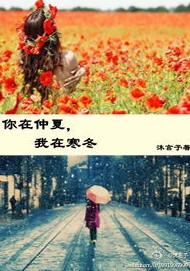我在诏狱看大门-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就不是我们此次南下巡查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万达将水碗放回桌子上。
“看来运河下游的清淤和修闸势在必行。不然涨价的可不止是粮食那么简单了。茶叶,陶瓷,布匹,丝绸,这些所有南方的特产如果真的必须要靠陆路北上,那价格势必跟着飞涨。说不定就连朝廷贡品的采买,到时候都会出现问题。”
邱子晋想了想,没把下一句说出来。
北方重镇的“市边”,恐怕届时也会受到影响。
如今朝廷和瓦剌人在边境互市,大明对外最重要的商品就是南方的茶叶和瓷器,多年以来,价格还算稳定。
若是不久之后,因为运输问题,导致茶叶和瓷器的价格疯涨。
邱子晋不认为那些北方蛮族,会坐下来倾听他们解释,说什么千年大运河受阻是实属无奈,而是认为你们汉人不讲信用,做买卖坐地起价。
原来一匹马能换到的茶叶和瓷器,如今要用两匹马才能换得到,那不就意味着汉人皇帝想要开战么?
京师的正常运转,全赖着大运河的维系。这条命脉堵住了,京师也就离危机不远了。
“宋大人。”
“不敢。”
邱子晋招呼县令坐下,对方谦卑地摆了摆手,不敢与邱子晋和万达两人争坐。
官场只看官阶大小,莫说这宋大人今年五十,哪怕他七十了,在二十岁不到的上官面前也只能站着。
“今年的御窑烧的如何?负责御窑烧制的督办又是哪一位?”
景德镇作为大明皇家御用瓷器的供应地,除了本地大量的民间瓷窑,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御窑”和“官窑”。
其中位于珠山的御器厂,负责皇家瓷器特…供,官窑中有所谓的“督陶官”,即督造陶瓷烧制的宦官和工部官员以及部分地方官员。
“大人,下官在此。”
跟在县官身后的工部虞衡司郎中出列,对着邱子晋和万达行礼。
听说这位巡抚大人莅临,整个景德镇的官员们都活动了起来。自然也包含负责御器厂和御茶园的大小官员,今天一早就集合在邱家宅的牌坊下,一路跟随,就等着上官召见问话。
“你是督陶官何瓛?”
邱子晋看着眼前这个留着一把胡须的中年人问道。
“正是在下。”
这位督陶官姓何名瓛,松江府华亭县人,在此任职已近三年了。
邱子晋离开家乡之前他还未上任,不过这一路上也听说过这位何郎中的官声。
他为官清廉,体恤窑工,在当地颇有人望,深得当地陶工们的爱戴。
“何郎中为民造福,本巡按早就耳闻。”
“大人过奖。”
督陶官只负责御窑造办,不理其他俗物,能做出这样的口碑,实属不易。
“督办太监又是谁,今日为何不在?”
邱子晋看了一眼他身后带着的两个陶工,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太明特产,督办太监和守备太监的权利凌驾当地官员之上。这种场合按理说那位公公应该出来露个脸才对。
何况这里站着在内侍圈里口碑一流的小国舅万大人呢,不出来拍拍马屁简直对不起“宦官”两个字。
“这……”
何郎中眼神飘忽,明显有些为难。
“但说无妨。”
万达在一旁说道。
“梁公公他……有事回京城去了。”
何郎中说完,深深地低下头。
“回京城?难道是御器厂发生了什么大事,需要回京上报?还是宫里内府出新的样式了么?”
这两年景德镇的陶瓷烧造技术突飞猛进,有一种成形与宣德年间的“斗彩瓷”,在最近深得陛下和娘娘的喜爱。
邱子晋以为是宫里新做出了花样需要景德镇御窑这边烧造,故而将督造太监招了回去,心道这也是常事。
万达日常出入昭德宫,对于他姐夫满身的“艺术细胞”也是长期进行过沉浸式体验的。之前在歙县的县衙里,不刚还体验了《一团和气图》的威力么。
万达也认为恐怕是他姐夫又想出了什么新的花样,或者“爱妻”毛病又发作了,想着给姐姐或是小皇子特意烧一套瓷器之类的,所以让内府八局的造办把那位“梁太监”给招入内宫了。
“之前御窑厂里烧制出了一批窑变的瓷器,梁大人特意送到京师去了。”
何郎中见隐瞒不过,只能实话实说。
“如今算来,已经走了一个月有余了。”
“窑变?何大人,窑变的瓷器虽然珍贵,但是作为贡品上供……是否过于不妥呢?”
邱子晋眉头一皱,语气也变得强硬了起来。
“什么情况?什么叫‘窑变’?为什么不妥?”
万达对这些瓶瓶罐罐完全没有研究,不解地拉了拉杨休羡的袖管,低声问道。
“制作瓷器,除了有培泥的配比,塑形,上釉等等工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火候的掌控。”
杨休羡凑到他耳边解释道,“‘窑变’就是火候出问题了。”
“那不就跟我做菜一样?”
万达心想这个我熟。
这做菜也讲究食材的来源,刀工的好坏,不过最考验厨子的还是对火候的控制。这种手上的功夫,除了不断磨练,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当然不一样,灶火说到底是人可以控制的。但是窑火的变数可就多了。变得好,得‘火气’之精华,烧制出的瓷器流光溢彩,光怪陆离。变得不好,就是所谓的‘死器’,釉色黯淡不说,可能整个胎器裂开,导致之前数日乃至数月心血全部白费。”
杨休羡补充说道。
若遇上太监催工,京师那边等着这批器物进贡使用,那真是要逼死人了。
“甚至还有所谓‘炸窑’一说,天数不对,一整个窑内的所有瓷器全部毁灭。甚至窑厂本身都可能发生危险,乃至殃及人命。”
因为不可控的变数实在太多,古人在烧窑之前,包括开窑那天,工匠们都会选择黄道吉日,并且供奉火德星君,在算准的吉日吉时开窑,以祈求平安无事。
莫说在烧柴烧炭,无法精确掌握温度的古代,哪怕六百年后的瓷器陶器艺术家们,在面对可以控温控湿的电磁炉的时候也会发生“炸窑”“窑变”的情况。
除了一句“天数”,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听到杨休羡这番解释,万达懵懵懂懂地捉住了些要点——
“就是说,最近的一次‘窑变’里,偶然烧出了一批精品瓷器,比预想的更加精彩,所以那个梁太监迫不及待地把它们送到京城上供去了是不是?”
“那这不是好事么?”
万达理所当然地想着。
这不就是“限量版”嘛,好东西送进皇宫天经地义啊。
“当然不是好事。”
邱子晋也听到了他俩的谈话,回过头看着万达。
“‘窑变’之事,可遇而不可求。这一次烧成这个样子,惊天动地,流光溢彩,皇上看了龙颜大悦。但是下一次呢?皇家的贡品可是要求年年上供同样的形制的。如何回回都能得到上天的眷顾?若是回回得到,那还算是‘窑变’么?”
万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有点触类旁通的感觉。
据姐姐身边的陈司膳所言,这宫里的日常饮食其实比宫外大户人家来得要无趣的多。
尤其是“不时不食”这点,除了因为皇帝身为“天子”,要顺应天理,不可与天时季候相反。
更重要的是——皇帝偶然一次在冬天吃到了西瓜,之后每个冬天都想吃西瓜怎么办?
一旦成为贡品,就意味着成为常例,常例不容更改,一改就是劳民伤财。
贡茶、贡瓷、贡缎也都是同样的道理。
身为帝王,一生被宫墙所困,不知外头节气变化还情有可原。
若是身边的太监宦官为了一己私欲,讨好皇帝和娘娘,导致“特例”成为了“常例”,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邱子晋不悦地转向何瓛,“何郎中,我听说自从你担任督陶官以来。就未曾将窑变的瓷器作为成品上供,而是就地封存。就是为了避免内局之人,逼迫陶工烧制同样效果的陶瓷出来。怎么如今又开了这样的风气出来?”
当地陶工之所以爱戴这位何郎中,除了他愿意为了给陶工说话,与负责督办监造的太监争取合理的工期和报酬之外,据说最重要的就是他敢于顶住压力,不上供“窑变”瓷器。
怎么如今看来,难道这口碑是虚假的不成?
“大人,这事儿不能怪我们何大人。”
见到邱子晋对何郎中疾言厉色,陪同何郎中一同前来的窑厂工头主动出声了。
一旁站着的官吏刚要斥责,就被万达眼明手快地拦了下来。
“你说,我们听着。”
“老朽姓庄,在这御器厂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还是老老皇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内廷烧制陶瓷了。”
老头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以前负责督造的公公姓张。那位张公公性格不紧不慢,与我们何郎中配合的相得益彰。何郎中提出不要上缴窑变瓷器的提议,也是那位张公公同意的。为此,还特意在窑厂北面建了一个仓库,专门用来存放窑变之器。”
邱子晋听着,赞同地点了点头。
万达则是内心一动——
一整间仓库的“限量版”?那还不得去看看!
皇宫里要说奇珍异宝最多的就是姐姐万贞儿住的昭德宫了,这个“限量版”仓库里的东西,是不是比昭德宫的更漂亮呢?
他将渴求的视线投向了邱子晋,大大的杏仁眼里飘过六个字
——晋晋,漂漂,看看!
邱子晋无语地转过头去,继续与那个庄陶工对话。
“你的意思是说,换了新的督造太监后,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正是!”
庄陶工斩钉截铁地说道,“老朽年纪大了,已经干不动了,子孙们也没有人能继承我的手艺。别人都不敢说,那就由我来说。”
庄老头看来是个猛人。
“这新来的梁太监虽然只是上任了不到一年,却是处处和我们何郎中不和。之前定下的规矩也被他改的七七八八。最近的一次窑变甚至差点出了人……”
“老庄!够了!”
何郎中高声打断了庄陶工的叙述,转身对邱子晋作揖,“大人,老庄他心直口快,绝不是故意要冒犯梁公公的,请大人们不要放在心上。”
邱子晋之前在歙县惩治当地豪强士绅的事迹已经传到了他们景德镇。
传说中眼前这位长得喜庆的万大人更是“暴虐成性”,“凶残无比”,把歙县的两个年老的乡贤吊起来拷打示众。
何郎中可不敢任由这个陶工继续说下去,免得他为此得罪人,丢了命。
“梁公公……是哪位?”
万达摸了摸下巴。
旁人眼里视若洪水猛兽的内侍太监们,在万达这里那就根本算不上什么。
别说一个督办太监了,就算是五军都护府的守备太监,封疆大吏,真的要是犯了法,他都有办法惩治。
“这事儿不急,一个太监而已,问问东厂那边就知道了。”
听这位小万大人口气如此之大,倒是把深受宦官之害的何郎中等人给听的没了脾气。
听听这话说的——一个太监而已,问问东厂就行——东厂的人难道是那么容易差遣的么?
邱子晋闻言,也是感慨不已。
他这监察御史的官职再牛,奏折能够直达天听又如何?
真的办起案子来,比起这位行走在各种势力边缘的万大人,还真的没有他横行霸道的底气。
“哎呀,别说这些了,那个‘限量版’仓库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在这热辣辣的日头下面走下去,万达都觉得自己要热炸了。还不如去参观参观御器厂,去室内看看珍宝呢。
“何郎中,你放心。”
一行人离开凉棚,朝窑厂那边走去。
“本官就看看,我不会要的。”
万达真诚地说道。
毕竟在他的眼里,侯爵府的瓶瓶罐罐与六百年后,路边上打着“跳楼清仓大甩卖,走过路过别错过”招牌的瓷器店里卖的东西也没啥很大的区别。
何郎中苦笑一声,和宋县令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
————————————————
紫禁城仁寿宫内
周太后趴在榻上,泪水流个不停。
已经爬上了淡淡细纹的眼角因为长时间的哭泣已经微微发肿,过于炎热的天气让本来四四方方的皇城更显的憋闷,教已经哭泣了将近一个早晨的太后几乎无法透气。
“娘娘,您不能再伤心了,不然崇王陛下知道您这样折磨自己的身子,怕是走在路上都要难受啊。”
她的大宫女跪在榻边,一边为她打着扇子,一边安慰道。
“那么热的天,他一个做哥哥的就舍得弟弟上路。汝宁距离京城千里迢迢,泽儿他在路上,要是有个好歹可怎么办?”
今天一早,崇王朱见泽就来到仁寿宫与周太后告别,随即启程,出发前往受封的藩地汝宁。
这对母子彼此心里都清楚,不管按照祖宗家法还是按照当今圣上的心思,只要崇王一离开皇宫,就意味哪怕身死魂消,他们母子都再无见面之日。
按照周太后原来的打算,至少也要拖到崇王成年,娶了王妃,最好连孩子都生了几个后,全家人开开心心地前往封地。
然后她再求求皇帝儿子,多给小儿子封些田庄,好保证幼子全家衣食无忧。
结果现在只有幼子一人孤零零地就藩不算,就连田庄,也只得了百顷而已——陛下说了,一切以旧例为准,参照的是当年郑王朱瞻埈的封赏。
这位第一代郑王脾气暴烈,曾经数次将人活活打死。
周太后的丈夫朱祁镇在位的时候,为了管教这位郑王叔叔,特意将自己身边的御史周瑛派去做郑王的长使。
名为“长使”,实为“监视”,从此之后郑王殿下就老实了一辈子,再也没犯过混。
朱见深以这位先辈为“榜样”,封赏自己的弟弟,恐吓的意味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