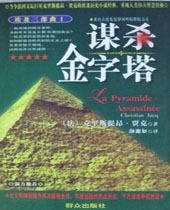我钻进了金字塔-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三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他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学四年,坚信我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勇敢诚实,而且生来一张直肠子驴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华社。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
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
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
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
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