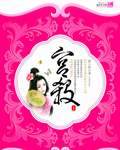南京大屠杀-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 '7'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7' 野间宏(1915-) , 日本作家。1941年曾应征入伍,到过菲律宾等地,1943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不久被开除军籍。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发表的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生活,获每日出版文学奖——译者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8' 长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绿川英子,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她曾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人民一起用世界语写文章,对日本进行日语广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自己的一生——译者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9' 竹内实(1923-),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译者'10' 索姆米译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发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杀事件——译者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11' 风见章(1886-1961) ,日本政治家。记者出身,曾任通讯社主笔、报社社长,并到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过考察。1943年退出政界。战后重返政界,1953年10月曾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访华。1957年被推选为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译者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第一节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道吗?
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道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并对第二编《“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著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一进行了批判。 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采用了旧著《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道,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 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道。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对虚假报道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人的虚假报道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是对当时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汇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著。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著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 悖理的话来, 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杀百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