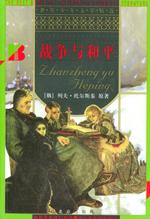战争与和平-第1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血从右侧腹部流出来,在草地上流了一大团血。
叫来抬担架的后备军人在军官们身后站着。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站着干吗,快过来!”
农夫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是他凄惨地呻吟起来,农夫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人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从军官们之间传出叹息声。
“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
几个农夫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夫的肩膀,叫他们停下来。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夫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夫,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裹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子军士,他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大声说话,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兵。正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顾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了欣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
………………………………………………
37
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a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
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钻心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噢!”他像个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道。
他认出那个不幸的、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腿的人就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扶起他,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着的肿起的嘴唇老挨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痛苦地啜泣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不知怎的和我密切而沉痛地连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还没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就想道。“这个人与我的童年,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却得不到答案。突然,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从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回忆。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手臂,她那时时都处于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心灵深处对她的眷恋和柔情苏醒了,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泪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于是对那个人强烈的怜悯和挚爱之情充满了他那幸福的心。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了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别人,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认识。
“对兄弟们、对爱他人的人们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散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
38
死者与伤者遍布疆场的可怕景象,再加上头脑昏胀以及二十个他所熟悉的将军或伤或亡的消息,往日有力的胳膊变得软弱无力的感觉,这一切在爱着死伤的人,并以此作为考验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拿破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印象。这天战场上的可怕景象使他在精神上屈服了,而他本来认为他的功绩和伟大都来自这种精神力量。他连忙离开战场,回到了舍瓦尔金诺土岗。他坐在折椅上,脸姜黄而浮肿,心情沉重,眼睛混浊,鼻子发红,声音沙哑,他不由得耷拉下眼皮,无意地听着枪炮声。他怀着病态的忧悒企望结束那场由他挑起的战争,但他已无法阻止它。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感情,暂时地战胜了他长期为之效劳的那种虚假的人生幻影。
他真自感受到了他在战场上所见到的那些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头和胸的沉重感觉,使他想到他自己也有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可能。在这顷刻间,他不想要莫斯科,不想要胜利,不想要荣誉。他还需要什么荣誉呢?他现在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得到休息、安静和自由。但是,当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高地时,炮兵司令向他建议,调几个炮兵连到这些高地上,对聚集在克尼亚济科沃前的俄军加强火力攻击,拿破仑同意了,并且命令向他报告那些炮兵连的作战效果。
一名副官前来报告说,遵照皇帝的命令,调来二百门大炮轰击俄军,但俄军仍坚守着。
“他们被我们的炮火成排地撂倒,可他们动也不动。”那个副官说。
“llsenveulentencore!……”①拿破仑声音沙哑地说。
“Sire?”②那个副官没听清楚,问道。
……………………
①法语:他们还嫌不够!……
②法语:陛下?
“llsenveulentencore,donnezleur-en.”①拿破仑皱着眉头,嗓子嘶哑地说。
其实,不待他发命令,他要求做的事就已做了。他所以发布命令,只不过因为他以为人们在等待他的命令。于是他又回到他原来那个充满某种伟大幻影的虚幻世界(就像一匹推磨的马,自以为在替自己做事),又驯服地做起注定要由他扮演的那个残酷、可悲、沉重、不人道的角色。
不止在那一刻,也不止在那一天,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沉重地负起眼前这副重担的人的智力和良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永远、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不能理解真、善、美,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的意义。因为他的行为太违反真与善,与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离得太远,所以他无法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不能摒弃他那誉满半球的行为,所以他要摒弃真和善以及一切人性的东西。
不仅在这一天,他巡视那遍布着死者和伤者的战场(他认为那些伤亡是由他的意志造成的),看着这些人,计算着多少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由此他自欺地找到了使他高兴的理由:五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也不只是在这一天,他给巴黎的信中这样写道:lechampdebatailleaétésuBperbe,②因为在战场上有五万具尸体,而且在圣赫勒拿岛上,在那幽禁、寂静的地方,他说,他要利用闲暇时光,记述他的丰功伟绩,他用法语写道:
……………………
①法语:还嫌不够,那就多给他们一些。
②法语:战场的景象是壮丽的。
“远征俄国的战争,本来是现代最闻名的战争,因为这是明智的、为了真正利益的战争,是为了全人类的绥靖和安全的战争;它纯粹是热爱和平的稳妥的战争。
那场战争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为了意外事件的
终结,为了安定的开始。新的境界,新的事业正在出现,全人类的安宁幸福和繁荣昌盛正在出现。欧洲的制度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建立起来。
在这些大问题都得到满意解决,到处都安宁下来之
后,我也就有我的国会和神圣同盟了。这些观点是他们从我这里窃取的。在这次各国伟大的君主会议中,我们应当像一家人一样讨论我们的利益。并且像管帐先生对主人那样向各国人民提出汇报。
按这样去做,欧洲一定很快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人不论去何地旅行,就如同进入共同的祖国。我呼吁所有的河流供所有人航行,海洋公有,庞大的常备军一律缩编成各国君主的近卫军。
回到法国,回到伟大、强盛、瑰丽、和平、光荣的
祖国,我要宣布,她的国界永远不变;未来一切战争,是防御性的;任何扩张都是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我要会同我的儿子掌管帝国政治,我的独裁要结束了,他的宪政就要开始……
巴黎将要成为世界的首都,法国人要成为万国人民
仰慕的对象!……
到那时候,我将利用我闲暇与晚年,在皇后陪伴下,在我儿子受皇家教育期间,像一对真正的农村夫妇一样,驾着自己的马车,畅游帝国各个角落,接受诉状,平反冤狱,在各地传播知识,施舍恩惠。”
天意注定他充当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他自信他的行动动机是造福于人民,自信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能凭借权利施舍恩惠。
“渡过维斯杜拉河的四十万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