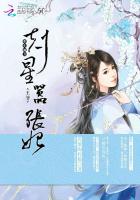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2)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也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莫斯科市检察机关也开始调查1997年抵押拍卖中某些值得怀疑的情况。当时那场拍卖结果是“诺里尔斯克镍业”大型工业集团公司转由波塔宁领导的工业——金融集团“国际俄罗斯”控制。波塔宁意外收到的总检察院通知函,要求他“尽早补偿”由于抵押拍卖过程中因违反规则和条件而使国家遭受的1。4亿美元损失。
6月底,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领导的“阿尔法”银行集团旗下的“秋明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账目等遭到查抄。根据总检察院要求接受文件调查和查抄的特大公司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样著名的大公司。一些报纸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针对大资本家的新政策,甚至是国家政权对“国家实业精英们”所发动的攻势。《货币》杂志通知自己的读者说,这次攻势的发起者普京总统将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特别咨文中,宣布与寡头们或“反对派资本家阶层” 展开斗争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预言都破产了,普京没有任何与大资本家做斗争的计划。
要知道,寡头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控制俄罗斯的全部经济部门,但也控制了不少部门和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进程的日益明朗化,可以分析出这种寡头资本主义模式所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
(1)第一阶段(1992~1993年)、第二阶段(1994~1995年)和第三阶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进程。最终结果是,大部分企业通过私有化这一形式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中。但是,这些个人和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大投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人有能力投资几千万或者几亿美元购买石油公司、机场、电视公司、汽车厂、铝业等。
结果是,大部分银行和企业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权和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他们要么是以超低的价格收购那种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证券,要么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从被欺骗的公民手中和预算中搜刮钱财。还有不少这样的新私有者,他们不是利用和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与罪犯集团相勾结而发家致富的,这一点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铝业战争”中明显地看到。
政府和总统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用“所有这些不过是‘原始积累阶段’ 不可避免需要缴纳的学费”这种荒谬的说法安慰自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更有成效的私有者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业主。1998年8月17日经济危机以后,不成功私有业主的破产进程开始显现;1999~200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许多大量侵吞国有财产的人对于如何消化这些财产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就连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绝大部分寡头是靠吸收国家这棵大树的营养而快速发家的。亚夫林斯基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应当让这些寡头远离这棵大树,而不必去弄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和非法占有了什么。
但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国家和国家预算的支撑,许多寡头简直就无法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尽管他们有钱在法国的蓝色海岸或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购置别墅,但却没有足够资金去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支付工人工资以及上缴电费和税收。
不过,国家不可能无休无止地供养这些“实业界精英”。
(2)国家短期债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导致1993~1997年全国金融资本人为急剧增长的个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有人利用现实经济部门、居民手中的部分闲钱和国家预算大肆进行投机活动。1998年8月17日的银行倒闭风潮不仅使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且让整个私有商业银行系统也受到重创。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这样曾经显赫的寡头都纷纷从大生意场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属于古辛斯基所有的“桥银行”以及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先后宣告破产。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头们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艰难地挺过来了,他们将自己银行体系内大部分“有活力” 的业务剥离到其他规模虽小但却“很友好”的银行中,而保持对规模庞大并且有赢利的工业集团(如“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运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无论是私人小储户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破产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实业界集团自身内部出现一些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搞清这种状况的任务应当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们身上,而不是由总统亲自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去保护所有私营者、而非只是大银行家和寡头们的权利。阿纳托利·丘拜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寡头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的、并且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争夺,成了俄罗斯许多富有的大商人经常遭遇麻烦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生意场上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复杂一些,”丘拜斯在接受采访中时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普京深思熟虑的一步一步消灭寡头的计划。这好比糖渍水果饮料,熬制的原料中有许多块水果,但人们却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事件是生意场上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进行较量的外在必然表现。”但是,当记者请求他详细解释自己的论断时,丘拜斯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我不能说。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3)
(3)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都受新出现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控制。
在西方,一些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一般都能给自己的投资人带来不小的利润,由于有利可图,这些大众传媒积极拓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其他商业领域建立金融工业公司和集团。而在俄罗斯,由于民众、其中也包括那些被称为中产阶级的民众生活贫困,因此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俄罗斯,报纸、杂志和书籍价格相对便宜,发行量低于5万份根本就不够支付纸张和印刷服务成本。即使发行量很大,大部分报纸和杂志也生存艰难。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反映在所有主要的电视频道上。哪怕是将数目不小的广告收入计算在内,所有主要电视频道,其中包括独立电视台、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都没有为自己的股东们和投资人带来利润。只有从大商人那里获得巨额补贴,所有这些大众传媒才能够正常运转。
不过,在向大众传媒投入相当大的资金以后,与其说银行和大工业集团想获得商业利润,倒不如说是希望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其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产生影响,并促使政权通过对某一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此外,这些大众传媒还可以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名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有关对自己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最后,还能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入联邦级和地区各级政权领导层。此外,重要的当然是广告收入,因为广告是能够带来较大利润的商品。
总统大选以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的局面出现了。不过,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稳定,才导致大商人对俄罗斯大众传播媒体的金融投入出现了根本性的减少。政权争夺战业已、或者说正在接近结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浪费大笔资金给报纸呢?
与“梅地亚…桥”公司丑闻同时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主要电视频道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事情居然到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公开希望将自己控股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49%的股份归还给国家的程度。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整个媒体生意让他亏损很大,他不得不用其他行业生意中的利润来填补媒体亏损的深洞。
更为复杂的是“梅地亚…桥”公司的财政状况,因为对这家公司来说,媒体生意正是有形强大实力的主要支柱,在俄罗斯的所有大众传播媒体中,被认为最有保障的就是这家公司。至少,这家公司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稿酬是最高的。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要比俄罗斯电视台的好得多。现在,上述这些优厚待遇都面临威胁。已经很清楚的是,“梅地亚…桥”公司在最近2~3年里从西方公司那里贷了不少款,而数目特别大的那笔贷款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些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超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样已经拥有不少信息资源的、相对独立的大公司会借给古辛斯基几亿美元,却又不急于要求他还清贷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列姆·维亚希列夫被迫承认,“在这些交易中,‘天然气工业公司’并没有获得任何利润。之所以将钱借给他们,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不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要是在其他国家的话,完全可以称这种关系为经济勒索,或者更简单一些,就是讹诈。
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后,他的控股公司里的一些头面人物立即兴高采烈地公开发表谈话说,经历这些磨难之后,再也无人能够将古辛斯基搞垮了,因为作为一名捍卫言论自由的卓越战士,西方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最大信贷大门都会对他敞开。但是,事实上他们所想像的那种场景没有出现。他们过分渲染了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社会、金融机构支持古辛斯基的力度。据西方媒体报道,古辛斯基及其领导的公司的总债务额超过10亿美元,没有人急于帮忙清偿这些债务……
在有关寡头们遭到迫害的报道方面,与俄罗斯大众传媒吵吵嚷嚷、议论纷纷的内容形成对比的是,护法机关所采取的调查行动的规模并不很大。2000年全年,在许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小小的以色列、瑞士等国的司法和检察机关对商人和政治家涉嫌犯罪案件所进行的调查都比俄罗斯进行的调查要多得多。我们可以回忆起德国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金融活动遭调查的情况;在美国,针对比尔·盖茨案件的司法调查已经不止一年,这令这位世界首富早已疲惫不堪;在英国,那位没有做任何不体面事情的商人、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已经被捕快两年了——而这个人是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偶像。
那么,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令俄罗斯超级富豪极度敏感、甚至胆怯的首先在于,他们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缺乏合法性。他们的生意是在异常混乱中完成的,缺乏透明度,恰恰是这一点,让人们盯着他们过去所经营的事业中曾有过的犯罪行为。
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拥有巨额财产,做过几亿美元的交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这些超大型企业从何处聚敛如此大量的资金以及控股股票,尤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都知道某一个全国闻名的大企业,甚至某一工业行业都成了私人财产——并且不完全能成为俄罗斯公民的私产。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一切是怎样、为什么发生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为国家及其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4)
为什么在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镍业今天成了几个80年代还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的私有企业?要知道,形成这家企业现在的规模,整整用了70年,其中还有斯大林集中营中几万囚犯的辛苦劳动。怎么能用1。5亿美元价格就买得到?这家企业每年光纯利润就可达到10亿美元,这些利润都跑到哪儿去了?
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的共青团员们,剧院导演和布景师,养蜂人或者是工厂厂长、国家部委里的官员们,又是怎么如此努力搞到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财富的呢?在20世纪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商业历史中,“巨头们”污点当然也很多;但在10~12年历史中,俄罗斯寡头们这样的污点或者是空白点却更多,这让那些希望在俄罗斯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生意人感到害怕。
缺乏合法性不仅让许多俄罗斯大商人感到担心,而且造成经营业绩非常不明显。他们的商业活动常常带有寄生性质,因为他们殚精竭虑地将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藏起来,以各种方式打到国外银行的账号上——最好是,离俄罗斯越远越好。
在巨大交易以及金融领域中,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
俄罗斯失控体制的完结
在签署了不离境的承诺书以后,古辛斯基从监狱里获释,由此而产生的尖锐危机也暂告一段落,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早在1997年,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曾以他特有的真诚慨叹来评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冲突风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两个寡头之间吵来吵去,让整个俄罗斯都感到了震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几年前还是在今天,国家和社会受“震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寡头们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以及彼此之间的争执,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失控,而这种体制形成于9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本人参与了它的确立。
鲍里斯·叶利钦宁愿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也要努力理顺和完善自己那个著名的“克制加平衡”系统,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激进分子们所提出的建议,他都一概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体制形成了。于是,他们开始划分各个政治家集团间以及寡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势力范围。此外,从横向看,政权上层之间划分;从纵向看,中央与州、边疆区行政长官,与各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总统们以及各城市市长与地方寡头们之间也分配权力。
我们非常清楚专制体制的缺陷,它是依靠一个人的意志和智慧为中心进行管理的。但是,一个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由政治家、官员们和商人们组成的集团与另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