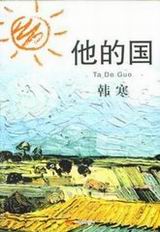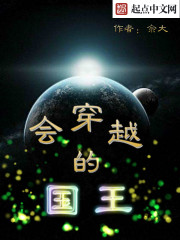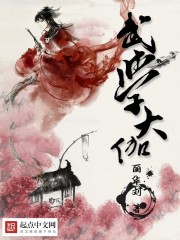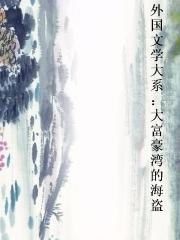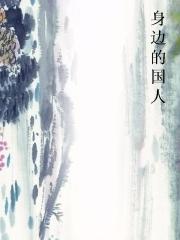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第54节:偶像陈寅恪(6)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 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 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第55节:偶像陈寅恪(7)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 。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 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