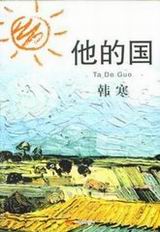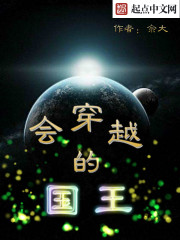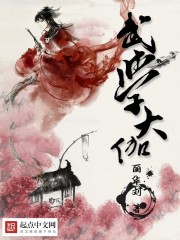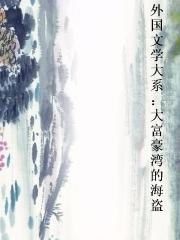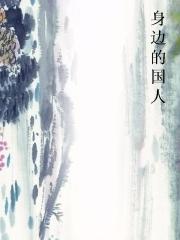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第5节:朋友胡适之(2)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 。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2 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第6节:朋友胡适之(3)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第7节:朋友胡适之(4)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