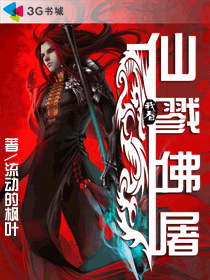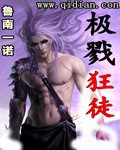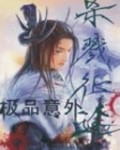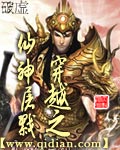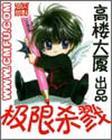秦汉戮-第1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丞相之议不可用!”周亚夫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朝廷中有可能呆不下去了。他有点悲凉地离开了未央宫,在离开宫门的一刹那,他扭头回望了一眼,摇摇头叹息一声,孤零零地离开了。
几日过后,匈奴徐卢等六人被封为侯。与此同时,周亚夫上了道特殊的奏折辞职信。这份辞职信正中刘启的下怀,早就想让你走,结果你主动提出来了,那就不客气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丞相没有作出任何挽留的表示。
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九月,周亚夫免职回家,御史大夫刘舍继任丞相。
周亚夫最终没有逃出他父亲的命运,无缘无故丢了丞相的帽子。
王信和梁王的阴谋最终得逞。总算报了一箭之仇,梁王很高兴,但他也没高兴得太久,因为他死了。刘启嫌梁王在长安呆久了,下令他离开长安回到梁国封地,回到封地后,梁王竟然一病不起,很快就死了。
他的死讯传到长安的时候,窦老太太几乎昏了过去。窦太后醒来之后,日夜啼哭,埋怨刘启逼死了兄弟。刘启没办法,只能将梁王的五个儿子悉数封侯,才让老太太平静下来。
梁王死了,刘启终于可以不为太子之位的稳固烦心了,老太太虽然难过,但在储君之位上已经没了人选,也无话可说了。刘启的后宫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安宁。像所有的君主一样,在所有威胁储君之位的隐患消除后,刘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培养太子羽翼之上。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接过他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八月,卫绾接任丞相,直不疑升任御史大夫。刘启这样的任命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另有深意,卫绾做过太子太傅,与刘彻关系非同一般,而直不疑是出了名的忠厚长者,他在做郎官时,同宿舍有人误拿了别人的金子回家,丢失金子的人以为是直不疑拿的,去指责直不疑,直不疑也不辩解,拿出自己的金子给了失主。等到同舍的人回来将金子送还时,失主非常惭愧。后来有人告直不疑勾搭嫂子,直不疑只回了一句,我没有兄长。除此之外,再也不多说什么。
刘启作出这两项任命后,又想起了早已免职的老熟人周亚夫。他想了个主意试探下这位昔日的功臣,便下旨传唤周亚夫前来宫中赴宴。周亚夫很快奉诏前来,刘启命人将酒食抬了出来。周亚夫受宠惊,但仔细过目之后,周亚夫就迷糊了。
酒桌上除了酒没有筷子,有一块大肉,却没有可以切肉的餐具。宴席中顿时散发出一阵诡异的氛围。
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周亚夫在心里犯嘀咕。
刘启装作无其事的说道,“吃!”
周亚夫对着边上的侍厨说道:“去取筷子。”
侍厨的反应是没反应。
刘启笑道,“还不满意么?”
周亚夫马上面红耳赤,向刘启下拜,刘启说道,“起来吧。”但在众人的惊愕中,周亚夫起来后,也不回宴席,直接就出了宫门。
刘启看着周亚夫的背影,喃喃说道,此人怏怏,非少主臣。这次宴席,其实是刘启最后一次试探周亚夫,但是周亚夫实在令刘启失望,也是从那一刻起,刘启决定彻底抛弃昔日的功臣。
同年,周亚夫经历了他父亲同样的痛苦,进牢房,不一样的是他父亲熬了过去,而他没有。
周亚夫的儿子为他买了五百具盔甲,准备父亲百年之后作为葬器用,因为工钱问题,周亚夫儿子与雇工发生了经济纠纷。雇工一怒之下,把周亚夫儿子告到了官府,告他私自购买兵器,意图谋反。
事情牵连到周亚夫,廷尉传唤周亚夫,周亚夫也是一头雾水,与廷尉问的风马牛不相及,廷尉将事情报告给了刘启,刘启勃然大怒,下旨严查。
为了得到周亚夫的罪状,廷尉再次传唤周亚夫,问道:“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我儿子买的都是葬品,怎么说是谋反?”周亚夫话音一落,廷尉就说出了让周亚夫吐血的一句话,“恐怕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在地下谋反吧!”
面对这种无理的诬陷,周亚夫只能无言以对。他被关在了廷尉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绝食。
在绝食五天之后,一代名将周亚夫呕血而死。我们在为名将周亚夫的屈死扼腕痛惜的时候,景帝刘启也提早跨入了风烛残年的岁月。
他才四十几岁,却已是垂垂老矣,皱纹爬满了脸庞,干瘦的身体已渐渐地失去了活力,一眼望去,活脱脱像一个行将入木的老头,只剩下喘气的劲了。
十七年的高强度工作耗尽了他的健康,透支了他的身体,作为最有权力的人,他可以选择享受,选择挥霍,可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勤奋努力的工作,即便没有人会给他颁发劳模的奖章,他也无怨无悔。十几年来,他为祖宗留下的万里河山耗尽了心力。他犯过不少错,他急躁,他疑心,他像他的祖父刘邦一样,炮制了不少的悲剧,他甚至不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但他仍然是一个好皇帝。
无可否认,大汉的江山在他的手上真正的富庶起来了。国库里堆满了钱粮,穿钱的绳子烂了,太仓粮食溢出来发霉。街巷繁华,田间地头,骏马牛羊成群。那时真是个好光景,家家富余,人人以犯法为耻。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盛世。刘启做到了,他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把大汉江山带向了更高点。用皇帝职业的行话来说,刘启已然无愧于祖宗社稷,无愧于天下万民。刘启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明白时日无多,但他仍然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从他登基到现在,匈奴边患这件事一直挂在他的心头,然而他一直隐忍不发,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彻底清除这个北方的凶蛮对手。
然而他已经做不到了。
他所做的只能是祈祷匈奴人能在他最后的日子不要再杀戮他的子民,不过匈奴人没有给他面子,在他疾病缠身之时,边境再一次传来了噩耗。
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三月,匈奴军队长驱直入雁门,雁门太守冯敬战死,吏民财货损失无数。失败的战报让刘启本已病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气得躺在卧榻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能找来稚气未脱的太子刘彻,再一次提醒他将来要痛击匈奴这个虎狼部族。
他已无力亲自发动一场战争来要回大汉的光荣,唯一的安慰只有太子眼神中的那种坚定了。刘启还是做了积极的准备,他下令各郡调派车骑,材官屯守雁门。同月,又下令内郡不得食用马粮,由官府统一收购,目的是为了边郡储藏战略物资。刘启就是这样带病坚持工作的,而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带到了死亡边缘。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刘启预感到了最后的时刻的来临,他召集了该召集的所有人,开始了最后的告别。
他要向这个为之奉献一切的帝国告别了,他要向这个由自己一手缔造的时代告别了。虽然有诸多遗憾,诸多不舍,但是他还是很欣慰的。他相信眼前的这个儿子一定能完成他的遗命,各位臣工一定都能继续克尽职守,守住大汉帝国的每一片疆土。当得到刘彻和大臣们坚定的回答时,刘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只见他安详的遗容中带着微笑。
在刘启的生命中,风浪不断,他失去过恩师,失去过妻子,也失去过儿子,也失去了臂膀,他的母亲和弟弟时常给他制造麻烦和痛苦。然而,他依然走过来了,从风浪中走过来的刘启成了一个勇于担当的人。
当我们想念起刘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他与他的父亲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文景盛世。
(本章完)
第255章 发诏征贤卫绾丢官()
送别刘启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一幕。
窦太后与他的儿子这辈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这一刻,哭得最伤心的还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这一刻,她不是太后,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永远失去儿子的可怜母亲。
年少的刘彻站在祖母的旁边,看着祖母伤心欲绝的样子,他有丝不忍,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劝慰。有些时候,宣泄的眼泪往往任何的话语更加给力。
躺在棺樽里的人同样是他的至亲。刘彻能感觉到,他的父亲能够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于自己。那笑容,包含着期待,也包含着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刘启,十六岁的少年刘彻继位为帝,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要说汉武时代,得先从年号开始说起。
年号这玩艺儿,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发明,而他的发明人便是刘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年号是给纪年取个名字。刘彻在公元前113年创立年号,他的初衷是不仅要给这个时代烙上强烈的印记,更要避免父辈们那种简单的纪年办法。以前的帝王纪年帝号或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在庙里的灵位,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号可以理解为谥号,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来,帝号和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能议定的。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试想假如你是文帝时代的人,你要写一封信给别人,洋洋洒洒热情洋溢写了一大篇,最后需要表明一下时间了,放在有年号的年代,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那时代没年号,那就得犯难了,总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笔这样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后你的人头也得跟着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没翘辫子,你就给他定了个庙号,到头来不但庙号不成立,你自己得进庙里了。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显然不能直呼其名,不避讳也是严重的犯罪。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文化的人可能会用天干地支,或者大汉某某年,没文化的就干脆不写,收信的人自个儿去琢磨吧。由此看来,没有年号确实麻烦。
汉文帝时,为了方便,刘恒使用前元,后元来纪年。而到景帝时,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后元来纪年。
如今,刘彻认为自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强体壮,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应该没有问题。仅用前中后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纪年办法无法反映国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实在不像话。
刘彻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历史中,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奉正朔”,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
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求变。
他的一生都在求变,在攻击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当然,在赞扬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
他下令,各级官员,列侯,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敢于直谏的人。
一道诏令,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
那段时间,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无论乘快马的,还是坐牛车的,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
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
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前者没有常制,举行与否全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隔年举行,以旧换新。
因此,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甭管是开铺子的,摆摊的,卖包子的,卖菜的,挣完钱之后,还能受到文人士子们的礼敬,怎么说也是一件快事!
不过,这么多文人士子,却让主管征召的大臣们犯了愁。这么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说一句话,也得个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觉。这可不行。大臣们出于对皇帝身心健康的考虑,还是决定先筛选一番。于是,几经筛选下来,最终留下的只剩下百余人。
剩下的这些人获得了与刘彻见面的机会,用较官方的术语来说,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问策。刘彻将这百余人一一召见,亲自与其讨论治国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还要写一篇文章,展示笔头上的功夫。
这么一来,又一批才疏学浅,走门路托关系进来的被淘汰掉了。刘彻虽然年少,但凭借着非凡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对于各种经书子集即便不能说有多深造诣,早已是烂熟于胸,张口即来。
所以,要在刘彻的面前混过去,难度极大,大部分的参加策问的人用事实证明寄希望于糊涂考糊涂,结果只能是自己一塌糊涂。
刘彻很快获得了回报,还是从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我们先来认识董仲舒,这位思想界的教父级人物。
董仲舒,广川郡人,景帝时任博士,因为学的是儒学,混得不好,他只能继续专心治学,学问日益精进,在很多学子眼中,俨然已是一代宗师。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应召,参加策问,并洋洋洒洒地写下让刘彻惊为文的文章。董仲舒的这篇文,不在于文笔,而在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