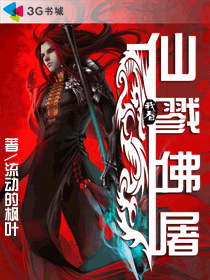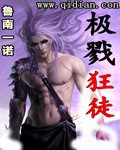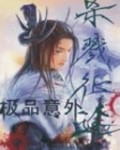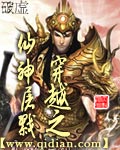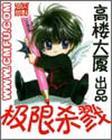秦汉戮-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此,姚贾告辞。”
“不送了。足下慎之慎之。”
匆匆走出典邦苑,姚贾驱车直奔丞相署,李斯却不在行辕了。
李斯欲会赵高,赵高欲会李斯,两人终于在望夷台下相遇了。
望夷台者,甘泉宫十一台之一也。咸阳北阪原有望夷宫,取意北望匈奴日日警觉之意。甘泉宫既为对匈奴作战而设,自然也有了一座望夷台。这座高台建造在一座最大山泉洞窟的对面孤峰之上,高高耸立犹如战阵中云车望楼。登上望夷台顶端,整个甘泉山俯瞰无遗,那条壮阔的直道展开在眼前,如巨龙飞出苍翠的大山直向天际。
李斯与赵高在台下不期相遇时,两人都有瞬间的尴尬。赵高指着那道巨大的瀑布说,要找丞相禀报陛下安卧所在,好让丞相安心。李斯打量着望夷台说,要向赵高知会发丧日期,好让中车府令预为准备。立即,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两人都说望夷台说话最好。及至登上巍巍高台,残阳晚霞之下遥望巨龙直道壮美山川,两人却都一时无话了。
“丞相,但有直道,驷马王车一日可抵九原。”
“中车府令驭车有术,老夫尽知。”李斯淡漠地点头。
“丞相又带剑了?”赵高目光殷殷。
“此剑乃陛下亲赐,去奸除佞。”李斯威严地按着长剑。
“这支金丝马鞭,亦陛下亲赐,在下不敢离身。”
“足下与老夫既同受陛下知遇之恩,便当同心协力。”
“丞相与陛下共创大业,在下万不敢相比!”赵高很是惶恐。
“发丧之期将到,老夫欲会同大臣,开启遗诏。”李斯切入了正题。
“在下一言,尚请丞相见谅。”赵高谦卑地深深一躬。
“你且说来。”
“在下之意,丞相宜先开遗诏,预为国谋。”
“中车府令何意,欲陷老夫于不法?”
“丞相见谅!”赵高又是深深一躬,“沙丘宫之夜,丞相原本可会同随行大臣,当即开启遗诏。然,其时丞相未曾动议,足见丞相谋国深思。在下据实论事:陛下遗诏未尝写就,说是残诏断句,亦不为过;既是残诏,便会语焉不详,多生歧义;若依常法骤然发出,朝野生乱,亦未可知。为此,在下敢请丞相三思。”
“也是一说。”李斯淡淡点头。
“丞相肩负定国大任,幸勿以物议人言虑也!”赵高语带哽咽再次恳请。
“也好。但依中车府令。”思忖片刻,李斯终于点头了。
“丞相明断!”赵高一抹泪水扑倒在地,咚咚叩首。
瞬息之间,李斯大感尊严与欣慰。
山月初上时分,赵高将李斯领进了一座守护森严的山洞。赵高说,这便是甘泉宫的符玺事所。李斯曾久为秦王长史,也曾亲掌秦王符玺。其时,天下所谓“李斯用事”,一则是指李斯谋划长策秦王计无不用,二则便是指李斯执掌秦王书房政务并符玺事所。符玺者,兵符印玺也。符玺事所者,昔日秦王兵符印鉴,今日皇帝兵符印玺之存放密室也。任何兵力调动,都得从这里由君王颁发兵符;任何王书诏书发出,都得从这里加盖印玺。是故,符玺事所历来是皇室命脉所在,是最为机密的重地。饶是如此,李斯却没有在这甘泉宫住过,更没有进出过甘泉宫的符玺事所,不知这甘泉宫符玺事所竟设在如此坚固深邃的洞窟之中,心头委实有几分惊讶。
“天字一号铜箱。”一进洞窟,赵高吩咐了一声。
洞壁两侧虽有油灯,两名白发书吏还是举着火把,从洞窟深处抬出了一只带印白帛封口的沉重的铜箱。铜箱在中央石案前摆好,赵高从腰间皮盒掏出了一把铜钥匙,恭敬地双手捧给了李斯。虽未进过这甘泉宫石窟的符玺事所,然李斯对王室皇室的符玺封存格式还是再熟悉不过,瞄得一眼,便知这是极少启用的至密金匮。古人所谓的周公金匮藏书,便是此等白帛封存的大铜箱(匮)。依照法度,此等金匮非皇帝亲临,或大臣奉皇帝诏书,任何人不得开启。
今日,赵高将始皇帝遗诏封存于如此金匮,李斯立即看透了赵高心思:任何人都无论如何不能说赵高做得不对,然任何人也都无法开启此匮,除非赵高愿意听命;因为,皇帝不在了,任何人都不会有皇帝诏书,而赵高却可以任意说出皇帝如何遗嘱此匮开启之法,可以任意拒绝自己想拒绝的任何人开启金匮。
当然,赵高若想拒绝李斯,只怕李斯会同大臣议决开启遗诏,也得大费一番周折。当此情势,赵高自请李斯开启金匮,且拱手将钥匙奉送,宁非天意哉!李斯清楚地知道,纵然大臣奉诏而来,打开金匮还得符玺事所之执掌官员。因为,此等金匮有十余种锁法开法,任谁也难以准确地预知目下金匮是何种开法。执掌吏员捧上钥匙,乃皇帝亲临的一种最高礼仪而已,并非要皇帝亲自开启。而今,赵高对自己已经表示了最高的敬奉,李斯足矣!
“中车府令兼领符玺,有劳了。”李斯破例地一拱手。
“在下愿为丞相效劳。”赵高最充分地表现出内廷下属的恭敬。
小心翼翼地撕开了盖着皇帝印玺的两道白帛,小心翼翼地反复旋转钥匙打开了金匮,又小心翼翼地拿去了三层丝锦铜板,好容易显出了一方黑亮亮的木匣,赵高这才对李斯肃然一躬:“丞相起诏。”李斯熟知此中关节,对着金匮深深一躬,长长一声吟诵:“臣李斯起诏——!”双手恭敬地伸入金匮,捧起黑亮亮木匣出了金匮,放置到了金匮旁的石案上,又对赵高一拱手:“烦请中车府令代劳。”赵高上前对黑匣深深一躬,啪地一掌打上木匣,厚厚的木盖便“嘭”的一声弹开。赵高又对李斯一拱手:“丞相启诏。”李斯明白,这个“启”不同于那个“起”,立即一步上前,一眼瞄去,心头悚然一惊——一卷渗透着斑斑血迹的羊皮纸静静地蜷伏着,弥漫出二片肃杀之气!
“陛下!老臣来也……”李斯陡然哽咽了。
“丞相秉承陛下遗愿,启诏无愧!”赵高赳赳高声。
电光石火之间,李斯的精神转换了,李斯不再是未奉顾命的大臣,李斯变成了谋划长策而从来与始皇帝同道同心的帝国栋梁。如此李斯,启诏何愧哉!心思飞动间,李斯捧出了那卷血迹斑斑的羊皮纸,簌簌展开在眼前——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陛下——!”李斯痛彻心脾地长哭一声,颓然软倒在冰凉的石板上。
读书可以感悟人生,这个人生可以是自己的人生,可以是历史的沧桑。
(本章完)
第31章 改诏立胡为新皇()
倏忽醒来,望着摇曳的灯光,李斯恍惚若在梦中:“这是何处?老夫如何,如何不在行辕?”
旁边一个身影立即凑了过来,殷切低声道:“丞相,在下私请丞相入符玺事所。丞相无断,在下不敢送回丞相。”
刹那之间一个激灵,李斯的神志恢复了。李斯双手一撑霍然坐起道:“赵高,屏退左右。”
赵高一声答应,偌大的洞窟顿时没有了人声。李斯从军榻起身站地,这才看见洞窟中已经安置好了长谈的所有必备之物。石案上饭食具备,除了没有酒,该有的全都有了;石案两厢各有坐席,坐席旁连浸在铜盆清水中的面巾都备好了。李斯一句话没说,刚要抬步走过去,赵高已经绞好面巾双手递了过来。李斯接过冰凉的面巾狠狠在脸上揉搓了一番,一把将面巾摔进了铜盆,板着脸道:“中车府令何以教李斯?说。”
赵高肃然一躬道:“丞相错解矣!原是赵高宁担风险而就教丞相,焉有赵高胁迫丞相之理?赵高纵无长策大谋,亦知陛下之大业延续在于丞相。赵高唯求丞相指点,岂有他哉!”
“中车府令,难矣哉!”良久默然,李斯长叹了一声。
“敢问丞相,难在何处?”
“遗诏语焉不明,更未涉及大政长策……”李斯艰难地沉吟着,“再说,此诏显是陛下草诏,只写下了最要紧的事,也还没写完……老夫久为长史,熟知陛下草诏惯例:寻常只写下最当紧的话,然后交由老夫或相关大臣增补修式,定为完整诏书,而后印鉴发出。如此草诏断句,更兼尚是残诏,连受诏之人也未写明……”
“丞相是说,此等诏书不宜发出?”
“中车府令揣测过分,老夫并无此意!”
“丞相,在下以为不然。”沉默一阵,赵高突然开口了。
“愿闻高见。”李斯很是冷漠。
“如此草诏残诏,尽可以完整诏书代之。”赵高的目光炯炯发亮,“毕竟,陛下从未发出过无程式的半截诏书。更有一处,这道残诏无人知晓。沙丘宫之夜风雨大作时,在下将此残诏连同皇帝符玺,曾交少皇子胡亥看护,直到甘泉宫才归了符玺事所。如此,在下以为:皇帝遗诏如何,定于丞相与赵高之口耳。丞相以为如何?”
“赵高安得亡国之言!非人臣所当议也!”李斯勃然变色。
“丞相之言,何其可笑也。”
“正道谋国,有何可笑!”李斯声色俱厉。
“丞相既为大厦栋梁,当此危难之际,不思一力撑持大局,不思弘扬陛下法治大业,却径自迂阔于成规,赵高齿冷也!早知丞相若此,在下何须将丞相请进这符玺事所,何须背负这私启遗诏的灭族大罪?”
“赵高!你欲老夫同罪?”李斯愕然了。
“丞相不纳良言,赵高只有谋划自家退路,无涉丞相。”
“你且说来。”李斯一阵思忖,终于点头了。
“洞外明月在天!赵高欲与丞相协力,定国弘法,岂有他哉!”
“如何定国?如何弘法?方略。”
“丞相明察!”赵高一拱手赳赳高声,“始皇帝陛下已去,然始皇帝陛下开创的大政法治不能去!当今大局之要,是使陛下身后的大秦天下不偏离法治,不偏离陛下与丞相数十年心血浇铸之治国大道!否则,天下便会大乱,山东诸侯便会复辟,一统大秦便会付之东流!唯其如此,拥立二世新帝之根基只有一则:推崇法治,奉行法治!举凡对法治大道疑虑者,举凡对陛下反复辟之长策疑虑者,不能登上二世帝座!”
“中车府令一介内侍,竟有如此见识?”李斯有些惊讶了。
“内侍?”赵高冷冷一笑,“丞相幸勿忘记,赵高也是精通律令的大员之一。否则,陛下何以使赵高为少皇子之师?赵高也是天下大书家之一,否则,何以与丞相同作范书秦篆?最为根本者,丞相幸勿相忘:赵高自幼追随皇帝数十年,出生入死,屡救皇帝于危难之中。丞相平心而论,若非始皇帝陛下有意抑制近臣,论功劳才具,赵高何止做到中车府令这般小小职司?说到底,赵高是凭功劳才具,才在雄迈千古的始皇帝面前坚实立足也!功业立身,赵高与丞相一样!”一席话酣畅淋漓,大有久受压抑后的扬眉之象。
“中车府令功劳才具,老夫素无非议。”李斯很淡漠。
“丞相正眼相待,高必粉身以报!”
“大道之言,中车府令并未说完。”李斯淡淡提醒。
“大道之要,首在丞相不失位。丞相不失位,则法治大道存!”
“老夫几曾有过失位之忧?”
“大势至明,丞相犹口不应心,悲矣哉!”赵高嘭嘭叩着石案,“若按皇帝遗诏,必是扶苏称帝。扶苏称帝,必是蒙恬为相。赵高敢问:其一,丞相与蒙恬,功劳孰大?”
“蒙恬内固国本,外驱胡患,兼筹长策,功过老夫。”
“其二,无怨于天下,丞相孰与蒙恬?”
“政道怨声,尽归老夫,何能与天下尽呼蒙公相比。”
“其三,天赋才具,丞相孰与蒙恬?”
“兵政艺工学诸业,蒙恬兼备,老夫不如。”
“其四,得扶苏之心,丞相孰与蒙恬?”
“蒙恬扶苏,亦师亦友,老夫不能比。”
“其五,谋远不失,丞相孰与蒙恬?”
“不如……足下责之何深也!”李斯有些不耐了。
“以此论之,蒙恬必代丞相总领国政,丞相安得不失位哉!”
“也是一说。”默然有顷,李斯点了点头。
“更有甚者,扶苏即位,丞相必有灭族之祸。”
“赵高!岂有此理!”李斯愤然拍案。
“丞相无须气恼,且听在下肺腑之言。”赵高深深一躬,殷殷看着李斯痛切言道,“始皇帝陛下千古伟业,然也有****之名。若扶苏蒙恬当国,为息民怨,必得为始皇帝****开脱。这只替罪羊,会是何人?自然,只能是丞相了。丞相且自思忖:天下皆知,李斯主行郡县制,开罪于可以封建诸侯之贵胄功臣;李斯主张焚书,开罪于华夏文明;李斯主张坑儒,开罪于天下儒生;而举凡刑杀大政,丞相莫不预为谋划,可说件件皆是丞相首倡。如此,天下凡恨秦政者,必先恨丞相也。其时,扶苏蒙恬杀丞相以谢天下,朝野必拍手称快。以蒙恬之谋略深远,以扶苏之顺乎民意,焉能不如此作为哉!”
“大道尽忠,夫复何憾?”李斯的额头渗出了晶亮的汗珠。
“丞相何其迂阔也!”赵高痛彻心脾,“那时只怕是千夫所指,国人唾骂。普天之下,谁会认丞相作忠臣,谁会认丞相为国士?”
“中车府令明言!意欲老夫如何?”突然地,李斯辞色强硬了。
“先发制人。”赵高淡淡四个字。
“请道其详。”
“改定遗诏,拥立少皇子胡亥为帝。”
“胡,胡亥?做,二世皇帝?”李斯惊得张口结舌了。
“丞相唯知扶苏,不知胡亥也。”赵高正色道,“虽然,少皇子胡亥曾被皇室选定与丞相幼女婚配。然在下明白,丞相很是淡漠。根本因由,在于丞相之公主儿媳们对胡亥多有微词,而丞相信以为真也。在下就实而论,少皇子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拙于口,尽礼敬士;始皇帝之诸子,未有及胡亥者也。胡亥,可以为嗣,可以继位。恳请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