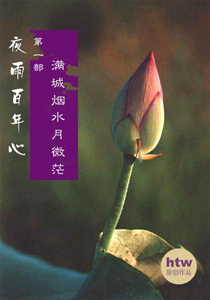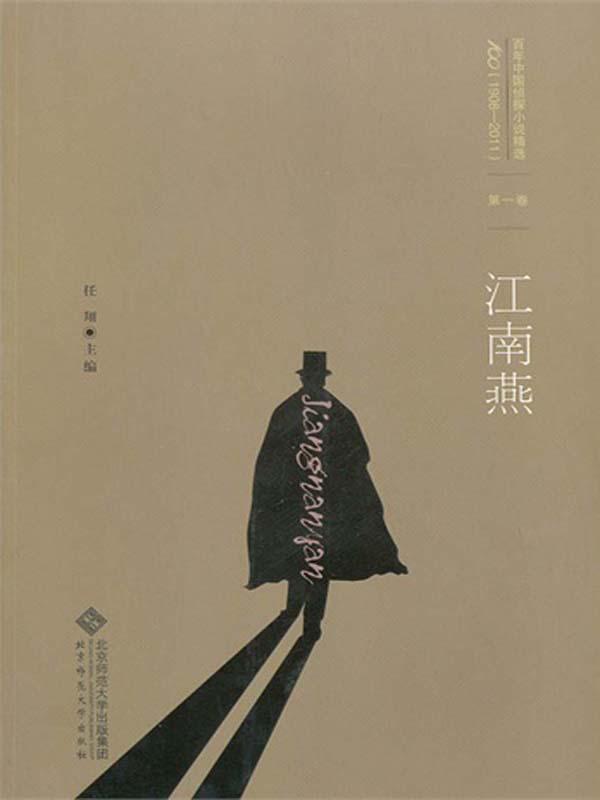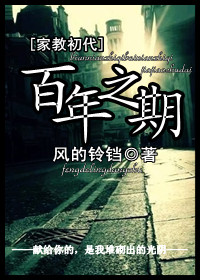百年功罪-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象”;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被敌国军队生俘;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分,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著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馀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最后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著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奸的“机制”。此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的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著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经过反覆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后唐,建后晋称帝。为了达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儿皇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矣,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于破裂,耶律德光大举进兵,灭后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其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馀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