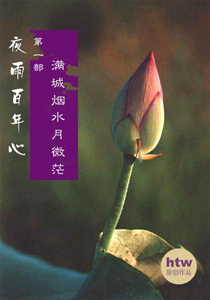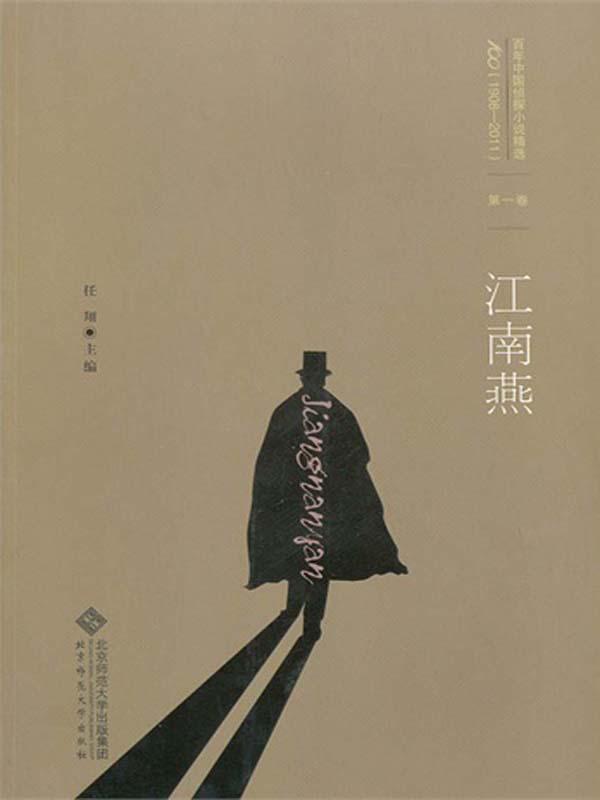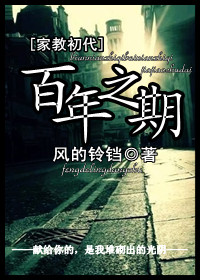百年功罪-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个翻译官。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藉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
周作人出任伪职,固然不光彩,但绝不是一种罪行。他在侵略军的威逼之下就范(包括枪击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职,没干过对不起民族的坏事。据曾在北平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替他争来的。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一个叫缪斌的汉奸想争这个位置。缪斌当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党便搜集他平时的反日言论,写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里,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由周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想尽办法抵制了缪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优秀的作家推进了“汉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谈之中,常流露出对日寇侵略中国、以致民不聊生、生灵遭受涂炭的不满情绪,还赞许和同情抗日分子,帮助地下组织在日占区安插人员(回忆文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这一切“比缪斌好得多”的事,后来都被一笔勾销,只剩下永生难赎的罪名。即使是被号称“最抗日”的共产党指责、孤立和打击的“最反动”的汉奸缪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时”有很多的“反日言论”,足以“写成材料”让日本人罢了他的官。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次大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一九四一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一九四二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九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一九四○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十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著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著纳粹的“”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一是几个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这期间绝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地位,以及横扫日本棋坛十五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乐家马思骢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战争怎么打了八年?就因为汉奸太多了。”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五十几年,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清朝丢失的领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全部、乌苏里江以东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还有它征服的蒙古、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结算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就会发现,它给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中国丢失的土地多得多一个王朝倾塌了。这个世纪一开局,它就呈现一派行将崩溃的败相: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赔款求和,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革命党接二连三发动起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驾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岁小皇帝宣统这一对“孤儿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捻回之乱、中法安南之战及中日甲午战争以後,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只等最後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降临了。事实上,它能够硬撑著拖一副迟滞的脚步,走到这个使人类社会发展最快、改观也最大的二十世纪来,而且竟还摇摇晃晃地继续走了十来年,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全部罪责由末代王朝承担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结局中,清王朝的结局是最为幸运的。虽说是一场革命,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征战;虽说搞了点宫廷政变,却也没有大动刀兵,闹到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虽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後却也咸与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的完整,没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辙。退位的皇帝还享受极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尊号不废,仍居宫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贴四百万元,王宫世爵“概仍其旧”。直到辫帅张勋进京唱了一出复辟的戏,才被日後的冯玉祥作为藉口,派兵把逊帝从故宫大院里赶了出来。谁教你先输了理,听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几天的回头草呢。不过也没拿他怎麽样,赶是赶出来了,房地产带不走,细软可是尽他扛。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国”的匾额从历史舞台上摘下来,已经十三年了。
然而中国人对於清朝,多半没有什麽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国上千年封建专制的帐,似乎都要记到它头上。就象任何一个朝代的全部罪恶,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来承担一样。它不但为後人提供了旧制度最直观的、令人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甚至还要为民国以後的许多糗事负责:窃国大盗袁世凯专权,军阀混战,列强继续欺侮压迫中国,贫穷、落後、愚昧……所有的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个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赔款,镇压变法,一次次阻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崇高国际威望的中国,沦为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样的政权没什麽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影响中国历史甚剧、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残酷争斗几十年的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假设当年不用革命……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於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就不会有後来的军阀混战,不会有列强扩展和强化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围,不会有国民党、共产党先後坐大的一党专政,不会有残酷无情的清党、内战和阶级斗争,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麽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大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这个世纪的最後十年再拿出来论战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总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则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变法、六四)要好。其实,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设历史。
革命不能保证推翻独裁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於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四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後来发生的革命相比。至於六四,牵涉到许多另外层面的问题,拟另写专文中再作讨论。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後连空话也不要了,乾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说穿了也就是独裁。一个政治家,同时受到两大相互敌对、都以擅长专制独裁闻名於世的政党崇敬和拥护,他本人会不独裁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怀疑。孙中山在他自己的党内排斥异己,大事一个人说了算;号召党员向他宣誓效忠,以党龄的长短封官许愿;对外推崇师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列宁,一心想走俄国的道路;……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於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独裁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独裁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份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好皇朝只有汉、唐、清
中国自秦始,建立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学家们称得上好一点的皇朝,却少得可怜。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