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这样,张保皋和郑年分道扬镳了,一人从商,一人继续留在军营中。”
王靖顿了一下,杜牧也暂时放下了笔。他一直在仔细倾听,间或在纸上做做记录。杯子里的酒已经喝干了,王靖重新续满,推到杜牧面前,杜牧接过来,慢慢地啜着。
“倘若张大使不弃武经商,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且,要是没有张大使,我的生意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兴隆啊。我在扬州收购波斯国及大食国商人手中的货物,然后通过张大使的船队贩卖到新罗,甚至远销到日本,同时又将两国的特产品回销到波斯国、占婆国等地。张大使在离开军旅之初,一方面将在唐朝的新罗人联系到一起,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另一方面建立了名为赤山法华院的新罗式寺庙,统一了在唐新罗人的信仰。张大使这些做法也许是早年他讨伐藩镇时向对手学来的吧,不管怎么样,他从军队出来仅仅六年,便成为全唐朝谁也不敢小瞧的大商人了。”
“后来张保皋怎么样了?”
杜牧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问道。他一直在不停地喝,所有的酒瓶子都空了,脸也成了枣红色,但是眼睛还炯炯有神。
“我刚才已经提起过,张大使六年前,也就是大和二年(公元828年)离开唐朝,回到新罗。兴德大王任他为大使,镇守清海藩镇。”
“这么说大使这一官衔相当于节度使?”
听到杜牧发问,王靖回答:“可以那么说。自从设立清海藩镇以来,张保皋大使率大军彻底消灭了一度在海上猖獗的海盗们,海上不法奴隶买卖也被根绝。海上现在一片和平景象,各种贸易船只繁忙地穿梭往来其上,不少人都称呼张大使为海上王呢。”
“那么。”杜牧好像有点心急,停了笔,望着王靖的脸问道,“另外一个人,郑年,他怎么样了?”
杜牧不愧思维敏捷。
对这个问题,王靖边摇头边说:“后来郑年怎么样了,我不太清楚。很久没听说过他的行踪了,估计可能还在军队中吧。不过,如果在军队中由军中小将升任总官,这个消息一定会在所有新罗人中传开的,可是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应该还在原位吧。大人若是真想了解郑年后来的情况,我倒有一个办法。”
“噢?是什么办法?”
王靖答道:“离扬州不远有一个地方叫连水乡。那儿的戍将名叫冯元规,他与郑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人如果去找他,一定能够详细地了解到郑年后来的状况。”
王靖提到的冯元规是当时泗州连水乡的镇将,他当年在武宁军中时便与张保皋、郑年私交甚密。后来,他从武宁军退役,回到他的故乡连水乡,成为官职六品的戍将。
如此说来,王靖的主意没错,可以说冯元规是现在最了解郑年的人了。事实上,当时郑年和冯元规经常见面。杜牧后来有所描述,那时郑年便在连水乡,他被武宁军驱逐,已经穷困潦倒。
其实早在郑年与张保皋分别之时,张保皋便劝过他可能会被强制退役。后来的情况果如其言,没了官职的郑年选择了到连水乡落脚,因为武宁军时的亲密朋友冯元规是那儿的戍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那儿是新罗人聚集的地方。
连水乡距楚州三十五公里,位于古淮河河口的北岸,经运河可以直达大海,是河运和海运的要冲。郑年当时便住在那里。
然而,尽管有王靖如此热心的介绍,杜牧还是未能前往连水乡找冯元规。于是,有关对张保皋和郑年事迹的寻访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此时杜牧突然结束了两年多的扬州生活,调往长安任监察御使。
离开时的杜牧,已扬州梦醒,如他当时写的一首《遣怀》诗所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所谓“十年”,其实是诗人杜牧特有的表达方法,是他对在扬州的两年多岁月的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杜牧在有生之年曾两度来到扬州,总共停留约三年时间。第二次是时隔两年之后,他故地重游,逗留了一年多。
杜牧重回扬州,是为了他的弟弟杜毅。那时的杜毅已进士及第后入仕,任直使馆,却不幸患了眼疾,成了看不见的瞎子,在扬州禅智寺疗养。其遗址迄今犹在。
爱弟心切的杜牧,在洛阳请了著名的眼科大夫,不远万里,一路陪同,到扬州为他的弟弟看病。
历史往往是那么机缘巧合,如果杜牧的胞弟没有患眼病,没有在扬州的禅智寺疗养,杜牧大概不会再来扬州。若是这样,杜牧的《樊川文集》中可能就不会有张保皋和郑年列传。
按着王靖的指点,到连水乡找冯元规便是他二度到扬州时的事。而此时,杜牧要暂别扬州了。
离开扬州,最割舍不下的人是豆蔻花。
那位令杜牧诗出妙语、美丽至极而“娉娉袅袅”的豆蔻花,那位只有十三四岁,如二月枝头盛开着的豆蔻花般的女人。“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如今要和她分别了,这是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痛啊。
七月的扬州,离别的季节。
红药桥边的青楼中,杜牧最后一晚和豆蔻花举杯共饮。窗外的夜景醉人,诗人张祜有诗赞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如果说张祜在扬州看到了神仙,那么天才诗人杜牧在扬州则做了一场白日梦。而今一旦天亮离开扬州,便将和豆蔻花永远地分别。
不仅是要告别豆蔻花,还要永远地告别蔷薇伴酒的日日夜夜。
似乎是体谅杜牧此时此刻的心情,夜阑青楼外边的桥上,呜呜咽咽地传来了凄婉的洞箫声,不知是谁在幽怨;晨光曦微,烛影阑珊之时,烛泪涟涟。
最后一次与豆蔻花的对饮,酒不醉人人已醉。醉了的杜牧突然抬起头来,问豆蔻花:
“含态花呀,离开了你我到哪儿再找到如此醉人的醇香啊?”
豆蔻花答:“大人有去必有回,小女子不管何时都在等着大人。”
然而杜牧心若明镜。
一旦天亮告别扬州,他将不能再见豆蔻花。
于是杜牧起身,展开豆蔻花穿过的裙子,即兴挥毫赋诗。就在这条豆蔻花常穿的绸裙上,留下了杜牧情深意切的离别诗篇,诗云:
多情却是总无情,
惟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第二天天一亮,杜牧告别了扬州,此时陪杜牧一起离开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正如后来宋朝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里描述的那样,杜牧已被牛奇章说服,离开时与两年前初到扬州赴任时已判若两人。
杜牧的儿子叫杜荀鹤,当时已有十多岁。据说,那时在垂柳掩映的运河中,杜牧突然掏出怀中一直伴随着他的酒杯,用力扔出,笑着对儿子发誓:“儿呀,为父再也不喝酒了。”
不过,杜牧并没有遵守对儿子的承诺,他一生都以酒为伴。因此杜荀鹤也无从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在年幼的自己面前,许下了兑现不了的诺言。父亲从桥上将酒杯扔到江里,发誓再不喝酒,不是要戒酒,而是要决心告别过去放荡的生活,领悟到这些,他已从一个父亲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
后来,唐朝受到黄巢起义的致命打击,国运日暮途穷之际,杜荀鹤有一首诗,《夏日题悟空上人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在连年战乱中,人们以超脱世俗,参禅悟道,来忘却现实的痛苦。诗中有云:“灭得心中火自凉”。意思是,心中如果没有杂念,大火自然便会凉下来。
据传,日本传奇武士信玄的菩提寺惠林寺被大火烧毁时,主持快川绍喜岿然不动地在法座之上吟诵道:“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这句禅味甚足的偈子便是出自杜荀鹤之诗。
父亲当年的一掷酒杯,实是要抛却心中杂念。杜荀鹤长大成人之后,才能慢慢体会出此意吧。
不管怎么说,杜牧暂时离开了扬州,有关张保皋和郑年事迹的探寻,暂告一段落。
但那之后两年,即开城二年,公元837年,杜牧又回到扬州来了,他的弟弟杜毅因患眼疾到扬州疗养,杜牧请来当代最有名的医生,到扬州为他弟弟看病。
《樊川文集》第十六卷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情况。杜牧第二次到扬州来,终于使未完成的张保皋和郑年事迹的探寻得以继续。
杜牧按着第一次访问时新罗商人王靖的介绍,亲自到连水乡来找冯元规。通过冯元规,杜牧了解了张保皋和郑年的后续情况,最终在《樊川文集》中完成了张保皋和郑年列传。
他还到九曲桥边的青楼里找过豆蔻花,但伊人早已不知去向。杜牧心中凄楚难过,岁月竟如此无常,叹息之余,一首传世之作由此而生。
这是一首吟诵弟弟所在的禅智寺的诗,题为《扬州禅智寺》,诗中杜牧的心情一览无遗: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
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诗中的竹西路是指扬州东边的大街,不知杜牧听着从夕阳映照下的楼阁中传出的歌声,是不是眼前突然浮现出与我见犹怜的豆蔻花同乐时的一幕一幕。“大人有去必有回,小女子不管何时都在等着大人”,分别时的承诺犹在耳边,然而真是人生无常啊!
不过,杜牧重回扬州毕竟完成了张保皋和郑年列传。由此看来,张保皋和杜牧也许是前世有缘吧。
第七章 龙虎相搏
兴德大王十一年,即公元836年秋。
从不远处的芬皇寺传来告知戌时的钟声,戌时过后亥时开始,城里实行宵禁,可是还不见有人从瞻星台上出来。
瞻星台是善德女王时建造的上方下圆形态的建筑物。为了占卜国家兴衰吉凶,专门派驻日官每日驻守在这里,日日夜夜观察星象。接替值守的日官进入瞻星台已良久,但迟迟不见品如出来。
品如曾向上大等金均贞透露东方天空出现败星,预示大王即将驾崩的“天机”。另外,他还通过“太白掩月”之星象,预言天下将出现叛乱。
瞻星台高十九尺五寸,上部周长二十一尺六寸,底座周长三十五尺七寸,专门供人上去观察星象的观象台位于整座高台的中部及上。
这一日入夜后,有一双鹰般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瞻星台。此人全身上下一身黑衣,在漆黑的夜晚,这身装束令人越发不易觉察。
夜空中乌云密布,偶尔有一丝月光透过乌云洒向大地,但转瞬之间又被乌云遮住,大地随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终于,传来一些声音,有一个人从瞻星台上走了下来。黑衣汉子隐身松树后,黑暗中以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他本能地一眼便判断出从瞻星台走出来的人便是日官品如。此时快要到实行宵禁的时间了,只见品如加快脚步,向城门走去。
日官品如不住在城里,栖身于城外南山脚下。
身着黑色夜行衣,乔装打扮的汉子也加快了脚步,若即若离地跟在品如的身后。尽管步履匆匆,却悄无声息,如影相随。
品如是观察星象和日月五行,占卜国家兴衰吉凶的日官。但此时他似乎并未占卜到有刺客已跟在自己身后,准备随时伺机索要他的性命。品如快步走出城门,向南山方向走去。
南山,自古便有金鳌山之称。自从传说新罗始祖朴赫居士诞生之地便是此南山脚下的萝井,这里便成了圣山。尤其是佛教成为国教以来,南山则更成为传说中信徒们瞻仰的天国众佛来到凡间栖息的地方。
品如向都堂山脚下走去。这里有座称为天官寺的寺庙,这座寺庙是金庾信为了祭奠思慕自己的名妓天官而建。这座寺庙的周围,居住着众多低衔官吏,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月亮时隐时现,通向村庄的道路也随之忽明忽暗,品如却轻车熟路,从容地走向村子。
田间传来潺潺流水声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突然,一个声音惊动了田间的秩序,蛙鸣声便瞬间停下来,四周归于一片寂静。
品如终于有所察觉,停下脚步回头张望。一直保持距离跟踪品如的影子亦闪电般伏身隐藏在田间的稻丛中。
“谁?”
品如胆战心惊地对着周围喝了一声。在秋风吹拂下,只听稻穗发出“唰唰”的响声。品如似乎放下心来,继续往前走去。
穿过田间,出现了一片黑黢黢的松林,穿越松林便是有人居住的村子了。品如身后的黑影离品如越来越近,加紧了跟踪的脚步。月光透过乌云照到那个汉子的脸上。身着黑色夜行衣的汉子,脸上戴着一个丑陋、可怕的方相氏面具,仿佛是一个追命夺魂的无常鬼。
只见那个汉子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佩月刀。看来在这片松林下手最适合不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品如再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停下脚步回头。就在品如回头的刹那间,那个汉子已腾空跃上一颗松树,如影如风,无声无息。
“是谁?”
品如转过身,刚走近那个汉子藏身的松树下,刹那间,汉子纵身跃下松树,扑向品如。品如还没有来得及叫喊,汉子的一只手已经紧紧捂住了品如的嘴。
杀手所能赐予的“最大恩惠”便是一刀即取下人的性命,不令其感觉太大的痛苦。汉子一刀刺入品如的胸口,手指间感觉到品如的呼吸逐渐微弱下去,直至停止。
品如作了刀下鬼。品如被自己的预言不幸言中,“一旦泄露天机,一定会没命的”。而上大等金均贞的预言“要是你胆敢到处乱说,小心你的舌头和脖子”,也不幸被言中。
热血如泉喷涌,汉子抽出刀,喃喃自语:“这回再也开不了口了。”
汉子扳开已死的品如的嘴,用刀割下舌头,揣入怀中。
汉子确认了品如已死无疑之后,悄无声息地沿原路返回。大概一团乌云刚刚散去,天地间四处闪着耀眼的月光,如银藏刀般寒光闪闪。
田埂间依然水流潺潺。汉子弯腰清洗沾染了血迹的刀和手。虽然刚杀过人,但他看上去却没有丝毫的自责、不安,连呼吸都平稳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擦洗干净之后,汉子摘下面具,开始洗脸。这时,他才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那是一张极其凶残丑恶的脸,看着便令人不寒而栗。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日官品如送上黄泉之路的正是他——原名阎文的阎长。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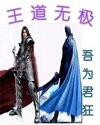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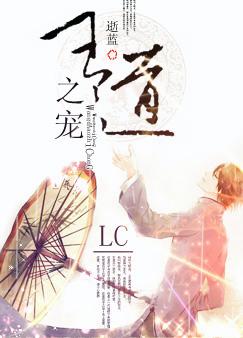
只有你能听见的声音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