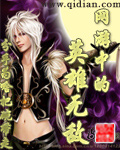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未受歪曲的传播产生于每个(有交际能力的)说话者用推理恢复方式对每一个有效声言的正当性进行严格检验的能力。相反地,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出现于在理想的言语情境的语用准则受制于具有优先地位的旨趣时,从而产生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对有效性声言的虚假的一致意见。在《合法性危机》中,哈贝马斯认为,国家通过把基本上无法检验的有效性声言强加于社会成员而与后者保持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换言之,它用特别的旨趣取代了一般的旨趣。在社会层次,只有基于理性的一致意见的准则才表示一般的旨趣,否则它们就以实力为基础,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在后一情形下,哈贝马斯用“规范权力”来指称由意识形态建构的准则。
因此,一个批判意识形态的社会理论在只是嵌入社会的机构体系的规范权力始于一般旨趣抑制模式时才能识别出它来,并把存在于某一时候的规范结构与假设的由推论形成的体系状态相比较。这样一个与事实违背的、投射的重构……可以由这一问题所引导(据我的观点,这可以为普遍语用学的观点所证明):一个社会体系的成员,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阶段,如果他们能够而且实际上通过推论的意志形成、根据该社会的限制条件和功能要求的适当知识,是怎么以集体方式、在一定的约束下解释其需要(而且哪些准则是他们作为正当准则接受)的呢?(1975,113页)
根据我提出的基本前提之一即,组织文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推论实践产生和再现的,现在让我们检验一下哈贝马斯的推论理性模型在组织情境中的应用。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组织的意识产生和意义形成是由社会成员通过符号过程完成的。但是,一般来说,关于组织文化的著述仅仅止于对某些旨趣通过符号实践的结构形成被证明合法的方式的检验。当交际行动由于某些特别的旨趣强加于某一群体而受到歪曲时,规范权力便存在于一个组织内。
组织形成的批判理论
在把诸如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应用于组织传播的分析时面临的固有问题之一是,在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关于组织形成过程的管理概念之间有着根本的不相容性。例如,有多少经理人员会坦然接受这一观点,即组织旨趣有一种不公正的偏向,支持相当有局限的、由管理层确定的对组织应该如何运作的定义?有多少组织会欣然接受以结构更民主的、参与性的方式进行组织建设的思想?事实是,大多数的组织研究保持着一种明确的以管理为主的方向,但是这与研究人员的意识形态倾向一般没有很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实用的考虑占据上风,例如研究所需的经费常常是由有关组织提供的,或者组织问题是事先由管理层确定的,研究人员被雇用来寻找解决办法。总之,一个显示出对管理层对组织形成的定义持同意态度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接触研究的环境。
除了这一问题以外,对组织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更为使人惊奇的是,这一观点的某些最为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那些从事比较传统的管理项目的人们。可以肯定地说,许多支持组织文化观点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主要把它视为一个新的管理工具(在传统意义上),但也有不少研究人员在运用这一观点时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他们把它视为认识组织形成过程的新方法。
在对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中,福里斯特(Forester,1981,1982)对推论理性可被用于检验组织中政治关系的产生和再现的方式做了调查。福里斯特指出:
这篇论文的观点实际上是,哈见马斯关于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概念可以通过确定其在构成任何社会组织的社会关系的基本传播再现中的位置而得到发展,并在具体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具实践性。这一再现(知识,一致意见,信任和注意的关系)的范围在哈贝马斯对普通交际行为和言语的分析、即他的所谓“普遍语用学”中是基本的概念。(1982,
13页)
福里斯特从组织计划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计划者不仅寻求某些目标,使得组织产生某些结果,而且他们也应该再形成那些最适合组织的目标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从形式的角度说,计划者的目标本质上纯粹是工具性或技术性的。但是,技术判断本身就是由社会规则和习惯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技术的判断之得到尊重和给予合法地位是因为在适当的习惯制度情境中居有一席之地。因此“技术判断可以产生工具性的结果……因为那些拥有熟练技术的和那些需要技术判断的人们的社会作用是由社会和政治所再产生的”(Forester,1982,6页)。但是如哈贝马斯(1970c)指出的,这类技术-理性决定的实践(社会)性质被技术的意识形态特征模糊了。技术判断之合法仅仅因为技术旨趣来自实践旨趣。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颠倒了这一关系,使得实践旨趣似乎是源于技术旨趣。
福里斯特(1981,1982)把哈贝马斯的四个有效性声言稍稍做了些改动,以把它们与组织中的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直接而明确地联系起来。从这一角度出发,组织被视为试图通过知识(真理)、一致意见(正确性)、信任(真实性)和注意(可理解度)的关系而再现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实际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构。这些关系中的每一个都必须予以适当的控制以保证组织内外某些权力结构的再现。
例如,公司必须经常对代表自身的公共形象予以仔细监控。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可能希望对某些或许与突出的公司形象不太吻合的组织特征进行掩盖。这主要通过对信息的流通采取控制来实现,后者支配着组织内和组织外的知识,而这两者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例如,IBM公司的广告宣传集中在其组织的人性化的特征方面,如对普通员工的关心帮助(在公司许多广告中可见的由卓别林饰演的形象所体现)。但是,这一形象的推出主要是为了促进公司外顾客的消费,是为了公司的市场营销需要。公司内部的知识则更集中在组织的效率和坚持严格的行为规范(由公司深蓝色的制服和白衬衫的“一致性”所代表)上。
同样地,麦当劳也特别善于利用电视来传递其公司形象,它的重点是放在美国人传统价值观上,如家庭、友谊和辛勤踏实的劳动。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麦当劳在电视上所营造的现实与我们在公司的联营店里得到的实际体验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并没有完全否定其广告片力图造成的使我们心里感到温暖的符号现实的努力作用。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组织权力以推理形式体现其自身的方式。所有这些公司都在从事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因为它们所介入的话语活动,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是不能完全恢复的。在每一例中权力的实施是因为组织有能力把某一特定的结构加之于它们所介入的话语活动,同时则不使该话语的准确性受到挑战。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公司在其广告片中都撒了谎,而是说它们能够以推论形式构建某种现实,而这一现实一般由于电视信息流动的单向方式而未受到挑战。在这一方面,福里斯特指出了推论的有效性声言和权力的实施之间的明确联系:
权力可以被理解为并非是一个行为者神秘地作用于另一个行为者的占有物,而是把两个行为者绑在一起的一种规范关系,一种构建一个施事者对另一人的信息的依从、对另一人的假定的权威的遵从、对另一人的意向的信任和对另一人的注意声言的考虑的关系。(1982,12页)
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情境中,合法性问题包括不是通过理性获得的一致意见、而是通过对不能经推理恢复的真理、正确性声言等等的强加而使意义结构制度化的能力。因此权力是和那些最能够作出真理声言的旨趣群体在一起的,这类声言最能够抵御推理恢复。不仅如此,这样的规范权力在被那些被迫接受者不加怀疑地接受以后会得到大大加强。例如,一个组织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信息的依赖在后者有意对有助于依赖群体的重要信息加以控制时会产生经过系统歪曲的信息。这一经规范方式构成的关系在依从群体看来可能是有疑问的,是需要加以改变的,或者被简单地视为“事情就是这样”,即组织行为的自然结构。
这些规范关系不仅仅是有关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组织形成过程中结构方面的一个结果。即是说,由不同的群体所形成的意义结构通过具体的组织行为来体现的方式而具有一种真实的特质。这一行为反过来由对组织成员提供组织现实意识的意义结构所框定(Giddens,1979)。因此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概念必须被视为不是一个纯粹的推理(即语言)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形成过程的一个物质性的方面。
因此,对组织文化的批判理论越过了意识形成的表面问题,进而对某些意义结构得以比其他意义结构更具渗透性、被更广泛接受(即更具合法性)的手段进行研究。换言之,从批判的角度看,关注的重点是既得利益能够潜在地限制推论选择、从而形成一个虚假的、而不是理性的一致意见的方式。作为既得利益的载体的组织对传播进行歪曲和限制以使得这类利益得以保持和再现。在这样的情境中,如哈贝马斯所认识的批判理论的作用便是社会重构作用;即是说,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体系的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的结果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形成,恢复一种理性的一致意见。
有的理论家试图把组织传播的批判理论包括进去。例如,弗罗斯特(1980,503页)提出,“批判的组织科学应该努力把理论和革命行动结合起来,这样使得个人充分意识到组织中存在的矛盾和不公正,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一立场代表了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付诸实践的倾向。迪兹(1982)和迪兹及克斯滕(1983)用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们提出,批判理论对社会重构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解、批评和教育三大任务。这里,理解指的是社会行为者介入“推论渗透”的能力(Giddens,1979),同时承认形成和保持组织现实的因素中人和社会的作用。批判指的是对意义结构得以被作为合法接受的过程的审视和分析研究。最后,教育包括对组织成员积极参与自我形成过程这一需要的承认,这是指在通过未受到强制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建立由推论构成的另一种自我现实。
关于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的例子可见于前一章所介绍的迪斯尼乐园的劳资纠纷。理解的过程显示于组织成员对管理层试图就迪斯尼乐园组织成员作出的再定义(即把“家庭成员”重新定义为“雇员”)的认识上。批判见于组织成员对管理层采取解雇工人和削减措施的行动的合法性的质询上。教育则出现于工人们积极提出一种与管理层意见不同的组织概念,它产生于试图把这一新的现实现散布给公共成员的实际行动中。
任何关于组织形成的批判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把批判行动本身包括在内——这一行动使得人们对自身的生存条件进行反思。这一自我反思过程在较为传统的研究组织文化的理论中是缺乏的,因为在这里对意识形成过程的解释本身被视为目的。尽管它们承认这样的意义形成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对这些意义形成的批判性评估由于缺乏反思的成分而受到严重限制;这即是说,现有的组织文化理论一般并未赋予组织成员重构思想的能力。相反地,它们一般被视为在社会形成过程内运作,尽管它们自身创造并再塑着这样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提出“情境中的选择”和“情境的选择”的概念来指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差别。前者代表了解释论和自然主义的观点,一般限于对构成组织成员日常的社会实践的表层意义结构的描述;这里关注的是对由情境和成员形成的概念为基础的组织的描述。后者则超越了简单的描述,集中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上,试图揭示歪曲传播过程的束缚和阻碍。在这一意义上,情境的选择在组织的表层意义后面进行探索以提出其他的关于组织行为的思路。例如,布拉韦(Burawoy,1979)对机器操作者的研究选择把一般接受的组织逻辑倒过来,他这样提问“为什么工人们干得那么努力?”而不是从管理者角度通常提出的“工人们为什么不干得再努力些?”这一概念角度的急剧转弯使得布拉韦能够不仅探索工人自己的组织现实,而且还包括组织压制和统治的深层结构性质。因而布拉韦对情境的选择使得他避免了让自己的研究陷入由占主导地位的管理层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意义框架中去。
哈贝马斯提出的批判的整个过程以弗洛伊德的推论干预为基础,这被他认为是最接近于理想的言语情境的具体例示。之所以把弗洛伊德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是因为“心理分析作为把自我反思结合在内的科学的惟一具体的例子而与我们相关”(1972,214页)。心理分析理论公开的目标就是通过消除阻碍公共传播进入个人的无意识的阻力而解放患有神经过敏症的个人。这一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其目标所示,通过前者的自我反思,自我身上受压抑的部分可以得到重新认识和检验。心理分析师的任务是帮助患者把自我的这些用私人的语言受到压抑的部分进行“转换”,并把他们重新组成为可以用公共的方式进行交际的东西。因此,“心理分析者结束抑制过程的努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与符号解构相连的过程”(1970a,214页)。
通过应用于社会层次,批判理论的心理分析成分把社会整体的集体神经症作为其分析的目标。麦卡锡(McCarthy,1982,194页)指出哈贝马斯利用“心理分析概念在社会的制度框架和个人心理之间建立了联系”。神经症的概念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后者成了支持社会中特定的权力群体的现实形式。只有在意识形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