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陈染散文集)-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心里不高兴,认为自己并不老。
其实,她最怕的是跟不上我了。总问:“再过20年,咱们还能一起散步吗?”
我说:“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她又说:“你就会跟我不耐烦,你敢对天秋不耐烦吗?”
我说:“敢。”
她说:“谁要是喜欢你,做你的朋友,才算倒霉呢!”
我说:“对,真是天大的倒霉!”
母亲也喜欢天秋,她们偶尔也通个电话,互相控诉我如何如何”不讲理”。我和母亲穿了很厚的外衣到冷街上走,树木不日之间,全都光秃秃枝杈裸露,像一个个秃头歌女在冷冬的街头摇曳吟唱,马路也忽然变得空旷,这使得我们心情沉重地怀念起天秋夫妇和刚刚逝去不远的绿意浓郁的暖日。
母亲又一次揭我的短,提起奶粉事件,指责我的没心没肺。最后,搬出天秋来压我,说:“人家天秋就比你会行事。”我母亲总是觉得天秋比我能对付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
我说:“你饶了她吧!”
我一下子情致全失。
路边一簇簇绽开的月季花,炫耀着月白、紫黑、粉红及艳绿,五颜六色染透街边角隅。炮竹一响,又仿佛提前到了春节,而春节那种万家灯火、欢歌笑语,从来都使我思念起遥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我的故乡是在所有的那些个莫名其妙的远方,比如伦敦,比如这儿、那儿。特别是街头巷隅处处响起《喜洋洋》或《步步高》之类的节日乐声之际,我的心里每每总会立刻堆满难言的忧虑和惆怅。
炮竹没有用,无非是碎纸化在人家的屋顶上雨珠般嘭嘭敲响,从透黑的枝篱间飘飞零落,发出枯萎的扁叶子的沙沙声。地上人家的屋舍,铁皮窗子如抽屉一样紧闭,冷酷的季节降临了。炮竹制造的欢乐,无非是取悦空洞的日子,没有用,到底一样是空洞的。
我多年来所以经久不衰地热爱着走路,即使是在这样萧条的冬季,想来大抵是由于走路可以延伸内心的对话吧。走上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便可以全神贯注地沉醉在思想里。任何一种伪造的繁盛与喧哗,都无法抵挡内心对话的清醒前行。而安谧沉静的身体,决不会有一丝裂缝,使内在的对话渗透出来。
那心,自然不是结在路旁枝头上的果实,任是谁人也无法将她强暴地击落或掠走。
天秋的小说里说得好:我只对温柔妥协。
逝去的声音
逝去的声音
两周前的一个清晨,天气已凉,我骑车去出版社的路上,秋风打透毛衣浸在肌肤上,感到一阵阵寒气。我脚踏车蹬,机械而重复地转动,我的神思却随着向前滚动的车轮往回倒转--从澳洲返回北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街景和路边的树木、草丛、商店我已经熟悉得对它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我的肢体安于我所熟悉的街区的同时,我的心却那么不安分地寻找着新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的双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拒绝我的过于冷峻、自省的理智,本能地寻找着什么。
从我家到出版社只有10分钟路程,我的思路来不及在任何一个点上延伸进去,腿已经迈进编辑部四敞大开的房门。我的脸上随即也换上一种身置公共场所的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礼貌、平庸,把自己思想里任何一个小角落的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全都掩埋起来。平庸(不等于平凡)的人群里不能容忍不平庸。不平庸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总是要受到指责的。早在1
9世纪叔本华就说过: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品德时,无疑的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每个人都谦虚,世人便都类似了,这真是平头的平等啊!
我早已懂得,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编辑部里正在传阅《联合报》,当报纸上的文字刺目地闯入我的眼帘时,我一下子被震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中国大陆朦胧诗人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威赫克岛上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自缢身亡。报纸的大标题下边是一幅顾城的照片,他头戴一顶白布帽,神情是他惯有的那种忧郁,让人看了仿佛是他自己正在给自己祭奠。那照片上的眼睛一如几年前一样,黑大而茫然,我仿佛就看见他那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纤纤的瘦手指固执地比划着他脑子里的那些怪念头。这形象无论如何无法和报纸上的文字对应起来。那文字好像蓄有强大的电荷,几次都把我落在上面的目光击开,使我无法与之对视。
这血腥而疯狂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但我除了震惊却无一句话可说。死了就是死了,他这样选择了结局就是这样的选择!我不想对此评头品足。若是我,也许会找个没人地方,谁也不打扰,谁也不伤害,自己解决了自己。也许,只对最亲密的人说一声:就当我出远门了。然后离开,非常简单。死亡这个词藻,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种话题,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物,它只是一个不轻易去碰的到此为止的黑色行为。也许是我过于珍视这个字眼的庄严,所以我在以往和任何公众的交谈中,一向对此缄口不言。回想起来,只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在绝望不堪的软弱之时,曾流露过谈论这个词的念头。
有一天,在餐桌上,我并不感到饿,也并不感到咀嚼的香甜,但仍然麻木而惯性地吃着。正是深秋的傍晚,房间里的暖气还没有来,餐桌上的那盏小灯昏昏沉沉,时间仿佛凝固一般,我的脑子却活跃地转动。桌上的食物很快就凉了,狼藉凌乱。我想,人生不过如此,到最后不过就像这桌残羹剩饭,乏味而无所欲望。
风风雨雨活过来30年,对于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分别(死亡只是各种各样的分别里的一种形式)都已不再有早年那种”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大呼小叫。再见就再见,永别就永别!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就在那天的晚饭桌上,望着一桌渐渐冷却的餐食,脑子里闪电般胡思乱想着。忽然,我对着母亲说:“再过两小时就要被枪毙,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小时您准备做什么?”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慢慢转过神来,”神经病!”她说。
我说:“想想总可以吧。”
果然,母亲就认真地想起来。
”那么,是枪毙我还是枪毙你?还是两个都枪毙?”她问。
”我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别那么具体。”我说。
”不具体怎么想呢?”
”那好。比如,就枪毙我吧。”
我说着,心里已经迅速地周转起来:有两三个长电话要打,有两个文件要写,关于我的书稿文字委托权和属于我私人的遗产,等等。
记得有一次,我非常失意地对好友谈到死,她立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骂了我:“别那么自私、混账!生命不全是你一个人的!”她骂得我非常感动。
那天的餐桌上,母亲听了我忽然提出的只剩下两个小时生命的话,眼睛里立刻盈满泪水,质问我:你为什么会做这种设想?!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改口说,我只是随便一说。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随便一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这样:死,是对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我不知道我能否有一天,冷酷地面对着我最亲密的人说出:我只是我自己的!
尽管我一向喜欢探索一切不可能和禁忌的事物,爱好古今中外的怀疑主义哲学和离经叛道的学说,尽管自取死亡这个黑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但我从来不把它仅仅视为哲学问题,也缺乏对它更深入的探索。因为探索再向前迈进一步,那么任何结论都将由于死亡而中断、而消逝。
死去的已经死去,我怀念他们!而我,还要继续自相矛盾地活着。
去死,在某个层面上,起码是对平庸哲学的叛逆;死,是一种否定行为,这种否定于某一类人来讲,我以为正是对生命的渴望,尽管这样说是有悖逻辑的;死,还是一种艺术的极端,用结束来实现这种极端,那么在实现的同时又会全部丧失,这是矛盾的、悖论的,同时又是悲壮的、惨痛的。
几年来,在故去的人群里,有我曾经深深喜爱过的人,我就当他们出远门了。当然,也有一种只是因为出远门而背离了我们情感的人,那么我只好就当他们死了。
平庸呢?我以为也是一种出远门--是一种精神的远离。
我看”自杀”
我看”自杀”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为女主人公的死做了如下天真的设想:
1.方式:两瓶强力安眠药。先吃7片,待神志濒临丧失的时候,急速吞下两瓶。向右侧身曲腿而卧,左手呈自然状垂至胸前,右臂内侧弯枕于头下。
2.地点:在贴近母亲墓地的宁静无人的海边,躺在有阳光的雪白或灿黄的沙滩上;或者是一条蜿蜒海边、浪声轻摇的林阴小路之上。但不要距海水太近,免得被浪潮卷走而让鲨鱼撕碎; 同时也不要离海水太远,要能聆听到安详舒展、浪歌轻吟的慰藉之声的幽僻之所。
3.时间:在生命还没有走向衰老的9月的一个黄昏,太阳渐渐西沉了,天色黯淡下来,世界很快将被黑暗吞没。这个时候,善良的人们都回到温暖的房间里,谁也不会发现一个女人在幕天席地的海边静静地安睡过去,永不醒来......
4.遗言:不给任何一个人留下只言片字或照片。话已说尽,路已走绝。
5.遗产:销毁所有信件、日记、照片、作品手稿、录音带、私人信物,
等等。其余,全部留给一位单身无依的、具有杰出天才和奉献精神的守寡人。决不把遗产当做最后的功名献给××机构。只把它献给像我一样追求和忠诚于生命之爱,但由于她无家庭无子女,政府就不分给她房子的人。
6.死因:我死于自己的秘密......7.碑文:原谅我只能躺在这里用冰凉的身体接受你的拥抱......
设想总是美妙的、浪漫的,真正的死亡肯定不是如此这般诗情画意。但设想总有它自身的道理:我们肉体虽然已经死去,它如同一摊烂泥无权要求什么,但是,那死去的人的尊严和感情没有死,依然渴望人们尊重他的愿望。
直到如今,在我身体不适、精神颓废乃至于绝望的时候,当空洞如同雾霭弥漫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当普遍的冷漠像房间一样把人们的内心隔绝开来的时候,我依然常常想到”死亡”这个黑色的字眼,想到无论何时只要一想就会感到心疼而无望的张爱玲的结局......我无法使自己摆脱”死亡”的阴影。尽管第二天或第三天阳光灿烂起来,远处红色的绿色的窗户纷纷开启,像嘴唇一样绽出微笑,我依旧会坐到书桌前来平静地继续工作......但我知道,”它”依旧掩埋在清晨我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光洁的脸孔后边,深隐在我的努力随和待人处世的笑容的尽头......
按照一般的观念,人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逃避和责难,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自杀。在古典的宗教里,甚至有的视自杀为罪恶。我不这么看,我不否认,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存在着由于个人的狭隘或精神失常者的自杀现象,他们对活下去的恐惧超过了死的恐惧,非常可怜。但是,的确有另外的一种自杀,一种视自己的信仰、追求高于自己的生命的勇敢者。有勇气向这个不完美的甚至有时候肮脏的世界大声喊”不”,我以为是充满责任感的人,而为此自杀,正是最大的一声”不”的叫喊和对人生的极端的质疑。我所敬仰的几位艺术家、思想者的自杀就是这样的自杀。
再有,即使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而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是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中惟一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结束生存的类种,我们是有权利享受人类这一特殊”优惠”的,并不是人人都想活到掉光了牙齿,思维和浑身的”零件”犹如长了锈一般难以转动的那一天。比如,茨威格的安详的自杀,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结束方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不自杀的选择,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更为顽强的精神支撑,那是对自杀的一种超越。米兰·昆德拉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言论,他说,一个他所爱的死者对于他永远不会死,他甚至不能说他曾经爱过,他拒绝用过去时态,他说他爱(现在时态)。
他还举了一个我十分熟悉并为之感动过的福克纳一篇小说的例子,一个女人因流产死去了,她的男人这时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他被判了10年徒刑。有人送给他一粒白色的毒药,但是他经过痛苦的精神挣扎和决断,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惟一能延续他所爱的女人的办法,就是记住她回忆她,让她在他的生命中永不消失。这样,他必须首先得活下去......”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将都不复存在。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表演悲剧
表演悲剧
昨晚上空空等朋友三个小时,他未来。僵坐在沙发里,神不守舍心不在焉地胡乱翻着杂志。等到十一点,便不再等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他那边支支吾吾说来了客人,我说有事可以来个电话,这样轻易地失约不好。我说完就挂断了。
脱衣更鞋,然后进卫生间彻底冲浴一番,似乎那整整三个小时的冗长的等待,沉落了一身的灰土,需要干干净净地淋尽。我知道,那灰尘的感觉缘自内心里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烦躁。从卫生间出来,清爽了许多,径直把电话关上,不想再给他以解释的机会。关上电话心里又不安起来,就又打开,电话刚刚打开就炸响起来,于是又迟疑着不想接通,就又把电话接到录音留言上。结果,电话铃轰鸣不断。
不想与人说话。
出版社刚刚发了一套三岛由纪夫系列,夜里便翻开他的那一本传记,阅读起来。十年前,我曾经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当时是与川端康成的书交替而读的,书桌上还同时并放着几本其他不相干的书。这次不知是心境的缘故,还是十
年来内心越来越沉于平和,读他的传记,我发现我越发不甚喜欢三岛了。这个人的张扬膨胀、自我中心、刚烈易碎,远不足以引起我的敬意。1970年自杀的三岛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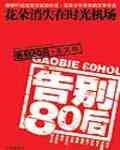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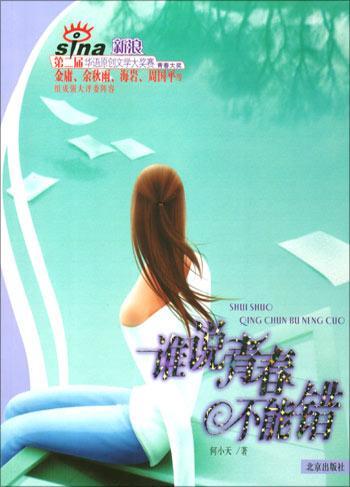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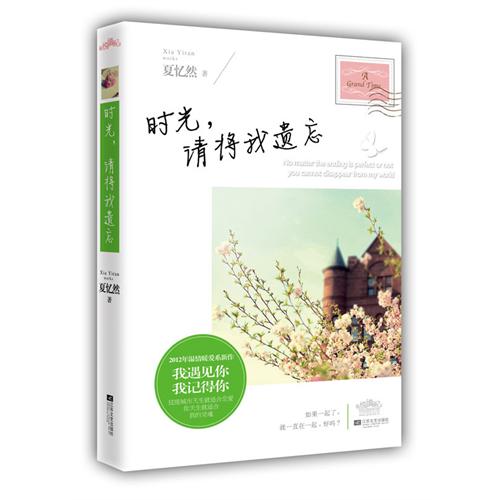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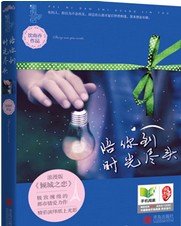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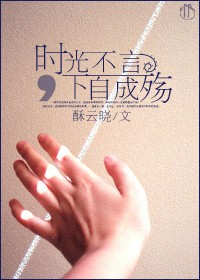
![(综漫同人)[网王+柯南]时光迷城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12/12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