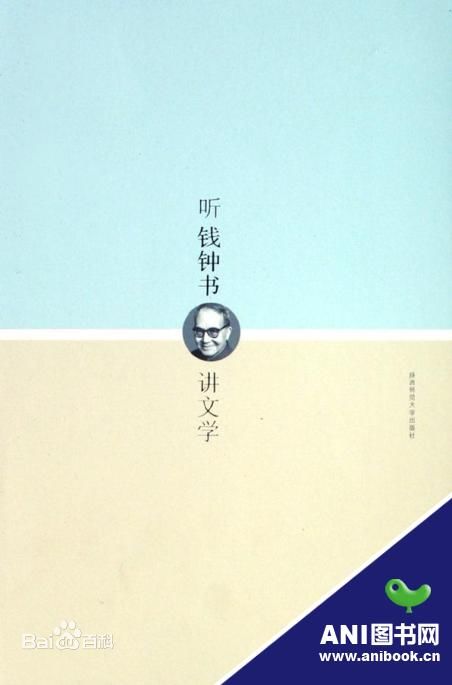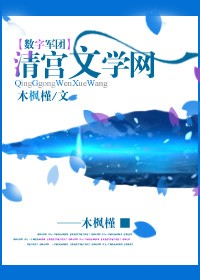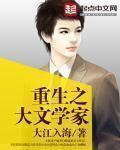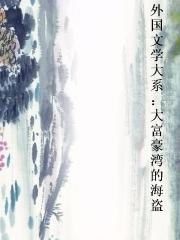钱钟书讲文学-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做人要有道德,作文须有文德。文德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勇气。
注释
'1' 诗史:是中国传统的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很多人把诗歌和历史混淆起来,认为诗歌要有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于是把作品当作作者真实经历的反映,把各种比喻都理解为作家的理想抱负的投射,特别是自从屈原以后,香草美人几乎成了贤相明君的固定说法,这种观点对一部分诗文适用,但是忽视了艺术创作的虚构性,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规律,因此受到钱钟书的批判。
'2' 《文心雕龙》:南朝刘勰创作,因为写文章要仔细雕琢,多方修饰,好像雕龙一样复杂细致,故如此命名,意思是文学家运思写作好像雕龙。全书10卷,50篇,谈到了文学的本质与起源,构思与创作,风格与体裁,写作技巧、批评与欣赏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杰出的一部著作。
'3' 美刺: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4' 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为屈原的弟子,曾为楚顷襄王大夫,流传至今的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六篇作品。
'5'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成都人,擅长写作辞赋,著名的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是汉大赋的杰作,王莽时因事被株连,投阁自尽。
'6' 嵇康:223—263,三国时魏国人,著名文学家,诗风洒脱豪侠。他的《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杰出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玄学的代表著作。
'7' 魏收:505—572,北齐史学家、文学家,与温子升、刑邵并称北朝三才子,但生性轻薄,官至尚书右仆射,编修国史,著有《魏书》,当时的人因为他褒贬不公,称该书为“秽史”。
'8' 阮大铖:1587—1646,明朝人,天启年间任吏部都给事中。因为依附宦官魏忠贤被罢官。明福王时,和驸马马士英共同把持朝政,官至尚书。清兵进攻南京时,主动乞降,后来因为一次卖国的密谋被识破,跳崖而死。
'9'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曾任河阳县令,因在县里种满桃李,一时传为美谈。他擅长辞赋,尤其擅长悼亡诗。潘岳长得非常漂亮,传说出门时妇女向他乘的车上扔果子表示爱慕,果子装了满满一车。后来“潘郎”就成了妇女所爱慕的男子的代称。
'10' 章学诚:清代人,在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任职,学贯古今,尤其精通史学。
'11' 王充: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小时候学习儒家,但又能兼通百家,只做过一些小官,还不断和上司发生矛盾,于是弃官回家,专门进行学术研究。他的《论衡》抨击神学迷信,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写作,什么样的书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美的等问题。
'12' 范缜:南朝梁人,著作《神灭论》针对当时佛教盛行的现象进行了犀利抨击。
'13' 钟嵘:南朝人,他创作的《诗品》也是文学理论名著,和《文心雕龙》一起被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此书主要对从汉到梁的122位诗人进行了诗歌品评。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刻薄人善做文章”的观点?
2.“文如其人”到底对不对?怎样辩证理解它?
3.如何培养自己的“文德”?
三、读书的精神
章节提示:
对传统的继承是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它根源于人的天性,作为一种能思考的生物,人的每一刻也许都在追问“是”或者“不是”,人生多半是在自我肯定和自我怀疑的矛盾组合中度过。知识积淀同样受这一矛盾的支配,因此,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具有怀疑的精神,不断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钱钟书治学,就是本着辨伪求真的精神。即使是那些已成定论的事物,也是从不轻易相信的。典籍高册、历史文献,概念名理,这些都要经过他深思明辨的心灵透镜的检验。书不可尽信,这是钱钟书的一个读书原则,因为了艺术创作或者其他原因,历史上常有很多言不由衷的书,尽信书往往会闹出笑话。
同样地,历史也不能尽信。虽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语言却容易失真。古人史识浅薄,不懂得区分真幻,存疑传信,记事时往往体会人情,揣摩情境,不自觉地运用想像、虚构,还以为理所当然。历史,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小说的道路上去了。钱钟书辨析了“诗”与史的关系。指明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说“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历史,总是人的精神心理蜕变留下的痕迹,从此意义上讲,不仅史书是史,一切典籍都是历史。只凭具体的历史事迹不足以认识历史,要多方参考,绕到史书的背后体会历史精神。
名教传统在历史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常常将名和实分离,概念、名份成了人的心理负担。钱钟书深感世间事物多有名无实,提出无论读书还是治学都不要“只求正名,浑忘责实”,不要尽信名而忽视了实际。
怀疑的精神
由于艺术创作和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身边常常存在一些言不由衷的书。了解一些信息误传的手段,可以提高我们鉴别的能力。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不如无书。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怀疑的精神。
钱钟书曾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唐代一个叫王彦龄的人好唱《望江南》词,去宫廷拜见长官时,他的上司责备他,王彦龄立刻上前用《望江南》的句式回答道:“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下句没想好,回头正看到一位姓马的军官,于是接着说:“请问马督监!”退下宫廷,马督监责备他说,我又不知道情况,你干嘛让我作证啊?王彦龄笑着回答:“暂且借您押押韵,请别见怪”。另一个是《说郛》里记载了一个叫李廷彦的人,他给上官献上排律百首,其中有一联说:“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读后替他伤心道:“想不到您家里遭到这样的不幸。”李连忙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儿,这么说只是为了押韵方便。”
对于这两个故事,钱先生说:“虽发一笑,足资三反。”反思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次,是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应持的态度;再次,推而广之,对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文学追求艺术性,当然离不开虚构。如上文讲的两个人可笑之处不是因为他们随意编造,而是因为一个人不分场合,需要明言事实的时候仍然用艺术手法处理,所以闹出“环境错位”的笑话。另一个则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把文学创作理解成纯粹的形式追求,不着边际地臆想。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作家还做着类似可笑的事情,并把为了追求艺术形式而不着边际的虚构作为创作的真理。我们的文学史上向来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首先是用于抒发情怀抱负的。若“情”和“志”完全受“属对须之”、“押韵须之”的驱遣,文学就变成了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两个故事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文学和生活的距离。类似得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屡见不鲜。把作品里的故事作为生活的理想,甚至在现实中模仿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生活,是很多年轻人易犯的错误。因为他们缺乏怀疑精神,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推而广之,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得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给后世好学深思、对书传记载抱怀疑态度的人有很大启发。而钱钟书对这句几乎被奉为真理的话同样有自己的看法,进而补充、申发。他在《管锥编》中论《诗经》的时候谈道:“顾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各坠一边,不尽信书,斯为中道尔。”后来又进一步解释说,学者观赏诗文,总喜欢推究考证那些缺少证据的言辞,难以验明的事情,这种工作固不可少,但若做得过分,就像扶不住的醉汉,从东边扶起又向西边倒去。完全相信书不如无书,但完全不相信书就等于无书,好比楚国没有得到,齐国也从口边溜走了。
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当中,唯有文字将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但是文字是静态的,是没有感情的表达。人们在传达或者转述的时候,往往会加入自身的感情色彩,导致事实失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所以,人们在探究与治学的时候要有怀疑精神。
王充在《论衡》里讽刺世人,以为凡是写在竹帛上的东西,都是从圣人那里传下来的,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相信得一塌糊涂。自然,也闹出了许多笑话。
笑话通常这样产生:古书里的话一般说得非常简练,有些从神话或历史中沿用的掌故常常是一带而过,不免给后人的理解造成困难。可偏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想当然地随便发挥,而且发挥得头头是道,解释记载下来,流传开去,等到明眼人再翻开历史的书卷,发现漏洞时,就又多了一件闲谈的笑料。
这里讲讲钱先生说过的两个笑话。在上古传说的唐虞时代,有个叫“夔”的人,做大夫。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大家都说:“调乐如夔一足矣”,意思是,主管音乐,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但在世人流传中却成了:夔只长了一只脚。
另有一个笑话是“宋丁公凿井得一人”。讲宋丁公没有凿井时,每天要派一人去打水,凿井之后,打水的劳动力就节省下来了,所以说:“得一人”。俗传却成了宋丁公凿井时,在井里发现了一个人。
市井百姓喜欢传疑,往往一件事传来传去就变形了,如果只把它归结为小民百姓读书少,见识浅也就罢了。可是,钱钟书发现,很多书籍的作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出于无心,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强词夺理。怎样才能在读书时学会质疑?钱子谦在《钱学论》中将钱先生有关“传疑”伎俩的论述总结了一下,称为“学究操术”,我们看过后也许能对号入座,以后读书时才能防止被蒙骗,同时也避免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下面就对“学究操术”做个大盘点:
一、望文牵合。就是望文生义。只理解字面意思,却不探求作者的本意。
最有趣的例子是孔子乘桴浮海。《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是孔子晚年感觉到自己无力挽回衰退的文化,文教德育的主张行不通了,所以打算乘个木筏到海外去。并感叹说:“跟随我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听了很高兴。孔子又说:“仲由这个人太勇敢,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什么可取的了。”可后人把这理解为,孔子看着滔滔大海,想做条船,但不知去哪里寻找木材。而后来的传说更加稀奇古怪:曾经有一个鲁国人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茫茫大海中隐约见到人影晃动,原来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遨游海上。孔子给了鲁国人一只木杖,让他闭上眼睛骑在上面,安全地返回家。后来,鲁国人出海,把木杖扔进水里,木杖化为游龙,乘风而去。
钱钟书评论道:孔子竟然从不轻言神怪的忠厚长者变成了飘洋过海的神仙,跟随的人也不只是仲由一人,而成了浩浩荡荡的七十二弟子了,望文生义,虚构谣传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把孔子说成神仙也正好对了某些人的胃口,他们可以拿出一本《论语》,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神仙是存在的吧,龙也是有的,连孔子都可以证明呢。”很多人都善于通过古书发挥丰富的想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你就只好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二、坐实使信。就是说把话讲得头头是道,让你不得不信。
这种办法往往奏效。因为作者几乎把话讲得滴水不漏。可是,锐利的眼睛和好思的头脑仍然能找出破绽来。《太平广记》里面搜罗了许多传说和故事。其中记载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升仙的故事说,刘安升天时脚踏的石头上至今还保留着人和马的足迹。钱钟书却讥讽说,脚印沉重得都能陷进石头里,还谈什么升天啊?话说得越确切,反倒越不可信,越让人觉得荒唐了。当然,这个故事如果当做神话传说来读,细节反而能增加不少趣味。可是,它也教会我们:读书的时候,既要能进得去,又要能出得来;既能充分体会欣赏,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文学的虚构总是经不住真实世界检验的。
三、自圆其说。有些人在写作的时候喜欢拉出古人为自己做辩解,可是,他们不尊重人家自己的想法,而是弄虚作假地为自己设定的念头服务。
钱钟书引用嵇康的《养生论》为例。在这篇文章里嵇康说:“曾子衔哀,七日不饥”,曾子的亲人死了,他七天不吃饭也不感到饥饿。嵇康这样说是为了证明哀伤可以作为人的养生之道。后人提出质疑说,不感到饿这话是曾子自己说的吗?钱钟书则拿来《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的话“我虽然心中伤悲,但仍然想着要吃晚饭。虽然痛苦,但我的肚子命令我吃饭,可以把痛苦稍稍忘掉。”证明嵇康的养生之道不值得相信。如果完全相信了嵇康的话,按照他说的去做,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危险来。
四、引人入胜的误解。误解有时会给后学者造成危害,有时却也别出心裁,造成一些引人入胜的效果。西方诗人如瓦莱里'1'、艾略特'2'都曾谈到或应用过这个理论:“误解或有创见能引人入胜”。钱钟书发现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唐初大诗人张九龄,他做过一首咏梅的诗,其中一句是“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有一个传抄的本子把“馨香”误写成了“声香”。但是,后人在选编时一直就错了下去,当唐朝诗人钟惺'3'读到时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反而评价这有声音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