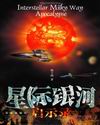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7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153'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154'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权利缺失。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155'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156'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157'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的歧视显然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同质的——它们都既异质于“私人交换”的社会(即今人所谓资本主义),也异质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的未来社会)。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为种族隔离与歧视黑人的制度辩护时自有一套理论,从白人归正教会关于他们是“上帝选民”的神学解释,“白人比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史学观点,直到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得出“白人的人权标准不适用于黑人”、白人与黑人只能“各自发展有各自特点的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振振有词。而中国那种对待农民的二元体制当初在苏联也曾得到列宁所谓农民是“半反动阶级”、“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158'的阶级优劣论的促成,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以农村为“殖民地”、靠“剥削”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当然在靠“农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与苏联人相比要积极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农民”从一开始就指所谓“绝了发财之望”的那些人,他们很多其实是游民;而所谓“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那些上进农民,他是非常厌恶的。'159'由此产生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小农“落后”、“自私”、“保守”的阶级歧视理论和敌视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即使“文革”时理论上最“左”、“贫下中农”形象最高大的时候,那些不服服帖帖“为革命种田”而要进城打工挣钱的人也不被当作“贫下中农”,而被谓之“盲流”,那时就备受歧视,改革后对“农民工”的歧视其实就是来源于此。
现实中中国的农民歧视与过去南非的黑人歧视的确同样是“非竞争”的、制度性的、强制性或身份性的,两者都截然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属于更为落后的基本人权不平等。而且笔者前文已经列举的大量事例都证明:这种歧视的力度在中国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国民工办暂住证要交很多钱,南非黑人办通行证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证就不会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时期出示了暂住证仍然会被抓;中国民工的“无证被抓率”总体上也比南非高;中国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严格;中国“农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劳工低,而“两栖”率比南非黑人劳工高;中国“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铁腕,而且南非毕竟还有“安置”,中国则往往是纯粹驱逐;而为了把“暂住者”留在乡下,两国搞的乡村建设中,中国的财政投入也远不及南非;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对待黑人比中国对待农民更恶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来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规模(而非速度)来讲比我国目前的圈地运动要更严重。
当然,在世界潮流中这两个国家都在进步,中国改革中的进步是明显的,南非即使在1994年民主化之前也已经有不小的变化。在弱化歧视、提高人权的过程中,中国总的趋势与南非是相似的,但进度则比南非晚许多年。例如,中国由征发劳工制转向“流动劳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南非是在上世纪一〇年代;现在南非已经由“流动工人”变成了自由就业与定居,中国还远未做到这一步;在对“流动者”的盘查中从“无证抓人”为主改为以“无证罚款”为主的“软歧视”,南非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我国发生在2003年后;南非的“通行证”于1986年废除,我国至今尚未废止,只是一些城市最近出台了改“暂住证”为“居住证”的试点,尽管只限于特定的“人才”,毕竟也可能是“暂住证”制度衰亡的开始;……当然也应该指出,中国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在一些方面进展还是不慢的。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的身份歧视即“低人权”现象,因此需要基本人权平等(即马克思讲的“形式平等”)的改革,而且中国甚至更需要。
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中国能避免民主化以后的“类拉美化”危机吗?
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国与南非可比,那么“中国的明天”会发生“南非今天”的事吗?今天南非那些好事,如身份平等政治民主等等,乃至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倡导和解、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待历史问题的化解,等等,当然已成为佳话。但是新南非的“类拉美化”治理困境的确比较严重。我们在南非的华商作为治安不良的重要受害者,感受固然比当地黑人强烈,但当地舆论也是非常不满的。各国历史上民主化以后有一段“转型混乱”不止南非为然,例如不少中东欧国家也有过这个阶段。但是1990年前后发生变革的中东欧除了极少数发生战乱者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早已结束“阵痛”转入复兴和繁荣,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考试”加入欧盟成为“准发达国家”。而南非民主化比他们只是略晚,却至今还没有走出适应期。应该说,要讲“民主化的代价”,南非付出的这种代价要比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更大。
但是南非现在即使是白人,也绝少有人讲不该民主化的。这固然说明了民主、人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另一方面,我国有些人总喜欢拿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之后的“乱象”来证明转型搞不得。南非既然转型之后“更乱”,应当更好拿来说事。无奈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正确”似乎比反对“斯大林体制”还明显,它已成为从自由主义者到南非共产党人都坚守的“共同底线”。所以我们上述网友的那些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恐怕上不了正式媒体。
然而既然有人这么想,我们也应该回答:假如未来中国推进了社会转型,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
严肃的学者不会以算命先生自居,但我至少可以说,中国如果推进了社会转型,出现南非式困局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南非如今并非一切问题都是“路径依赖”所造成,1994年后南非是有些教训要汲取,这里无法详述。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与过去南非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同质性的一面外,当然也还有一些重要区别。其中主要有二:
第一,南非的“黑白之别”要比中国的“城乡之别”更为刚性化。
所谓刚性化,就是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前面说过,有的国家的体制性歧视力度在很多方面比南非还大,“低人权”比南非还严重。但是歧视力度大,并不意味着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也大。由于南非的肤色差别直观而且固定,“黑转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农民即便在身份壁垒最严格的时代,也有一些人获得恩准“农转非”。南非亲白人政权的黑人保守派酋长再受宠,充其量也只能在白人政权支持下统治“黑人家园”,不可能进入白人国家的权力层。然而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尽管在公务员录用上同样有身份壁垒,但“政务官”却实行“特恩制”。即便在当年农村中饿殍盈野、农民一般状况比南非黑人糟得多的“三年人祸”时期,中国的官员中出身农民的也很多(其比例甚至比今天多);而且在中国特别典型的“官本位”下,农民出身者一旦当了大官,老百姓哪怕是“市民”在他面前也得俯首帖耳。显然,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势并不是因为他种田,而是因为他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所谓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其实是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别。
不仅现在如此,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布衣卿相”,有人认为这就是“平等”,其实,这只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别的“刚性”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权者欺负起无权者来就更温和,也不意味着“官民矛盾”就更小。道理很简单:“布衣卿相”并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皇恩之下的“布衣卿相”只是政治暴发户,他的暴发并不意味着“布衣”阶层有了“代议士”。相反,他虐待“布衣”甚至可能甚于贵族虐待自己的属民。因为“受宠的奴才对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对奴才更厉害”。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多于一般贵族制社会中贵族逼反附庸的现象,是毫不奇怪的。而反过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基本上都是由非农民人士、甚至是由贵族领导的。
今天推进社会转型当然绝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