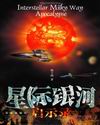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这时竞选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相对形象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17'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而另一方面,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又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0。36,并不高于欧美,而黑人中却达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加上黑白差异,导致南非全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为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旧南非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乎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非国大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经济,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需要拍卖国有资产,于是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也都能得到支持。但很快,一些“有来头”的暴富者就引起了非议。如2004年10月媒体披露,南非公共投资委员会将出资购买国有南非电信公司(TELKOM)15。1%的股份(市值约60亿兰特,约合5亿多美元),并很快转卖给一个名为“大象”的黑人财团,而这一财团恰是政府通信部前总司长和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牵头组建的。这条新闻令舆论一片哗然,南非工会首先质疑此项交易的公平性,称其为蜜蜂法的“最佳反面典型”。图图大主教也对此提出公开批评。舆论压力迫使姆贝基总统亲自发表长文为蜜蜂法辩护,声称黑人富豪中没有一个是依靠政府资助或扶植发家的,他们的致富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对TELKOM股份交易做了解释,有关的非国大官员也纷纷表示没有从此案中以权谋私。'18'
黑人首富莫泽佩
莫泽佩、恩加塔尼、恩金曼德、哈尼夫人等在哈尼墓前
民主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原则是“有错推定”,民间有质疑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举证释疑的责任,你不能证明无错,那你就是有错。非国大政府还是有足够的公信力的,姆贝基亲自出面释疑,风波便告平息。不过当时此类猜疑甚多,无论如何,当时的确有大量资源从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转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给定的条件下则主要是转入黑人私人手中。
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号称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泽佩,他在2011年拥有私人资产净值27亿美元(221亿兰特)。莫泽佩原来是个黑人律师,对法律变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经济赋权法》刚通过,他就从中捕捉到机会,筹资盘下多处矿山,包括金矿、铂矿、有色金属和铁矿,成为南非首个黑人持有的巨型企业“非洲彩虹矿业”集团(ARM)的老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黑人首富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时可以看到他与南非共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党的集会上。
而他的姐夫西里尔·拉马弗萨的崛起更是传奇:他是老资格的非国大活动家,而且是非国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矿工工会(NUM,作为工大会成员的21个行业工会中最大的一个)的领袖。过渡时期他是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又是制宪会议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为非国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过后,他立即华丽转身,辞去政府职务(但仍保留非国大的要职)下海“采蜜”,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创办Shanduka集团,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银行、保险和电信等业,从矿工领袖一变而为矿业大亨,成为与其内弟齐名的大富豪,据说其个人财产在“非洲大陆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拉马弗萨与祖马
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黑人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强大的工会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资明显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速不够和结构调整,黑人失业率一直很高,导致贫困率也居高不下。结果就是: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分贫富,黑人全都穷。而新南非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黑人从普遍穷困的“平均主义”状态很快变得远比白人更加贫富悬殊——这使人联想到:中国这些年不也是从所谓“平均主义”时代很快变成远甚于西方的、基尼系数高达0。5—0。6的高度社会了吗?
由于黑人中贫富分化的发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缩小,南非今天全国总的贫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种族隔离时代更高。有统计认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19'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70'20',乃至0。75'21'等。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2'就变化趋势而言,有研究认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代的1993—2008年的十五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从0。66升为0。70'23',还有数据说从1994到2005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从0。593升至0。631。'24'总之,新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要比过去平等。但是黑人内部的分化却很剧烈,而黑人又是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原来占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种族隔离废除后部分白人迁走,现在已经占到五分之四,黑人中的分化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南非的分化状况。这就使得旧南非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新南非总体上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从绝对值而言南非的贫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从趋势来讲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对南非新生的跨种族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对南非的贫富分化不能只看数值(基尼系数),还应考察分化的机制和性质。种族隔离时代身份性特权造成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不同于新南非,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阶级分化”。这正如我国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中(例如工人中或者农民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同身份等级间的“待遇”悬殊伴行,到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下也变成了显性的贫富分化一样。应当说,一定程度的非特权性的竞争型分化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有的现象。但是它不能悬殊得离谱,不能“赢家通吃”。特别是如果分化的悬殊又和旧体制留下的“起点不平等”有关,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在这方面,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了一定的“镇痛”作用。民主南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治比较完善,《黑人经济赋权法》和经济改革的其他法律尽管一直有争议,但却是在各阶层的“代议士”充分博弈后由议会多数通过的。这个突出“黑人赋权”的法律未必是“机会均等”的,但由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机会的严重不公正,在不搞经济清算的情况下对黑人进行“机会补偿”,也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连诺齐克这样极端强调自由竞争的思想家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当然,即便在黑人中,成为“蜜蜂富豪”的机会也远谈不上平等,尤其对于拉马弗萨这类从高官变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权致富更是争议很多。不过暴露在相当自由的南非舆论下的拉马弗萨似乎比较自信,因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穷人(不是自称代表,而是确实在自由竞选中得到大量穷人选票)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的支持——既然穷人都不“仇富”,你们不那么穷的人还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温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历史上白人殖民过程主要是在农业时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重要的历史罪恶。“奴役人民”的问题在黑人解放后解决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个“政治正确”之所在。尤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受到过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宗主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很多乡村还保留着非洲传统的部族、部落状态。而南非和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却主要是在所谓“独立”(白人自立建国)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统治,这些本土白人绝大多数原是农业殖民者(如所周知,所谓“布尔人”即“农夫”之意),他们对传统黑人部落生存空间的挤压,要比“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严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问题也就更突出。应该说,殖民者用强权“霸占土地”要比类似我国自古以来土地私有制下民间买卖、继承形成的土地关系更不公平,土地改革的号召力也更大。
如果说“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历史问题,那么南非现代化农业中的劳资矛盾就是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认为资本主义的兼并过程会消灭家庭农业,在农业中普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从而发展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阶级冲突。但欧美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使用业主家庭劳动和辅助性季节工的家庭农场至今仍在现代农业中长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现了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场景:使用全职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节工)的大农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于是南非农场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斗争就比欧美明显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这些黑人农业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乡村黑人还是生活在类似过去“黑人家园”那样的传统部落地区,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份地由家庭耕作,类似我们的“责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贫状态下糊口型的自给农业,并没有我国“责任田”那种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旧南非只是以此作为城市黑人“流动工人”的所谓退路,把他们的“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人群。由于靠这种糊口农业维持黑人劳工家庭的“两栖”性显然不可持续,当年设计这种“种族主义新农村”体制的汤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给“黑人家园”补充土地,使那里的农业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农场主不肯而未实现。白人政权转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长“独立建国”来实现流动劳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这一邪恶的梦想。新南非废除黑人家园制度后,这里的两栖家庭主要去向是进城团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则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更新基础设施以便就地脱贫。真正想既不进城又脱离部落,移居到原白人农场地区去通过土地改革“当家作主”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进土改的主要是黑人农业工人。尽管在前“黑人家园”与白人农场区接壤地带很多“家园”居民就在附近白人农场做工,并因而兼有农业工人身份,但是南非农业工人总数仍比前“黑人家园”人口少得多,当然比总数约4万余人的白人农场主还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没有我国那种农民(peasants)概念,原“家园”人口被视为传统部落居民,所谓“农民”(farmers)是指农场主。新南非尽管黑人中出现很多“蜜蜂富豪”,但农业并不吸引他们,所以农场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