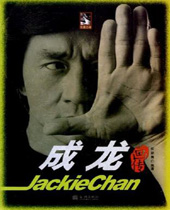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谓“红钱”是纸的,用硃砂染过,据说谁接到即可避邪。故此,每逢撒红钱的时节,台下一片争抢,很是热闹。遇到这种场合,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木讷而引不起兴趣,即便是“红钱”自动落到了他的脚下,他也不会弯腰去拾。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批以读书为生的人呢?同鲁迅的父亲一样,田产是前辈挣下的,到了他手里,功名求不得,唯一的事情是读书。家就在他们这一代败落下去。他们命定是要看到封建大厦之将倾的。
对于杨朝熙来说,父亲不是一个实体。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飘,便过去了。真正将性格、气质遗传给他,在他的四围筑起一个环境,耳濡目染,在精神上首先影响他的,只能是母亲。
他母亲
父亲逝世后,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母亲的天地构成小朝熙童年的天地。
母亲的身坯很大,他并不像她。从外表看,哥哥更像她,高高大大的。哥哥脑壳也大,诨名就叫“杨大头”。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他跟母亲更相似。大约六、七岁起,他就能跟着舅父、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他哥哥便不敢。
(你的安县街坊说,杨二哥黑黑、深深的眉眼,宽大的鼻子,还是满像他母亲的)
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荄镇人,姓陈。他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母亲的叔祖父郑香园,是本县的名举人,曾在甘肃花马池做过官。安昌镇西街天后宫,是本县福建籍人的会馆,其中郑姓占着主要地位。当杨朝熙出世的时候,天后宫已经由族人做主卖给李翰林家,直到他的舅父郑慕周有了地位才又赎回。郑慕周解甲还乡,一位亲属转送他一张李东生书赠郑香园的横批,具体文字记不得,但从内容上可以推知郑家原是,也曾经风光过,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
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外祖父续弦没几年也谢世。萧氏外祖母无生育,母亲和舅父是在继母的严酷管束下长大的。后来几乎脱离关系,视同路人。朝熙还记得萧氏外祖母晚年沦为半贫民,寄住在市街萧氏宗祠里。身边仅止一个兄弟帮衬,这个兄弟一脸麻子,以打柴、帮短工为生。舅舅为了了却过去的恩怨,最后把她接到家里来同住,为她送终。萧氏外祖母善于操持家务,只是心胸狭窄。母亲在她的挟磨下生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等婚后主持一个家庭,渐渐显示能力,境遇才有所转变。比起后母,她有凄苦的童年打底,待人善良多了。
(这个外祖母锻炼了你的母、舅。苛刻的环境给他们姐弟注入巨大的韧性和在社会上独立闯荡的才干。母系亲属对你生活的直接影响,要比父亲的大得多。你似乎应该姓郑)
1909年,杨朝熙的父亲病逝,母亲落入守寡和被小叔子们挟持的命运。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二叔母也死了。这样,他们这房,父亲已有两个男孩,三叔、四叔都只一个儿子,么叔又子女俱无,按照惯例,便由亲朋做主,把他过继给二叔,顶了一房人。
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这个家面临分崩离析。印象景深的便是几个叔叔一年中要和母亲大吵大闹几回,逼着分家。平日的小吵闹更不用说了。每当这时,尽管开朗、能干如母亲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偷偷地痛哭一场,然后再赶忙张罗请客,找亲友来评理申诉。幸亏父亲生前喜欢助人,结交下几位在安县有点名望地位的朋友,一个詹夔(詹棠)詹举人,一个刘子良,一个谢健卿。而他三叔、四叔、么叔因从小有哥哥操持家业,只顾吃喝游乐,在社会上交际不广。所以,尽管闹分家闹得凶,最后一次还闹了好几天,简直天翻地覆,可待詹、刘、谢几位一到,纠纷也便立时解决。就象鲁迅《离婚》里七大人的到来一般。
这样,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分了家,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每房四十亩。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分得了近一百亩的田产,都在老家河清。三进的大院,他们分得两进正房,还有后面一块空地。
看起来,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当然要由他们这两房来负担。记得单是一个焦家字号,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焦家是安县最大的士绅,田地、闲钱多,又开票号,雇陕西人经营,放帐生息最有一套。每年冬至一过,那些被安县人称为“老陕”的,就背起长长的褡裢,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朝熙自小一见这些“老陕”来,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胆怯,心烦。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家业的重理,她甚至还想振兴一下。她从小铸成的男子气魄,现在有了施展的机会。她治家虽严,对待下面人却很和气。安县打零工的都愿意到“杨大老爷娘子”家来干活,因为她工钱公道,饭食又好。她识字不多,不会记帐,但擅长管理,事事要强。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得惊人。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太和镇、遂宁销售。但才两三个月,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他失败了,初次经商亏了本,连船都赔了进去。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为了购置枪支弹药,母亲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很明显,你母亲充分利用了分家得来的有限家产,来培植你舅父,这才扭转了杨家的颓败。你的性格可没有这么“强”,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但她又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在家里供起佛像,招来一群婆婆大娘,抱点米来,抱点菜来,然后都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家里还供有“坛神”,每各都要“庆坛”,请十多个巫师,戴起各式各样的面具,焚香,敲打,起舞,一搞就是两三天。这时候,就等于给小朝熙添加了一个节日!
母亲对敬菩萨、逛庙会为什么兴趣浓厚?因为女人的苦楚不被男人社会所容纳。她青年守寡,没有到茶馆整日喝茶、摆谈的可能,更不能到社会上经商干事,随意抛头露面。吃斋念佛是母亲可以采用的一种心理平衡手段。当然,社会风气也允许这样做。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不光是婆婆大娘影响你写何寡母吧。这是综合来的,特别是何寡母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呢?呵,这倒是有一点的)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过去有一个时期,一天要喝一台,有时一天两台。这个爱好一直到他第二次胃溃疡发作动大手术后,才不得不戒绝。母亲还要他跟着吃花花斋,就是每逢阴历三、六、九吃素,忌食牛肉。直到十五六岁,才在舅父的劝说下改了。结果是他一生喜吃牛肉。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对他就更放松了,成为他欢乐的日子。除夕祭祖,贴春联,点灯,放鞭,在斗秤上贴“黄金万两”。不许谈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翻菜油。在给长辈叩头辞岁、吃团年饭之前,这里还有拜堂子年的风俗,便是先到亲戚、熟人家拜访。去一般商号、铺子,或有地位的人家拜年是朝熙最觉好玩的,不会有在大人面前叫不出那些复杂称呼的难堪,只需和哥哥拿着红纸写就的“恭贺新禧”的条子,拿着浆糊,在门上一贴就行了。杨家这时的地位不很高,但收到的条子很多,因为母亲人缘好。这成了风俗性的“民意测验”。
到了初二、初三,一个木匣糖,一块肉,一把面,开始正式拜年了。家里要做些糖什么的好回礼。在母亲的指派下,他们家每年的过年糖食,一入冬便请糖坊师傅来做,什么米花糖、谷花糖,原料好,做工又细,远近有名。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市镇尤其见得正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
茶客们开始赌牌。一般茶馆打两串底的小麻将,偶尔有人团足一场五分一角的赌局,就会传布开去,成为新闻:“××店里今天打银角子哩!”普通是打纸牌,有的“扯招”,有的“打点点红”,或者“挑麻雀”,各有各的玩法。大部分人站在牌客后面当“背光”,出起主意来比当事人还要热心。
十字口这样子的茶馆还有“唐摸王”开的唐家茶馆。本地语瞎子叫“摸人”。摸而成王,可见这个老板的精明厉害①。萧清淼开的是萧家茶馆。萧很善于巴结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大家授他一个绰号“金眼鸽子”。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镇子,拥有这么二、三十个茶馆,在四川真是平平常常。
成年的杨朝熙后来用“尹光”的名字写过一篇散文,描写家乡人们喝茶的情景,其中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①文章写于三十年代,由茶馆这个“窗口”看出故乡社会消蚀生命的封建性质。当然,这不可能是童年的他所能具有的眼光。不过,儿时的朝熙,也已经能够粗粗分辨县城内不同地位的人所上的茶馆是很不相同的了。
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案、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詹在省府读过书,拉得一手好胡琴。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赌的输赢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世界被什么力量分成了各个部分。你从小身处茶馆社会一定早早感到人间的等级森严了吧?我慢慢直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东西在操纵。不过无论欺侮人的与被欺侮的,都可在各自的茶馆登场表演)茶馆的门口围着各种吃食担子。卖抄手(馄饨)、醪糟蛋、担担面、凉粉,一招呼便殷勤送上。这些小贩往往几代人干这个营生,生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