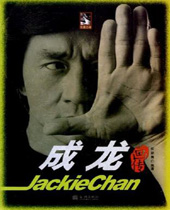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天晚饭,他正有滋有味地细嚼扑水蒸蒸,突然觉得胸中一阵搅动,比任何一次胃疼都厉害。他喊一声“心里痛”,跑回房间躺下,便大吐不止,并不知吐的是什么东西。“完啦”,这个念头一闪,天旋地转,人已昏迷不醒。
萧一家围在他床边。还是萧母有经验,见他吐出的是三坨硬血,连忙让儿媳把血块捡起放在瓦片上,用微火烤脆,研成粉末,灌他吃下。这是民间的土方,认为可以生血止血。当晚萧业贵去睢水报信儿,大家闹了一宿,不管如何,他确实没再吐血了。
第二天早晨,萧业贵兄弟俩用滑竿把沙汀抬到睢水,找萧文虎的父亲萧懋森按脉。萧老先生是个不挂牌的“业余”郎中,医道精良。吃了他开的药方,病情似得到控制。郑慕周派人来说,要送他去成都动胃溃疡手术,已经让老友陈序宾医师代为安排一切。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终于未成行。郑又送来二两西洋参,让他就地诊治调养。
半个月后,玉颀到苦竹庵探他,送来一罐嫩藕猪肺肠。他斜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端着汤罐用勺子吃了几口,揩揩汗冲妻子笑了笑。他的舌头能觉出这比萧家给他炖的花生稀粥有味,只是身子还很虚脱。这一天他无法忘记。自1941年他有睢水周围的乡镇隐蔽,七年来,这是与玉颀第一次在避难所相聚。她有上海地下活动的经验,生怕随便走动会暴露他的行止。王大娘和她的儿子王大生,在胜利后已经回河清乡重整家园了。岳母的年事渐高,不像以往那样能张罗。玉颀一身挑家务、教务双重的担子,够沉重的了。
这次,娇弱的妻子相信藕肺止血的功用,扔下奶娃,亲自送来。如果不是病为媒,还很难想象她会来呢。人生就是这样,祸福好坏往往倒错。
面对死亡,他有过惊慌,他不是那种淡泊到底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死神是可以随时降临的。
死是对“第六病室”的解脱,同时也是对写作、书籍、故乡、亲人的永远告别。此时此地,玉颀从他微微涨红的瘦削脸庞上所能“读”到的,便是对生与爱的留恋。最具特色的生命之药,是家乡的一剂“回龙汤”,即童便。他过去听说童尿内含有石灰质,产妇吃它可以打下积淤的血水,修补破裂的血管,没有想到它的止血功用如此广大。好在这付方子不需要任何“破费”,居停主人萧业贵家里便有一个现成的六岁男孩,足可“就近取材”,每天喝它两大碗。第一次喝下这名声赫赫的东西,一股腥咸的气味冲得他差一点呕出来。可是一天天喝下去,也就习惯了。他一直坚持服用了近两个月,居然意外地脱离了险境。
(在毫无医疗保健的条件下,你面对死亡,表现了生之顽强。老年的你,给人的印象是对生非常小心翼翼,可看不出多少“英勇”气质。我从来也没有英勇过,我对死的理解,便是要争取生。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对生的理解,在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死的方式,如果他能选择)
这段时间,玉颀和他不断发信向外界呼救。艾芜回信最快、最多,他拖了一大家口人自顾不暇,但还是寄来了一百元。法币废除,金元券刚使用便同坐飞机一样贬值,艾芜在信中叹息,姑且用来买几个鸡蛋吃吧。
凤子寄了五十元。王西彦穷得劼劼响,也救济不了朋友,便写了封长长的信来打气,称赞沙汀这几年的创作丰收。可惜“丰收”换不来谷米。蒋牧良令人感动,他俩只在鲁迅丧礼上见过一面,他自己分文皆无,却动员了一位电影戏剧界完全不相识的编导寄赠了一笔钱。
后来,以群的“新地”汇来一点版税。上海的“文协”总会闻讯后,曾汇款救济。特别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的催促下,把《还乡记》等预支的一大笔版税寄到睢水,这才有了药费、营养费,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四面八方涌来的友情使他对生充满了信念。
等到稍有好转,能下地走走路了,便遇上“水涨”。就是前面说过的睢水乡公所向县府“具结”,以担保沙汀不在本地。他第二天,在简毅的陪同下,抱病长途跋涉到永兴避祸。这时是1948年11月。
他认识简毅已有四五年。这是一个趣人。早年入过共青团,但很快退了。红军经过川北后,他被当作“乱党”逮捕,终止了在成都的学业。回到安县县城,整天以拉京戏胡琴自娱。他有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上海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就凭着这个,自拉自唱,倒也渐渐有了相当的水平。
睢水的乡长萧文虎正热心此道,便拉了简毅来睢水安家落户,挂上乡队副的职衔,并在中心小学代课。这个乡队副实在滑稽,他还是一天到晚教人唱戏打锣,并不懂得如何搜刮百姓。与沙汀讲起时势,头脑不糊涂。对本乡袁、萧的寡头政治,粮役上的弊端,时常加以透露。沙汀对睢水社会内幕的了解,一部分得之于他,这是与未来的《红石滩》有关的。
他跟在简毅身后,脚步已经空虚不稳。他的打扮好怪:头上戴顶用“博子帽”改造成的“毡窝”,加一根山民用的青布帕子绕头,遮住半个眼睛,脖子上一条毛线围巾把下颏挡住,拄一根竹棍。因为睢水场的轿夫张驼子被人召去抬新娘,大病初愈的他只好步行经拱星、河清,往永兴熊仁卿家去。
苦竹庵到河清五十里。挣扎着走进简毅堂姐家,一头坐下就不能动弹了。所幸简毅在将散的场口碰上熊仁卿,雇到两副滑竿,吃罢午饭,便与简分手,黄昏时到达永兴。
河清是他老家,二十年代当县教育局长期间去察看过几次。永兴却是第一次来,认识的人只有熊仁卿。熊入过他的家塾,算是同学。多年前,永兴的掌权人物看中了熊的“笔杆子”,青年时代被招纳,现在成为一乡之长。熊身材魁伟,强壮,一看就是那种文的武的粗的细的都来得的人。他的家在永兴场一里地外的梓潼宫,院坝宽敞,住房、门堂、围墙都不讲究,主人的心思显然没有全部放在上面。
熊每天不落屋,回来与老同学谈起战争,时常故意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然,就磨研他弄来的一块据说是真正的“虎骨”,吃着各种可疑的“补”药。
他的老婆是邻县一家财主的闺女。被他用骗婚、抢亲的手段搞到,现在却扔在一边,让她陪着烟灯和盲眼的儿子,在悲悲戚戚的回忆与哀怨中讨生活。她的价值只是婚前可以预见的陪嫁和昔日的青春美貌。听她一再讲自己的身世,到第二次、第二次,沙汀就忍受不住屋子里这种阴凄凄的坟墓气味了。他避到梓橦宫,找主持和尚谈天气和佛学,引得这个只会念“观音经”的人的尊重,后来甚至介绍了一位盲人来谈佛理。
在苦竹庵的病床上,他读过一点能到手的《六祖坛经》、《难经》的书。可能是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觉得玄妙的经学很引人入胜。单是那文词之美就够他欣赏的。他能观察与描写社会的争斗,但是骨子里,他对平和静谧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很容易与寺院的气氛合拍。
永兴梓橦宫这个“病室”只住了半个多月,熊仁卿告诉他,省保安司令部严密缉拿他的命令下来了。商量后将他转移到熊手下一个保队长的家,离永兴五里地更其偏僻的邹家抱房。这个姓邹的袍哥是五排,三十上下,短小精干。此人父亲在民国年间是大袍哥、大土匪,诨名“金毛辫”,杀人如麻。后来被地方军捕杀了。
邹家的院子比熊仁卿的大三四倍,四面靠墙均是平房,中间的晒场足有网球场那么大。这是刚抱出的小鸭儿的饲养、活动场地。这个院落最奇特之处,是到处安设门户。大门,后门,左右两面围墙上各开有两三道门。当初是为“水涨”的时候,“金毛辫”的人马从哪儿都可以跑得出去。放鸭子的伙计进出也方便。
沙汀住进这样大而无当的房子,听邹母念叨他家往日的“光荣”,感叹今日的式微。他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听老太太诉说了四个月的邹家抱房兴衰史。因为只有极有权势的人,才敢开抱房。孵出的鸭子放给赶浮鸭的人,没有哪个码头敢欺负。成百上千只半斤重的鸭儿,一根竹竿赶着过乡踏县,不花饲料,随处赶进刚收割过或还没割过的稻田,拣谷子吃。等它们丫丫地磨蹭到成都,已经够了份量,大了,肥了,成为市面上的水盆鸭子、烧腊鸭子。一路放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邹家大爷的面子。不然,鸭子会被人捉得净光,连根鸭毛你都剩不下。沙汀想,这放鸭儿真是一篇绝好的社会小说材料。
不过这里也不宜长久养病。一个保队长的家,来往杂人很多。姓邹的成天在街上“打滚龙”,游荡吃喝搞女人,就和《困兽记》里的徐懒狗一模一样。能与沙汀说得上话的,也是一个中学生,保队长的弟弟。同谢象仪的小儿子谢荣茂、袁寿山的儿子袁琳差不多。四十年代的中学生在两次战争中长大,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明显表示不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在解放后很快跨入新生活。保队长弟弟经他介绍,后来成为地质工作者,而袁寿山与这位保队长,却并不能因“保护”过他而立地成佛。1949的春节,他在邹家抱房度过。即便看不到任何报纸,只从周围老百姓每次赶场带回的“议论”,也能了解解放战争的过程了。
“嗨,听说蒋委员长都自己下台啦!”
“!银元券也跟前一向的金元券样,只有拿来揩屁股喽!”
“今天场上米来了好多?一斗涨到多少了呵?”
现存社会露出了所有的败象。他感到在这样的时候,这样闭塞的地方,实在呆不下去,便捎信儿给玉颀,问能不能住到离睢水近一些的地方。4月开春,玉颀让睢水小学的校工杨志远去接他。他像个被大人允许上街玩耍的孩子,急不可耐地走出邹家“病院”。
在睢水,大家都称他杨老师。他在永兴,化名叫“王先生”……那次我去接他,中午到邹述才家,午饭后两人上路,专挑小路走。到红牌楼已经行了四十五里,距睢水还有一半。我建议留宿,他不同意,硬要走夜路。到旁边农民家要了一个火把探路,沿着大河边高一步低一步,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深更半夜摸到家里,才说吃饭的事,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①仗着玉颀和睢水小学所有的旧报纸,他消除了半年来对外界的隔膜。形势发展比预料得还快,北方的几场大战役都打完了,半个中国已经光明,黑暗正在退缩。翻阅一通《新新新闻》,他被一则私人启事吸引住。启事的大意是:鄙人年老力衰,已经多年未当公事,更从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民主同盟。现任县参议员一职,近日已呈请免去,以另举贤能云云。
他读后大笑,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他觉得一下子捉摸到这些小头面人物眼前的政治困境,以及他们拙劣的“应变”本领。他久久思考这一新的社会动态和社会心理,《炮手》的故事霍然而生。吐血以来,他许久没有动笔了。这个短篇引出整整一组“蒋管区生活实录”的小说,都是以后在板栗园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临解放前一次按捺不住的写作高潮。
吴瑞卿家是舅父把他硬逼去的。他有点恋家。从永兴回来,岳母大大施展她的烹调技艺,为他调补亏损的身子。看着玉颀和身边的三个孩子(杨礼已去县城读初中),他真不想离开。可郑慕周一听说他返回睢水,马上催他下乡。凭郑的经验,深知越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很可能正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正是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看到那张报纸,他说了一句“总算等到了”。帽子落在柴灶的灰窑里烧着,也没知觉。几天后吴瑞卿乘赶场的机会,亲来把他接走。
十年避难所遇的各色居停主人里,吴瑞卿是唯一的非权势者。这是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员,四十岁左右,做过刻字匠,性格质朴,与沙汀一家都熟。他住的地方与绵竹拱星连界。一个小院子,正面是三间瓦房,另砌一间草屋,是厨房兼饭堂,白纸糊的大窗户可以推开,显得明亮,这是吴自己设计的。最惹眼的是沿院篱笆空地一侧长了十几株峭拔茂盛的老栗子树,向天上挺着生气盎然的枝娅。远近的人给吴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板栗园。到了深秋,一斗板栗可以换五六斗米,甚至还换过一石米呢。
1949年5月11日晚上,我丈夫领来一位带行李的客人,让我叫他“杨老师”,对外不要多说。当晚杨住在紧连南房的一间破旧柴屋里。柴屋没有窗子,用木板当门,柴草扒在一边安床。一面是靠南房的土墙,三面用竹片夹起。冬天在这里过夜是冷的,但好处是能在紧要的时候,撞开竹篾墙跑进不远的山里。
他生活简单,一般不外出,只饭后在院里散步活动。我有时数了数,至少要走十六个圈圈。然后进柴屋写字。晚上,不是与我丈夫摆谈,就是在菜油灯下读书写字,半夜熄灯。
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①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园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