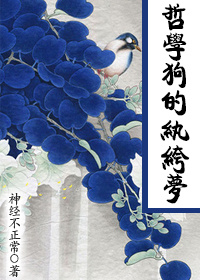哲学的慰藉-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他同许多雅典人简短地交谈后,发现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有着普遍的看法,多数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漏洞百出。而人们谈到这种看法时自信的神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的期待相反,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那些人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3.两场谈话
据柏拉图的《拉凯斯篇》记载,有一天下午,这位哲学家遇到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尼西亚斯(5)和拉凯斯。他们都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人作战,因而赢得雅典城里老人的敬重和青年的仰慕。后来,两位将军都战死疆场——拉凯斯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牺牲,尼西亚斯则于公元前413年死于不走运的远征西西里之役。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不过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同帕台农神殿上一组壁画中的两位马上骑士相似。这两位将军坚定地信仰一种被奉为常识的思想:为了证明一个人勇敢,必须参军,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杀死敌人。但是当苏格拉底在露天广场与他们邂逅时,忍不住要再问他们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拉凯斯,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勇敢,好吗?
拉凯斯:我说,苏格拉底,这太容易了!如果一个男人自愿与自己的队伍在一起,直面敌人而不逃跑,那他肯定就是勇敢的。
但是苏格拉底记得在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6)中,希腊军队在斯巴达执政官保萨尼阿斯带领下,先后退,然后才勇敢地打败了马多尼斯领导的波斯军队。
苏格拉底:据称,普拉蒂亚之役,斯巴达人遭遇(波斯人),不愿面对面作战,退了回去。波斯人在追击中打乱了队伍,然后斯巴达人再转回身去像骑兵那样战斗,从而打赢了那一战役。
拉凯斯不得不再思,然后又提出第二种常识的观点:勇敢是一种坚韧精神。但是苏格拉底指出,坚韧精神可以指向鲁莽的目的。为区别勇敢和胡来,还需要另外的因素。拉凯斯的同伴尼西亚斯在苏格拉底指引下,提出勇敢还应该包括知识,知道辨别善恶,而且不能总是只限于打仗。
于是,雅典人极为推崇的一种美德,其标准定义之严重不足就在一场短短的室外谈话中揭露出来了。这场谈话证明,原来的定义没有考虑到战场以外也可以有勇敢,也没有考虑到把知识与坚韧精神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许看来很小,但是其意义深远。如果在此之前,一位将军所受的教育是命令部队撤退就是懦夫行为,尽管撤退在当时是惟一明智的策略,那么重新定义勇敢之后,就使他的选择余地有所拓宽,并且有了应付批评意见的依据。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有一则苏格拉底同一个对一种常识观点极端坚信的人的谈话。美诺是一名专横跋扈的贵族,从他的故乡塞萨利亚到阿提卡来访问,他对金钱与美德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美诺的画像,不过我在雅典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一本希腊男人的杂志时,我想象他可能同画上那位在灯光照耀的游泳池中饮香槟酒的男人相似。
美诺自信十足地告诉苏格拉底,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苏格拉底问了他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所谓好东西,你是不是指健康、财富之类?
美诺:我的意思包括获得金银,以及城邦的显要职位。
苏格拉底:你心目中的好东西只是这些?
美诺:是的,我指的是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
苏格拉底:……你在“获得”一词前面要不要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你认为有没有区别?如果是不正当地获得的,你还称之为美德吗?
美诺:当然不啦!
苏格拉底:那么,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附加于“获得”(金银)之上……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
美诺:看起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缺少这些东西更体现美德……
美诺:看来是逃不出你的结论了。
片刻间,已经向美诺证明了金钱、权势本身不是美德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富人可能值得仰慕,但这取决于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
4.为什么别人可能不知道
话题可能会过时,但是其根本意义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
美诺和两位将军的观念不健全,因为他们没有先论证其逻辑性就全盘吸收了流行的规范。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来指出他们这种被动态度的不合理: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某些困难的活动从外表就看得出很困难;而有些同样困难的事物却看起来很容易。对如何生活有一个健全的观点属于第二类;制作陶器或制鞋属于第一类。
制陶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把泥土运到雅典,通常是从城南7英里处的科利亚斯角的一个大坑中取土。然后放在一个轮子上转,每分钟50至100转,转速与器皿的直径成反比(东西越小,转速越快)。然后进行擦拭、抹平、抛光和装手柄。
下一步是上一种与碳酸钾混合的优质黏土制成的黑釉。等釉干了以后立即放进开着风口的窑内加温到摄氏800度,烧得颜色变成深红,那是黏土硬化成为氧化铁(Fe2O3)的结果。然后再全封闭加温到950度,窑里再加一些湿的树叶以维持潮湿,这样,陶身变成灰黑色,而那层釉呈烧结晶的黑色(磁铁矿Fe3O4)。过几个小时,再把风口打开,把叶子耙出来,让温度降到900度。此时釉仍维持第二次火烧成的那种黑色,而陶身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深红色。
难怪很少有雅典人不假思索就去自己制作陶器。制陶业的艰难谁都可以充分看到。可惜,达到良好的伦理思想却不是如此,这属于另一类表面简单而内里十分复杂的活动。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5.如何独立思考?
这位哲学家不但帮助我们设想别人可能是错的,他还教给我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很少有哲学家比苏格拉底对此的要求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录中随处可见,由于其步骤一贯,很容易用说明书、手册类的语言表达而不走样,并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
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
(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
(6)不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加以歪曲,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致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盛气凌人的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作后盾力量(犹如普拉蒂亚战役和在腐化的社会中致富),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
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致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
(四)
苏格拉底在70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3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沉默,甚至杀死他。
雅典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7)位于集市之南,那是一幢庞大的建筑,一头是陪审团员坐的长凳,另一头是公诉人和被告方的讲坛。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讲话,接着被告讲话。然后由200到2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或举手表决是非曲直。这种用计算赞成的人数来决定某种主张的是非的办法贯穿于雅典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个月中有两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约3万人,应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头集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城邦的重大问题。对于城邦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等同于真理。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500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军职或文职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释说,他已献身于哲学,因此即使陪审团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他也不可能放弃: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