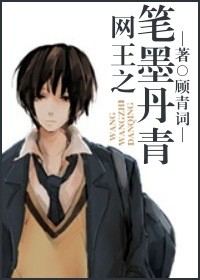我负丹青-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骰淙还庀甙担沧プ×说愕愕蔚蔚那啻菏惫狻!∫蛭挥邢滤溃』嵌冀嗨苯悠迷谠豪铮笔⒍癯簦钩闪嘶镜奈滞痢N野ǎ游薰し蚴毯蚪磕鄣幕ǎ圆辉裕⒆用撬姹阒值南蛉湛⒁熬铡⒛鹃取⒑热捶璩ぁS幸恢昴鹃瘸さ酶吖蓍埽砺桃端鼗ǎㄐ穆允┟岛欤獯耘ㄓ舻哪鹃日诟橇宋壹业钠瓢苊磐ィ⑽易髁艘淮蠓突嘶蚜髀浜M猓付缺慌穆簦<悸迹哪柑迦丛缫芽菟懒耍敢帐醭な佟!∥液臀览弦煌魅牍ひ彰涝汉螅颐切度チ税旌靡帐跹г旱闹氐#唤痰慊』婊挂睬崴桑可⑷胱约旱拇醋鳌5葡械娜兆硬⒉痪茫Jι阆孪纭八那濉保弥斗肿永辞謇砼┐甯刹康乃牟磺逦侍狻N宜娑尤ズ颖比蜗嘏┐逯旒彝停鞘乔钔噶说谋狈较绱澹颐怯诖擞肱┟裾嬲酝 N易〉姆慷业娜兆颖冉虾霉蛩抑灰桓龊⒆印S幸惶炷呛⒆有朔艿厮抵焱脱菹妨耍郎戏慷ァ糉JF〗?〖FJJ〗望,但失望了,并未演戏,原来我们一个同志的半导体中在唱戏,他们颇为惊讶。当地吃白薯干粉蒸的窝窝头,其色灰褐如鸡粪。颜色难看恶心,饿了便顾不得,但每咬一口都牙碜,真难下咽。房东看了也同情我们,拿出玉米窝窝头来,但纪律规定,不许吃房东家玉米窝窝头。夜晚,房东家炒他们自己种的花生吃,也分给我们,我们照例不敢碰,那孩子说,你们咋不吃,这花生真香。日子久了,房东对我们的防线放松了,才敢取出藏在草垛里的自行车。 我从来不怕吃苦,却怕牙碜,几乎顿顿吃不饱,逐渐逐渐不想吃了,不到半年,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学生给我寄来胃病药,无效,病了!回北京朝阳医院抽血检查,看验血结果那天,妻焦急地等在家门口,问我怎样,我说:肝炎,她脸色顿时刷白。医生嘱我卧床休息一月。我从无卧床休息的习惯与经验,感到十分痛苦。妻远去珠市口买到一张竹制的躺椅,我每天便躺在廊下看那破败的杂院,精神已沉在死海中,我绝不善于养病,也从未得过病,人到中年,生命大概就此结束了。一个月继一个月,验血指标始终不降,也找过名中医,均无效,我肯定医学在肝炎面前尚束手无策,我开始严重失眠。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严寒(1)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因病不能参加,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我很坦然。但众目睽睽,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毒害了青年。由学生写大字报来“揭”老师的毒与丑,其实大部分学生是被迫的,上面有压力,不揭者自己必将被揭。我到工艺美院后授课不久便下乡“四清”,放毒有限,而以往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已分配各地,他们不会赶来工艺美院揭我的毒,何况,是毒还是营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妻冷眼看:若不是撤消了艺术学院,我的性命难保。妻随资料室并入美术研究所,研究所设在中央美院内,暂由美院代管。在工艺美院,攻我的大字报相对少,内容也空无实证,结果我被归入靠边站一类,我们几个同代的教师,必须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系办公室坐以待命,讥称911战斗队。我抱病天天坐在911队部,一天一天送走明媚的阳光,至于院内贴满的红色大字报,我基本不看,在读谎言与闲送光阴间,我选择了后者。 抄家,红卫兵必来抄家,孩子们帮我毁灭油画裸体、素描、速写,这一次,毁尽了我在巴黎的所有作品,用剪刀剪,用火烧。好在风景画属无害,留下了,卫老那幅芍药也保住了。犹如所有的年轻学生,我家三个孩子插队到内蒙、山西及建筑工地流动劳动。接着妻随她的单位美术研究所去邯郸农村劳改,我一个一个送走他们后,最后一个离开会贤堂,随工艺美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劳动,继续批斗。当我锁房门时,想起一家五口五处,房也是一处,且里面堆着我大量油画,不无关心,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五口六处。 我们在李村也分散住老乡家,但吃饭自己开伙,吃得不错,所以老乡们的评语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只大手表。劳动要走到很远的干涸了的河滩开垦,解放军领着,列队前进时个个扛着铁锹,唱着歌,孩子们观看这一队队破衣烂衫的兵,指指点点,没什么好看,也就散去了。我的痔疮严重了,脱肛大如一只红柿子,痛得不能走路。我用布和棉花做了一条厚厚的似妇女月经时使用的带子,宽阔结实,像背带裤背在双肩,使劲挺腰将带子托住痔疮,这是一种托肛刑吧,我在服刑中种地。解放军领导照顾老弱病残,便将我调到种菜组,我心存感激。我管的一群小绒鸭有一只忽然翻身死了,于是有拍马屁的小丑报告指导员,说我阶级报复,打死了无产阶级的鸭子。指导员叫我到连部,要我坦白,我说绝非打死,是它自己死的,我感谢领导调我到种菜组,我是兢兢业业的。这事很快在地头传开了,有人问我,我说真是《十五贯》冤案,有几个同学也评说《十五贯》。指导员第二次叫我到连部,我以为他会缓和语气了,哪知他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吼:“老子上了《水浒传》了,《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过,我要发动全连批判你!” 大约过了两年,连队里严峻的气氛松弛下来,节假日也允许作画了。我的肝炎一直没有痊愈,只是不治而已,后来情况严重才让我去白求恩医院治一时期,也不见效,绝望中我索性投入作画中逃避或自杀。我买地头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制作画板,用老乡的高把粪筐作画架,同学们笑称粪筐画家,仿的人多起来,诞生了粪筐画派。粪筐画派主要画玉米、高粱、棉花、野花、冬瓜、南瓜……我这一批粪筐作品均已流落海外,是藏家们寻找的对象了。 每次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来看,便索性在场院展开,于是大娘、大伯们都来观赏、评议。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我发现了严肃的大问题: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何况画的大都是庄稼。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很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呵!他们不懂理论,却感到“像”与“美”的区别。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剪裁重组的,东家后门的石榴花移植到西家门前盛开了。有一次画的正是石榴庭院,许多老乡来看,他们爱看开满红彤彤榴花的家园,接着他们辨认这画的是谁家,有说张家,有说李家,有说赵家,猜了十几家都不完全对,因为总有人否定,最后要我揭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房东家,大家哈哈大笑,说:老吴你能叫树搬家!后来我便名此画为《房东家》。
严寒(2)
政治气氛松弛了,军队的头头们要我们作画了。能书法的、国画的被召去连部给军人们写和画。我也被召去,我还是学生时代跟潘天寿学过传统国画,大量临摹过石涛、板桥的兰竹。画兰竹最方便,便画了一批兰竹,也有同学要,随便画了就给。那是七十年代初,传来潘天寿逝世的噩耗,我利用现成的笔墨,作了一小幅仿潘老师的山水,并题了一篇抒发哀痛之词,由一位同学收藏了。 下放劳动的地址也曾转移。妻的单位美研所跟美术学院走,最后他们搬到前东壁,离我们李村只十里之遥。美院和工艺美院的教工间不少是亲属,领导格外开恩,在节、假日允许相互探亲。我和妻每次相叙后,彼此总要相送,送到中途才分手,分手处那是我们的十里长亭,恰好有两三家农户,照壁前挂一架葡萄,我曾于此作过一幅极小的油画,并飞进一双燕子。 有一时期我被调到邢台师部指导文艺兵作画,条件比连里好多了,也自由多了,上街买一包牛肉干寄给妻,但包裹单上不敢写牛肉干,怕妻挨批判,便写是药。妻因插秧,双手泡在水里太久,后来竟完全麻木了,连扣子都不能扣,她哭过多次,先没有告诉我。有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正在地里劳动,不禁想写一首诗,刚想了开头:接信,泪盈眶,家破人未亡……指导员在叫我,我一惊,再也续不成下文了。 岳母在贵阳病危,我和妻好不容易请到了假同去贵阳。途经桂林,我们下车,我太想画桂林了,并到了阳朔。抵阳朔已傍晚,住定后天将黑,我是首次到阳朔,必须先了解全貌,构思,第二天才能作画,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妻只能在旅店等候。我跑步夜巡阳朔,路灯幽暗,道路不平,上下坡多,当我约略观光后回到旅店时,一个黑影在门口已等了很久很久,那是妻,她哭了,其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地生疏,确是相当冒险。翌晨先到江边作画,无奈天下细雨,雨不停,妻打伞遮住画面,我们自己淋雨。当我要迁到山上画时,雨倒停了,却刮起大风,画架支不住,我哭了,妻用双手扶住画板代替画架,我听到了她没有出口的语言:还画什么画!到贵阳时我的食欲渐渐好转,因肝炎食欲长期不好,食欲好转意味着肝炎好转,后来检查果然指标正常了,有人认为我作画时是发气功,艺术之气功治愈了病,也许! 昆曲《十五贯》中,况钟等官员启封油葫芦的旧居,打开门东看看,西望望,用手指敲一下门、墙,便急忙张开纸扇遮、挥尘埃与落土,表演入微,美而真实。一九七三年,我被提前调回北京,参加为北京饭店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我到家,启开未贴封条的门,跨进门,立即联想到油葫芦凶宅。耗子大胆地窥我,不知谁是这屋的主人。房无人住,必成阴宅,我之归来,阴宅又转阳宅,我应在门前种些花,祝贺这户人家的复活。 大学均未开学,学院乃空城,我的全部时光可投入绘画,且无人干扰。饥饿的眼,觅食于院内院外,枣树与垂柳,并骑车去远郊寻寻觅觅,有好景色就住几天。画架支在荒坡上,空山无人,心境宁静,画里乾坤,忘却人间烦恼,一站八小时,不吃不喝,这旺盛的精力,这样的幸福,太难得。我一批七十年代的京郊油画,大都作于这一阶段。待妻返回北京,我们的家有了主持,才真的恢复了家庭。不久可雨也从内蒙被招考返京任中学教师,一直到大学恢复招生时,他考取第一批大学生,进北京师范学院重新当学生,但他最美好的年华已留给了草原牧区。他带回一双硕大的牧羊毡靴,妻为我将那双毡靴剪开,缝制成一块平整的毡子,我用以作水墨画之垫。我七十年代中开始兼作水墨画,就作这样小幅的,大胆试探,完全背叛了当年潘老师所教的传统规范。一张三屉桌是全家惟一共用的写字台,因屋里放不下第二张桌子,这桌主要是我用,其次是妻,孩子们基本用不上。除了写稿、写信、写材料,现在要用它作水墨,它兼当画案了,妻要找写字的时机都困难。我改用一块大板作水墨,大板立着,我的水墨也只能立着画,像作油画一般,宜于远看效果。 txt小说上传分享
酷暑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温度表又直往上升。一九七五年,青岛四方机械厂奉命制造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的总统车厢,邀我前去绘乞力马札罗雪山和维多利亚瀑布,然后根据油画织锦装饰车厢。我不爱画没有感受过的题材,何况又是任务,本无兴趣,但为了躲开北京的文艺高温,便接受了青岛的避暑邀请。四方机械厂中有几位酷爱美术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成了我的新朋友,尤其邹德侬更成了知音,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绘画的基础本来就很好。我的任务一完,他们便安排我们四人一同去崂山写生,我们住在山中解放军连部一间小屋内,很挤,仅能容身,好在我们白天都在山中写生,云深不知处。第一天车到目的地后,放下行装当即随车返回,因中途曾见一处景色迷人,我们到北九水下车,然后步行爬山返回宿处,一路爬山涉水,享受了一个无比开心的下午。但夕阳西斜,我们估计的方向却愈走愈不对头,山中杳无人烟,无处问路,爬过一岭又一岭,路消失了,攀着松树高一脚低一脚心里开始慌乱,因山里有毒蛇和狼,我们虽四五人,赤手空拳的人救不了自己。天将黑,终于看见了海,但还是不知身处何地。大约###点钟,有人听到遥远的广播,急匆匆朝救命之音奔去,确是逃命,但大家都不敢吐露自己的惶恐。月光亮起来,广播声渐近,望山跑死马,我们终于到了平地,进了村子,夜半敲开了老乡家的门,歪歪斜斜挤在柴屋里待天明。此地已不属于我们所住连队的那个县,而是另一个县,翌日吃了老乡们捕的活鱼,大队里派了一辆拖拉机送我们回宿营地。我后来捡回拳头大的一块山石,青岛一位同学王进家便在上刻了“误入崂山”四字,此石今日仍在我案头,天天见。在崂山住的日子不短,管他春夏与秋冬,大家画了不少画,邹德侬作了一小幅油画,写生在写生中的我,形神兼备,我为之题了首诗,已只记得两句:山高海深人瘦,饮食无时学走兽…… 我提前从农村调回北京,为了创作北京饭店的壁画《长江万里图》,那图由设计师奚小彭总负责,绘制者有袁运甫、祝大年、黄永玉和我,袁运甫联系各方面的工作,稿子酝酿很久,待到需去长江收集资料,我们从上海溯江上重庆,一路写生,真是美差。在黄山住的日子较久,日晒风吹,只顾作画,衣履邋遢,下山来就像一群要饭的。我们去苏州刺绣厂参观,在会客室听介绍后便去车间现场观察,离去时发现祝大年的一个小包遗忘在会客室,便回头去找,正好一位刺绣女工将之送来,她十指尖尖,用两个手指捏着那肮脏的包拎在空中,包里包外都染满颜料,她不敢触摸。我们一路陶醉山水间,与外界隔绝,但到重庆时,情况不妙,才知北京已展开批黑画,催我们速返参加运动,壁画就此夭折。我利用自己的写生素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效果不错,人民大会堂要求移植成横幅,我照办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