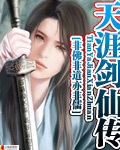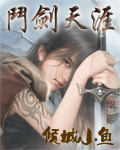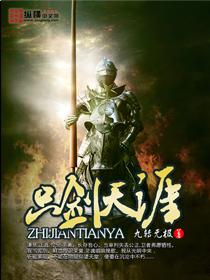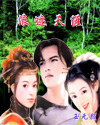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处理安排——家用请他交给三姐;衣服杂物叫他送人也都送到了;他办事从来有条有理的,我们到美国后,他把我们的书都陆续寄到了。现在还在家里的那部《四部丛刊》全本,就是他给寄来的——那要花多少工夫呀!」老人的记忆,似乎忽然都变得明晰敞亮起来了,「对了,我都想起来了,他是那家叫『修绠堂』的小书店的伙计,当时才二十二岁。一九七八年我们第一次回中国——是汉思跟余英时他们一起先去,我随后跟着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他早已经不卖书了,转做研究工作了,他学问做得很好,也常常写文章。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要书,还找过他。我们从他那里,也帮赵元任要了一部《四部丛刊》,为陈世骧也order (预订)了一套。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了。」
我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当时,还带着另一个女工人上的机场?」
「对,这又是另一段故事。」张先生微微笑着,「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后来,那位小挎奶奶,一直跟着你们么?」
「我们从青岛,先折回到苏州。小挎奶奶一直跟我回到苏州,就留在了苏州老家。小挎奶奶随身带了一个重重的包袱。到了上海我大姐家,我说:『你打开包袱,让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宝贝。』她打开来,都是一些破衣服,还有刷窗的刷子——因为出门前正刷着窗,她就把刷子也带过来了。逗得我哈哈大笑。」老人脸上溢满了笑意光彩,「汉思跟着我回苏州小住了一阵,南方也已经乱起来了。转眼到了四九年一月,我们从苏州出来,托人到南京办手续——按说我要跟汉思去美国,要办护照、身份什么的——可是南京已经不行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帮我们办手续的人,原来他已经从南京逃出来了。他叫郑泉白,扬州人,与丁西林是朋友,曾经到德国留学的水利工程师。记得他受过伤,有一条腿是义腿,他德文很好,国学也很好。对了,我画的那幅章士钊等很多人题咏过的《仕女图》,就是打仗的时候,在重庆大轰炸时,在他家画的。他的办公室连着防空洞,我在重庆时总是上他家去躲警报。他当时在中央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和他们在一起。傅斯年脾气很坏,人家把东西堆在防空洞门口,他就大骂。我当时的上司是陈立夫,教育部长,他平时在青木关上班,有重要的事情才到重庆的办公室去。那时我在他手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平时就跟丁西林、郑泉白他们玩在一起……」
老人又散漫地说了开去,我却还惦记着小挎奶奶的故事。
「小挎奶奶呀,总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当时二十一二岁,后来她就留在我们苏州家里做事,跟他的丈夫也团圆了。我走那天,我要吃一顿饭才上船,她要送我,我不让她去,她说她没看过大船,其实是找个理由,坚持要去送我。她看着我上船,就哭了,哭得很厉害,」老人敛住了笑容,「那以后,我和汉思就从上海上的船,到了美国。」
窗外一抹雪后初阳。老人轻轻结束了这个异国鸳鸯逃离战火的故事。「这是一个抱着一部《四部丛刊》去国弃家的中国女性。」我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浮起这句话。其实,那部《四部丛刊》,是李新乾日后为她寄到美国去的。深深留在我视野屏幕上的,还有那位手脚麻利的书店伙计和那位「小挎奶奶」,在乱世中与「张家四小姐」命运相纠结的素朴身影。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
张充和谈美国岁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充和与她的美国夫婿傅汉思,在上海港上了「戈顿将军号」(General Gordon)海轮,前往美国,开始翻开她多彩人生的新的一页。
「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汉思父母家在斯坦福,我们在他家住了一阵子,后来汉思在伯克莱大学找到事情做,我们就在附近的伯克莱安居——哎,你今天不赶着去上课吧?」张先生顿了顿,缓声向我探问。往常探访老人,我总是把叙谈的时间掐在一个小时左右,谈完一个话题就及时收止。主要是不想让老人太累,完后我再赶往学校去上课。但我见老人今天谈兴很高,便告诉她:「时间还充裕,只要你不累,我们可以顺着话题往下聊。」
张先生在沙发上换了一个坐姿——老人从来都是坐姿端庄、仪容端整的,向我娓娓道来——
「汉思的博士念的是诺曼斯语研究,可是回到美国他就不想再做诺曼斯语了,他想转向中文。赵元任他们那时候正在伯克莱,也很鼓励他。可是你知道,他已经有一个Ph。D了,要转一个专业方向,没那么容易啊。」老人眯缝着眼睛,好似回到了那一段筚路蓝缕的岁月,「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穷,没什么钱。汉思在伯克莱一直是做part…time(兼职),他的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教中国历史,有时编编刊物——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整整十年,汉思都没有一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
「整整十年?可真不短呀!」我感叹着,想起自己在美国大学求职的经历——前后骑驴找马地花了六七年,已经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我那时候在伯克莱的图书馆做事,倒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我知道他就卡在一个与中文有关的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 D!』」老人的语气变得短促、坚定,让人想起这位「张家四小姐」因为自小离家而养成的那种独立、执著、自助自强的个性。「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了八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汉思后来申请上了哈佛的中文博士课程。他在哈佛的朋友很多,也很了解他,都知道他本来就拥有博士学位,就说,『很多课你都不必修了,你就多写文章就行了。』一九五九年,汉思在斯坦福拿到第一份正式的教中国文学的教职,我们便在斯坦福待了两年。那两年我就不做事了,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左)傅汉思(1916—2003) (右)傅汉思与胡适
「你的两个孩子……」我正要开口询问,老人接过了话头,「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抱养的。男孩子在伯克莱的时候抱过来,那时才刚出生,今年整五十了。到了斯坦福再抱养了一个,是女孩……」
老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在美国,照料孩子,一般是请不起保姆阿姨的。这位从小就在「干干」(奶妈)和保姆怀里长大的「张家四小姐」,在异国异域与夫婿一起白手起家,抚育教养一对儿女,其间经历了何等的艰辛,老人却没有多言。我本来想问她:在那些日日面对尿布奶嘴、柴米油盐的艰困琐屑的日子里,你还能花心思在书法、昆曲和诗词上么?话未出口,又觉得多余——前面不是刚刚还谈到,胡适喜欢到她伯克莱的家中写字;《曲人鸿爪》的第二集,不都是那一个时期度曲、唱曲的留痕么?
「汉思是一九六一年到的耶鲁。耶鲁一开始给他的就是副教授的职位,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安定下来了。一晃眼,在这里也住了好几十年了。」 张先生环望着眼前的老宅,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我知道,在美国大学,副教授一般即是终身教职,往往需要熬六七年时间才能得到,耶鲁对此的要求更高。显然,汉思在那时候的学术成就,已经让校方「另眼相看」,并且很快,就升任正教授也即终身教授了。「我在耶鲁又恢复了做事,一直在他们的美术系part…time(兼职)教书,主要教中国书法,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还不时被耶鲁博物馆请去,帮忙给他们东亚部做事。」
一九八○年代,傅汉思、张充和夫妇与到访的何兆武教授合影。
耶鲁校园掠影
耶鲁校园的大钟楼
我提出要求:「给我具体说说汉思,说说耶鲁这一段的生活吧!」
「汉思的朋友多,人缘好,从来就没有什么复杂心思,」老人微笑着接过话题,「你欺负他,他也不知道,我就常常欺负他……」
我笑问:「你怎么欺负他呢?」
「他性子慢,我快。他一慢,我就急,俩人倒也没吵过什么架。可是说来也奇了,」老人笑眯眯地比着手势,「他性子慢,可比我的事情做得多;我比他快,可做的事情反而比他少,你说怪不怪?他不爱说话,闷头闷脑地做事。他对中国历史比我还熟,文章写得很多,做出的事情,一件就是一件地摆在那里,让我不得不服气。」
老人的语气里略带调皮,让人想起她个性的多面:娴静里不乏活泼,恬淡中藏蕴着锋锐、主见。
「在耶鲁这些年,我有两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安娜,她是早年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学中文的,会昆曲,她的老师就是我从前老师的学生。她的笛子吹得很好。这些年我唱昆曲,都是她给我吹笛子伴奏。她一直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好几年了。另一位是咪咪(Mimi),她是美国人,原来在耶鲁博物馆做事,后来去了西雅图,做了比尔·盖茨的继母。」
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比尔·盖茨,就是那位建立计算机微软王国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么?」
「对的,」老人笑着点头,「我认识咪咪的时候她还是汉思的学生,跟我学书法,学草书,她后来留在耶鲁做事,做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她人非常好,在这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一直给她帮忙。后来她到西雅图博物馆去了,在那边认识的比尔·盖茨的父亲。去年,我在西雅图办的那个『古色今香』的展览,就是咪咪请我去,并亲自操办张罗的。我在那里,也见到了比尔·盖茨。」
我想起去年老人从西雅图回来,送我的那本装帧精美的展览图册,心里恍然一亮:坊间都传说比尔·盖茨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近期宣布隐退后,首先在他的慈善基金会里专门设立了数目庞大的中国基金,举世震惊。我想,这一定与他有一位懂中文、专门做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继母有关吧?
没想到,一生与中国现代史中各种精彩人物有着广泛联系的张充和老人,在她的耶鲁岁月里,也与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的精彩人物,发生着如此间接却紧密的联系,这,真是我今天的一大发现。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二十一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关于「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的公案
那天,和张充和先生随意聊着那些旧人旧事,说着说着,又说起胡适来了——在我们近期的谈话里,胡适会不时成为重复「闪回」的话题。其实我注意到,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沈先生」,胡适之,这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张充和的生命里程中,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既是充和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那段著名恋爱故事里的大月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撮合作用;也是张充和当年以「张旋」的名字报考北大,以国文考试满分而数学零分,最终得以破格录取的关键性推手(胡适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但并不知道「张旋」就是张兆和的四妹);更是七七事变后,亲自在南京《中央日报》社(时张充和正顶替到英国留学的储安平,主编了一年多《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当着报社老总程沧波的面「强令」张充和马上离开南京,避过了随即逼临的烽烟战火的那位「救命长辈」。多年来,从一九三○年代的北平、南京,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后的美国生活时期,他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保持着亦师亦友、时相往还的亲近联系。
于是,我们谈起了一个敏感话题——关于「左」、「右」。在张充和生活、成长的年代里,这是朋友交往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战前,左、右两方面的朋友我都不少,也都有不错的关系。」张充和淡淡地笑着说,「我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要么不会跟我交往,要么这交往肯定跟政治无关。」
老人的话说得条理明晰。我心里,忍不住悄悄地在张充和的人生故事里 「画线」:若按左、右站队,她少女时代的老师张闻天、匡亚明,去过延安的卞之琳,左翼文坛的章靳以、巴金、老舍、黄裳,等等,自是属于「左营」的;「右营」呢,如果定义为自由派的文化人算「右」,胡适之、张大千、梁实秋,等等,则就光谱繁复了。但是,更多的,比如沈从文、沈尹默、杨荫浏,等等,其实「色彩散淡」,不容易这么二元对立……
她喝了一口茶,娓娓地谈到了胡适:「七七事变前,我在南京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那时候形势已经很紧张,我想赶回苏州老家去。胡适到报社来找社长程沧波,我去看他,他要我马上离开南京,听说我要回苏州,连连劝我说:『不要去,苏州回不去了!你一回去,就出不来了!』可是我不听劝。那时候已经兵荒马乱,苏州家里有个大摊子需要收拾安排。父亲办的中学那时候由我大弟张宗和当校长,与一位教务主任一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