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东风吹世换-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历史解读篇
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
〔文/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
〔文/悍马狂飙〕
这是一部在地下沉睡了500多年的史书,当战国时代魏国的那位史官在用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冷酷的笔触写下这部史书的时候,他必定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却成了颠覆儒家主流史学话语的惊世之作。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也有种说法为太康元年或者咸宁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有人盗掘魏国古墓,结果发现了一大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统计有十几万字,这就是对后世学术史有重大影响的“汲冢书”,西晋政府相当重视,派一批学者进行了整理研究,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来的就有这部著名的《竹书纪年》。
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前299)之间的历史,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记载能与甲骨文、金文、《史记》、《春秋》等多方面的资料相印证,真实可信,并且能够纠正现存史书的谬误,如《史记》中关于战国年表中的混乱错误,后世史学家通过《竹书纪年》重定年表,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不可或缺的主要依据。《竹书纪年》的出土和整理,还刺激了晋代史学的发展,编年体史书大量出现,比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等等,史学彻底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南朝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竹书纪年》在晋代这一学术转变中与有功焉。
然而更大的意义是:《竹书纪年》的发现,是对以儒家历史观为根基的春秋——左传——国语系统和后世的《史记》——《汉书》系统的一次重大颠覆(《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并非儒家,但其历史观受儒家影响至深却是事实)。根据《晋书·束皙王接列传》记载,与后世儒家经典大异的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是对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的一次八级地震般的颠覆。原先被儒家形容得穆穆雍雍、和谐谦让的所谓“禅让”,竟然是“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其实这也不是儒家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难》)
商代的伊尹是有商一代著名的辅臣,儒家的历史评论中是这样描写他的:新继承王位的太甲不听伊尹的劝谏,暴虐乱德,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自己摄政,后来太甲悔改从善,于是伊尹将他迎回而授之政(《礼记·缁衣》)。伊尹也就这样成了贤相忠臣的典范。然而《竹书》一下揭穿了这个天大的谎言:伊尹想篡位自立,于是监禁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的太甲找机会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将一个篡位谋政的枭雄说成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儒家史学在这里简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没有人怀疑,以厚黑学闻名于世的李宗吾就对儒家的史学体系提出过质疑:“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许有部分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某种愧疚。
欧阳修自负“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纪上赫然写着“契丹立晋”,成了后世的笑柄,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无疑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把人放到油锅里
〔文/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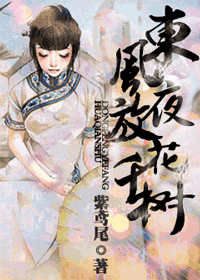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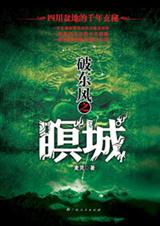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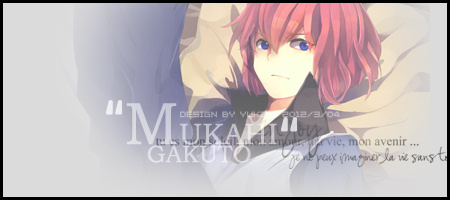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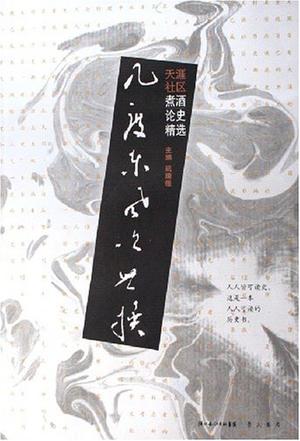

![[综仙古]墨迹未残闻弦歌·东风不还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32/328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