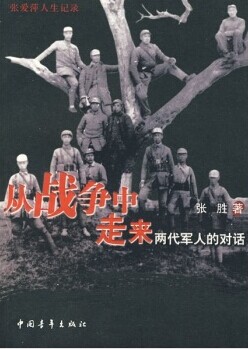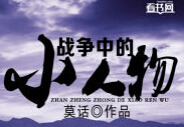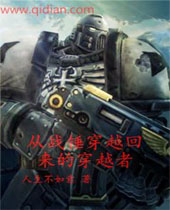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讲到这里,父亲解释说:“这个家伙起劲得很呢,句句上纲。我奇怪,他怎么讲得这么具体,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记得一清二楚。真是个有心之人!这几个月里,他可是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提过啊!”)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我们都笑了,用北京土话说,您老真够能矫情的!父亲自己也笑了,说,我的水平,开开他们的玩笑还是可以的。)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这种人,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前些年,我曾托一个认识毛远新的朋友,特意当面问了这件事。毛远新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
能相信他吗?舒龙山10月1日的信是何时到达毛泽东手中的?何以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和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都是在同一天?11月2日这一天。这不应当仅仅看作只是一个巧合吧?
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信。
毛泽东在张爱萍和舒龙山之间选择了后者。
父亲时常回忆起在长征路上,面对横在红军面前呼啸奔涌的金沙江水,毛泽东交给他任务的那个晚上。战史是这样记载的:“……由军团后卫改为前卫的红11团到达皎平渡后,该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第2营和侦察排先行北渡。这支部队抵北岸后,即穿过敌军间隙西进,设法与南岸红1军团取得联系,传达了中革军委要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然后,即在龙街北岸渡口,担负堵截滇军北进的任务。”(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65页)
父亲回忆说,是彭德怀带着他去受领任务的,他也是看着中央纵队和毛泽东登岸后,经过了他的掩护阵地北上的。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他率领红11团的将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征故事,大多是前卫部队的辉煌战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父亲说,断后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前边的大队人马过去了,就什么吃的也找不到了。他说,能执行断后任务,是光荣,也是信任!
不!毛泽东应当记得,起码他相信。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信任他,在金沙江畔托付了他这副重担。父亲对我说,长征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在他那首着名的长征诗中,只记录下了有限的几个地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
他孩子般的相信,金沙江的滔天巨浪,毛泽东不会不记得的。
他也常回忆起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回忆起自己那次打了败仗去见毛泽东时的难受心情: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今天你们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他回忆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叫他去组建海军,为解放全中国未雨绸缪;他那次给毛泽东照相,用的还是莱卡相机,底片和相机至今都还保存着。
现在,他们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的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吗?想打倒就打倒,想关押就关押,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之所以敢冒大不敬之罪,能够这样去做,敢于这样去做,不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吗?是毛泽东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代共产党员;毛泽东教给他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是背叛毛泽东?是不是丢弃了革命的理想,成了既得利益的官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那些鼠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父亲的心态是恬静的,他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时的那种委屈和困惑。他甚至认为,厄运这次又光顾了他,应该是个必然。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
像1975年的这次整顿一样,1962年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动因都不是出自于认识上、理论上的自觉,而是摆在面前严峻的现实。“饥饿规律”有时也是会逼得人们去突破“左”的理论束缚的。一方面在喊坚持三面红旗的口号,一方面在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多公布的文件看,毛泽东似乎并不打算这样快的就结束1975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两年就结束这场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想把魔鬼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不可能没有反思的。9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一个国家如何经得住如此折腾?要迅速结束动荡,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出山,有了1975,有了整顿铁路、整顿七机部……但这一切是要有代价的,这使他在晚年面临着两难抉择。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因为1966年他的行为多少带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实林彪死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错过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毛泽东的好意,左右两边都不接受。毛泽东曾要邓小平主持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定了口径:三七开。但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毛在记述她的父亲邓小平时写到:“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但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慎重的,他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不至于天平过于倾斜。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个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11月22日又批示:“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反倒会增加复杂因素。23日又批示:“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从口气看,显然,他并不赞同七机部的派性。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1975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王曾找过父亲,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没两天,邓小平就找父亲询问这件事。后来我们知道,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可见当时斗争的错综复杂和人心之叵测。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历史永远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筹码,虽然中央已经为此做过两次结论了。
科委参谋长李光军借随造反派来病房批斗我父亲的机会,背对着其他人,在我妈妈面前伸出手掌,在手心上画了三个点。我妈妈后来说,李光军是在暗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