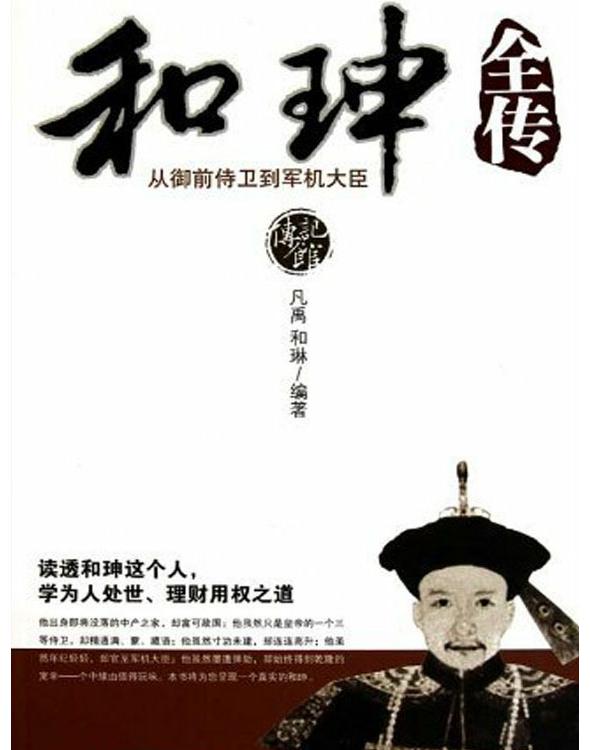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言词,强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都泪眼汪汪的。这样子挨打,心理上的恐惧更大,因为在别人挨打时,自己已经害怕不已。就是没有挨打的同学,看着一个个红着手心回座的同学,听着鞭子咻咻咻的声音,在座位上也给吓得要命。
记得有一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不见了,便报告老师,班导决定要好好查一查,就要全班同学都站到教室四周去,所有的座位全都空了出来。
老师先准备好了要打小偷的大棍子,记得一共两根,就是打算可以打断一根。足足有李小龙的双节棍那么粗,放在高高的讲台上。然后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桌子搜查。终于,在某位同学的桌子里搜了出来。老师命令这位同学站在讲台前,用大棍子痛打,连衣服都打破了,我看简直会把他给打死。小朋友站在教室四周,一如死刑犯执刑时的陪斩,个个脸色发白。
多年以后,我在国外遇到这位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却不认得我,后来又听其他的两三位同学说,这位同学也不认得他们。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再面对。
打人的老师早已作古,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为,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伤害有多深。
但是小孩子也不见得对此有不同意的想法,老师打学生的藤鞭永不缺货,因为总有小朋友会找到很合用的呈献给老师。老师得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一边称许一边摸摸他的头。同学也很少会恨这样的同学,只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就是没有人专诚送鞭子给老师,老师自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直到中学还挨打,我上建中的时候,一位英文老师,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他写过一本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辅助教科书。他会打人,随手带着一根细细的藤条,谁让他看不顺眼,他就叫上来抽他几鞭。班上有一位胖胖的同学,不记得什么事,他叫这位胖同学上台,二话不说抽上几鞭,边抽边以一口京片子骂道瞧你肥的,台北都让你吃穷了!
这位同学却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任他一鞭又一鞭地上下地抽。后来这位老师大概想想也不是事儿,只得停止。我对这位同学从此刮目相看,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做了许多在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事。
但是我在学校中挨打的机会很少,记不起来有哪位老师打了我,虽然我也不是个好学生。大概看起来我总是安安静静、斯斯文文的吧?
我遭遇的是一个长期的暴力家庭。
也许我说暴力家庭不太贴切,姐姐就不会挨打,她有一种天生的娇贵气质,让人打不下手。就是真的挨骂,姑妈骂她的语句好像也会文雅些。重要的是,她也没有让人为她读书跟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操过心,她不会逃学,不会不做作业,不会撒谎,不会考试不及格,更不会留级。她太柔顺,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完成,没有人找得出打她的理由,连骂都不必,对她把话稍稍说得重了点儿,她就会流泪。这也证明有的人挨打真有个人的理由,虽然也不可因此就可以把体罚合理化。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
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问我对于打过我的父亲、姑丈、姑妈,我会原谅他们吗?我的回应就是,要是当时,我说在当时,我有能力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反抗!一直挨打的不一定是我。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
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姑丈姑妈家,后来他们全家住在我们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教育就从姑妈那里得来的,算不算家教很可以质疑。连同姑丈跟姑妈的孩子,一共六个,大家吃得饱就不容易,还要讲究其他也许过分。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孩子比我们更穷,却没有打骂孩子的父母尊长。穷困也不必然可以成为打小孩的理由。
长辈总是相信为了什么理由,一定要打打孩子,否则将来会不得了。其实,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挨打的经过,至于为何挨打,记得住的很少。姑丈跟姑妈联合起来打我,总是在父亲出门之后。他们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方便另一个人用棍棒痛打。我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怎么可能反抗?我忘不了被提在半空中挨打的恐怖,简直是天崩地裂,巴不得当时我不在这个世界上。恐怖不是从挨打才开始的,挨打之前,风雨欲来,我全身的细胞个个紧绷,我的房间是在一处无路可逃的小屋,只有任其拖出痛打。
我死命地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想要拖延挨打时刻之到来,一分钟半分钟也好,但是依然徒劳。我被即将承受的痛苦吓得不知所措,甚至于装疯卖傻,也许那个时候真的已经疯傻了。我看着我的姐姐,她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觉得靠得住的人,然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打,我就像在大海中即将淹没的人,只有一根太细太短无法承荷我的浮木,我依然被淹没在恐怖的鞭挞中。我姐姐只能不声不响地在一旁流泪。我至今还要说,想起来我依然愤怒,我不会原谅任何以暴力加之于我的行为,只是无可奈何地放过了便是。打我的人都老了、死了,我又能怎么计较?纵使我依然痛恨那样的岁月。
以后我读书读到了孙庞斗法,其中孙膑曾经使用过装疯卖傻的“诈疯魔”一计,我总怀疑有用没用?人是会让人给逼疯的,我非常相信。
那一年,我应当还在小三,跟姐姐两人,都还在姑丈姑妈家一起生活,就已经开始挨打了。
有一次,挨了打回到房间,只有姐姐陪着我。我一边流泪一边说,人生这个样子,还不如自己出去流浪,姐姐只有陪着我哭。这该是一个才八九岁的小男孩说出来的话吗?常常挨姑妈打,她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十岁吧?梳一个四边往里卷的发型,后来我在东京买到一本早年的人物摄影集,手工染色的,那个时候方才发现,她那时的发型,跟早年日本女子是一样的,那种发型给我的记忆相等于恐怖。至少有一阵子,我想要减少这种恐怖的感觉,在准备考试或是做功课的时候,常常幻想姑妈变成小小小小的,像小人国里的人那么小,小到不及半根铅笔高,我相信她缩小了之后,就不会那么恐怖了。我的想象越来越具体,我看到了许多的小小的姑妈从窗沿爬上来,到了书桌上,一个接着一个,站满了一桌,然而,猛然间,我打了个寒战,那么多的姑妈!我的天啊!
姐姐马渝光(左为台大毕业之前)
最早挨打的记忆是父亲的暴力。
也许还没有满六岁,我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几句小孩子不该说的脏话,那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懂。我在厨房里跟我们家的女仆锦娘说,反反复复地说,开心得很。锦娘要我别说,我却偏偏要说,十分快意。
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回来了,锦娘顺口就跟父亲说我讲脏话,父亲只随口应了一句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啊。
当时的心理状况,现在终于可以理得清楚些。
我只是一个还不满六岁的小孩子,在跟锦娘说话的时候,正享受着叛逆的快乐,小娃娃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跟言行。越是不让我说,越是说得高兴。刚刚好父亲也给了我一个可以继续叛逆的机会,我的叛逆享受还没有过完瘾呢,锦娘的反应,父亲的言语,都伤害了正在得意的小家伙的自尊,于是我就跟在父亲身后,拿着鞋拔子在他背后打了一下。
父亲回身把鞋拔子夺了去,放好了公事包,返身抓住了我,轻轻松松地提起我来,痛打了我一顿。我哭得天昏地暗他也没饶一下子。这是我记忆里头一次挨打,到死也忘不了。想当然耳,父亲也好,锦娘也好,甚至于现在许多人也会这么想,这个孩子再不打真的不行了,连对老子他都能动手,怎么得了!趁早教训教训还来得及。因此在我挨打的时候,锦娘也没有来救我。他们哪有什么儿童心理的分析能力?或是意愿?
父亲打我最凶的一次,让我深信我可能让他给打死。
好像是为了逃学吧?反正我的罪过太多,弥天盖地的。当时我应当上中学了。我睡在一间榻榻米的房间里,晚上得挂上一方大大的、日本式的、快要跟这间屋子一般大的蚊帐。半夜里好梦正酣,忽然间帐子整个地掉了下来,覆盖全身,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小腿骨忽然遭上一记猛烈的敲击,痛入骨髓,登时酸麻得无法挪动,还没有来得及醒转,碗口粗的大棍子上下左右不分头脚地只顾一记记地轰轰然炸了下来,困在网中,我连闪避的气力都使不上,只得蜷缩成一团,任父亲打到他住手为止。
以后许多年,要是我先睡了,只要父亲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传来,我会霎时清醒得透透明明,一直要听到他也睡下,才能再度入梦。
后来我离家出走,终于可以安睡到天亮。
还有一次,我正在打盹,忽然之间耳边响亮的一声爆裂,接着类似金属相击的回声不绝,满眼金花,原来我挨了一记耳光,就在我准备考试,支撑不住,打瞌睡的时候。给我这一记的是我姑妈。第二天我就带着脸上五指的红印子上学去,当时恨不得死掉算了。至今我依然相信,会那么样在孩子睡着的时候,狠狠地来上一记,心态很不正常。要是大多数的长上都这样,那么,我曾经经历过一个狂人充斥的世界。我一直怀疑,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家,就像是个疯人院。
要是闯的祸太大,姑妈就要亲自跟父亲说,然后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