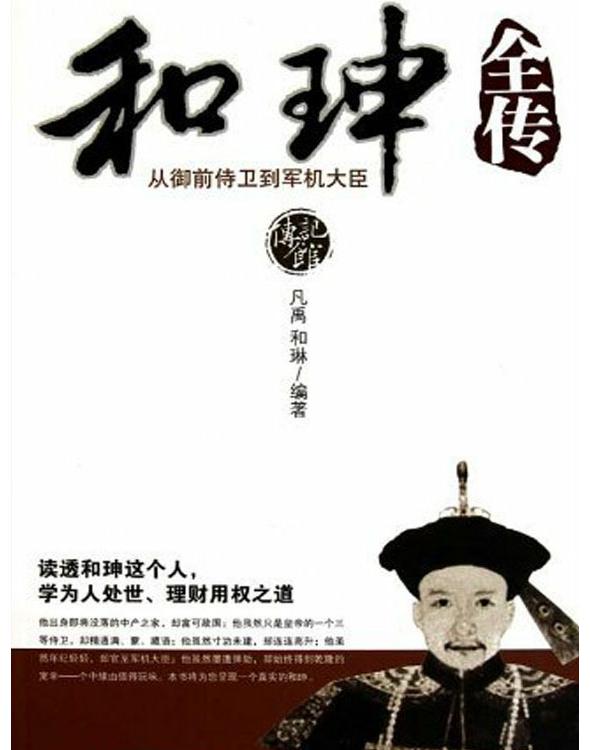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要走很远,才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上厕所没有问题,只是路远些,去火车站跟东西公路局总站,二十四小时都很方便。太急了的话,就只好在大垃圾场边上解决了。带动台湾经济的许多龙头人物的名字,如尹仲容、李国鼎、陶声洋、汪彝定、李达海、王昭明、赵耀东等,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很穷,移民潮天天都有,好像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远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好。
那个时候,林良国欢迎我住他家。
家,对我的同学,后来直呼他为阿兄的林良国来说,似乎要重新定义。一个是由人组成的家。另一个,是他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的家。这两者,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
林良国总是独来独往,他有父亲,但是很难得见一次面,父子二人都在台湾,但是各忙各的,父亲住在何处他似乎也不太清楚,我见过,很斯文,只会说福州话,因此他们父子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许会带一点钱给他,但都不是定期定额的,他得自己想办法赚到钱生活。林良国也有亲戚,比如他的舅舅,就在西门圆环红楼边上开了间杂货店。还有一位他唤作叔叔的,靠捡破烂为生,捡来的许多东西,我看依然是垃圾,居然就堆屋里,他陪着他捡到的破烂睡觉。但是这一位叔叔却很有一点武功,谁要是欺负他,他伸出二指,便能擒拿对方。那个人瘦瘦小小,跟林良国讲话,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他还有一位叔叔,有婶婶,也有表妹,但是住得很远,也是生活得不容易,大概这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了。
他的住家,自然无水无电,是个小到无法再小的阁楼,一把木头扶梯靠在经常潮湿的泥土地上,下面住的是推车卖面的,很少看到人。上了扶梯,头就要碰到屋顶,就那么点儿三角形阁楼的空间,却住了三家人。跨过去就是那位收破烂的叔叔,只一张三夹板做墙。隔壁姓陈的,也是他们的同乡,陈家三口,只有两个榻榻米都不足的范围,他们在林良国住处的后面,那就连窗子都没有了,没水没电,从早到晚只是昏昏暗暗地过日子。拉开扶梯边上的门,勉强还能立着,然而屋顶一路斜下去,到了一个人身长的尽头,只好躺下,跟睡在楼梯底下一样,只是更狭窄。勉强睡得了两个人,而我的阿兄却非常好整洁,每天要擦一遍铺在地上的草席,但我一次也没有劳动过。我生活作息不规则,给他带来的麻烦当然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不豫之色。多年以后,在闲谈中,他说道,你是落难来的,我不能让落难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