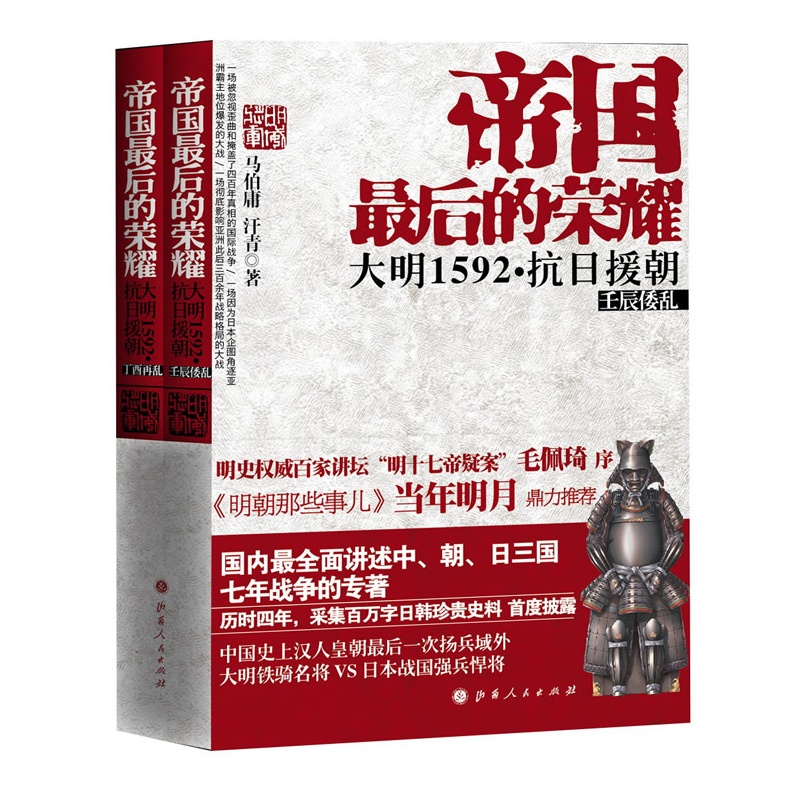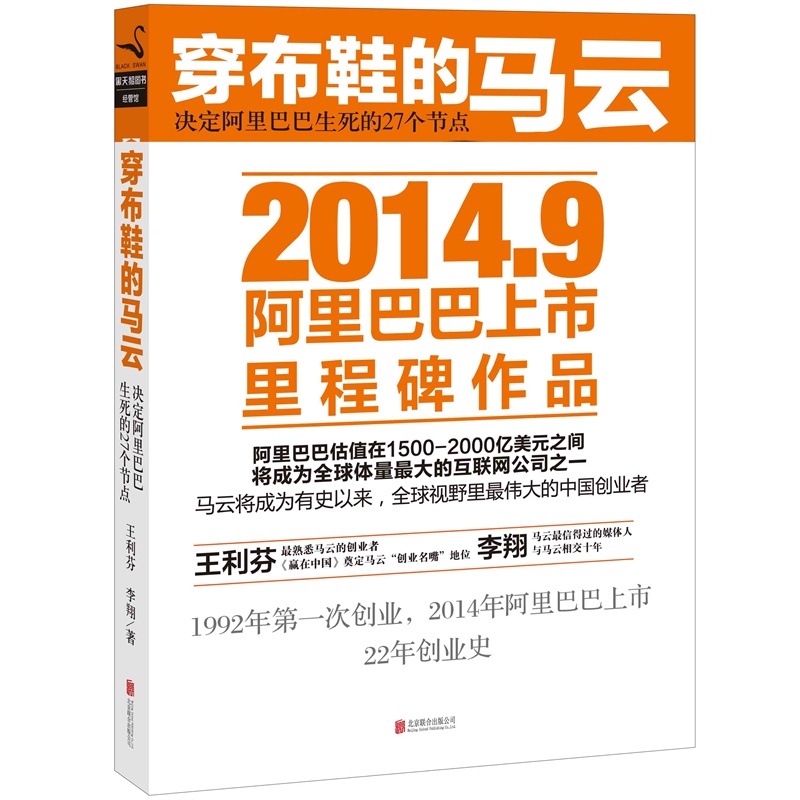鬼嫁(出书版)作者:公子欢喜-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他。
惊魂铃激越高亢,鬼气森森,房门无声开启,灌入满院风声。黑暗里,一道纤细的身影渐行渐近:「山野精怪,漏夜造访,实属万不得已,望请国师大人海涵。」
话音方落,人到眼前。是个女子,浅笑盈盈,眉如新月:「小女子初雨,见过傅掌教。」
「雨姑娘。」时常被鬼魅挂在嘴边的名讳油然跃入脑海,傅长亭神色一紧。
穿一身碧色衣裙的女子却从容。她挥袖将洞开的房门掩上,随著面上渐渐泛起的温婉笑容,一阵淡淡的幽香在房中缓缓弥漫开来:「听闻道长在找东西,小女子倒是有一件,只是不知是否正是道长要找的。」
轻移莲步,她嫋嫋站到圆桌另一头。隔著四溢的鬼雾,女子螓首微垂,笑得柔顺得体。她的手中握著一把木制的小刀。
傅长亭急忙伸手抓去,挥起的衣袖险些把烛台带倒。女子笑容亲和,全然不在意他的莽撞。「看来是了。」她话语欣慰,屋中的香气因之变得稍许浓烈。
木刀是孩童的玩具,雕工不见得精致,木料不见得考究,可是做工却费了十万分的心思,从刀尖至刀柄,不见一根木刺。韩觇在湖边喝醉的那个夜晚,他亲眼见他将之丢进湖里。醉了的鬼魅胡言乱语,说他做了很多。
以手为刃,傅长亭手起掌落,木刀立时一分为二。原来,内里居然中空的,一张纸笺轻轻飘落到桌面。纸面上寥寥四行,是一首打油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君子路过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与拨浪鼓中的如出一辙。
在她的示意下,傅长亭以手为刃,手起掌落,木刀立时一分为二。原来,内里居然中空的,一张纸笺轻轻飘落到桌面。纸面上寥寥四行,是一首打油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君子路过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与拨浪鼓中的如出一辙。
「起初,他们总是哭。凡人听不见,我们却听得分明。」被拘锁在湖底的幼童魂魄因为惊惧害怕,惶恐不得安宁。每到日落,哭声自水底传来,霖湖岸边风声尖啸。凡人无知无觉,兀自酣然沈睡。鬼魅就坐在湖边的石亭下,侧首聆听,从子夜到天明。
迎著道者冰冷的眼眸,她用平静的口吻如实相告:「兄长嫌他们太吵,所以往湖里丢这些小玩意。道长是天上真君下凡,恐怕有所不知,虽说人鬼殊途,不过鬼界同人间终究还是一样讲人情的。些许小贿赂,总能买到一夜无忧。呵呵,他口中这麽说,实则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呀……」
一声长长的歎息,撩起房中暗香浮动。一个拨浪鼓,几只竹蜻蜓,有时或许还有两根糖人。小小的礼物抚慰了孩童们的不安躁动。
血阵内的怨魂接收不到家人的供奉祭祀。那鬼用纸笔写下凡间安抚小儿夜哭的打油诗,夹带在送给他们的东西里。
「多少算是个安慰。」初雨轻柔地说道。
鬼雾在道者眼前起伏游走,丝丝缕缕的幽香随著雾气的弥漫散播到房内的每个角落。傅长亭听见屋外又开始下雪,「簌簌」的落雪声应和著桌上烛台「毕剥」的轻响。冰粒在叩打纸窗,寒风穿透了窗隙「呜呜」哭泣。
「有时,他会自己站在湖边念三遍。」女子清丽的容颜在稀薄的雾气里时隐时现,她掩著嘴,轻轻笑出了声,「要君子念才有用的。不过,後来他们真的不哭了。」
丝帕胭脂送给枉死的闺秀,纸砚笔墨赠与不甘的书生。偶尔,他还会让山楂做几样精美的糕点,端午的豆沙白粽,中秋的果仁月饼,大年三十不忘多加几颗蜜饯果糖……有时,他也会在纸上写点别的,超度往生的经文,短小精悍的轶闻,甚至,几行欲语还休的情诗。
凡人皆有七情六欲,贪嗔痴妄,爱恨别离。鬼没有,因为鬼没有心。但是鬼同样渴望牵挂与关怀。湖底太冷,一丁点熟悉的事物就足以慰藉他们不安的魂魄。
「那他吹箫……」道者清俊的脸庞同样也因为烛火的摇曳而徘徊於明暗之间。
初雨爽快地回答:「他们喜欢听他的曲子。」
冬夜的风声也很像那曾经散落全城的箫音,呜咽悠远,如泣如诉。
「我常说,他这麽做是在代他们哭。可他总不承认。」眼中波光流转,她落落大方坐下,无视道者晦暗的双眼,自在地为自己斟一杯茶,「血阵在那里,怨魂在那里,不论是丢进湖里的东西还是东西里夹带的纸条,都只是一时的抚慰罢了。他们的愤恨与哀怨总要抒发倾泻。比起哭声,还是箫声更顺耳一些。对了,我家兄长其实不懂音律,那是现学的。」
冷言冷语的鬼,看什麽都斜著眼一脸不屑。夜半的大树下,看他皱眉低头,表情是万般的不耐,嘴里咕囔著种种抱怨,手指却还是一个挨一个认真而吃力地按住了箫孔。少了一根手指,手势怪异别扭,曲调也是零落不堪。就这样,背著人偷偷摸摸地学,一夜又一夜,独自奏著破碎的悲歌。
「难怪城中虽有血阵,却始终不见怨气冲天。」傅长亭恍然大悟。当日他就断定城中必然有同党遮掩,不过事後,一直归咎於本地土气浓烈加之水汽丰盈的缘故。
「在道长眼中,他是有心隐瞒。不过在我看来,他只是不愿看怨魂受苦。何况,血阵以魂魄为食,吞吐怨气,兄长此举可算是化解污秽,削弱邪阵威力?凡事一体两面,你我各站一方,所见同一人,却一恶一善,大相径庭。彼此立场不同,见解不一也是自然。」仍旧是柔和缓慢的口气,她坐在灯下,娴静如临水照花,抬手在纸上细细触摸,「就如同他的作为,於道长而言,是为虎作伥。然於小女子而言,他……只是我面冷心热的兄长。」
一双翦水秋瞳倏然上抬,唇角弯弯,她笑晏晏看若有所失的他:「道长可知,小女子出嫁时,兄长为何力邀道长观礼?」
「为什麽?」
「因为别有用心。」
面沈似水的道者脸上毫无惊讶之色:「他从来不做徒劳之事。」
可他做的事却桩桩件件都对他自己毫无益处。
不请自来的花妖沈默地垂下眼,望著杯盏中的茶水。
半晌後,傅长亭沈声问道:「他为什麽找我?」雾气缭绕,他清朗的面容被烛火镀上一层暖色的光影,却在眉心处落下一道阴沈的暗色。
默默看他良久,初雨收敛了笑容:「小女子的夫家是芜州陈家,乃是鬼界中一支望族。愚兄妹二人混迹人间,无依无靠。兄长说,凡间嫁女总要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弟兄相送,以示娘家有靠,免遭夫家欺辱。他忧我孤弱,远嫁必受委屈。因此听闻紫阳真君入城後,才会不惜冒昧夜访,一再相扰。」
「有幸请得道长观礼,夫家果然对我以礼相待,不敢怠慢。道长恩德如山,初雨感激不尽。」她起身对著傅长亭盈盈一拜。房内立时花香四溢。
傅长亭怔怔盯著她额间的花钿。她如同她的兄长一样,浅笑时总把双眼弯下:「你该谢的是他。」
「小妹初雨」那鬼总这麽念叨。谈起这个出嫁的妹妹,他就眉开眼笑。
「他总提起你。」傅长亭说。平稳的声调略略低落几分。
「他也同我说起你。出嫁时,在西城门下。道长虽未显露真身,不过终南弟子的凌然正气绝非山野宵小的浑浊污秽可比。小女子刚到城下,便知道有贵客驾临。後来,他指著那棵槐树道,那树下站著的就是傅长亭,道众万千,唯他无双。」
傅长亭大惊,他不知道,原来他竟如此赞许过他:「他……」
初雨一径笑著。忆起往事她絮絮说来,不激越,不悲苦,散散淡淡如知己叙话。啜一口茶,说一件不大不小、无关紧要的琐事:「道长可知,小女子的婚事是天机子保的媒?」
投石入湖,石破天惊。
「什麽?」低呼一声,傅长亭趋身上前,就要越过桌面去抓她的手。
她面不改色,用一张状似无知的笑脸相迎:「原来道长居然不知道?那麽,这之後的事你就都不知道了。」
「小女子与兄长在城中隐居已有多年。起初,兄长与天机子偶有往来,可每每不欢而散。五年前,天机子看中此地地气丰厚,水脉充盈,地处僻远,便有心在此营造血阵,以求强转战局逆天而动。这些我也是後来才知道的。当时,兄长察觉城中有异,便邀他来此做客。不曾想不但苦劝无效,更被他以我等三人性命相挟,不得不牵涉其中。因为兄长与天机子是终南同修,熟谙摆阵布局之理。他便要兄长助他埋藏尸心,修建树阵。」
烛影摇红,颤动的火光跃动著暖黄色的光芒,照亮了女子秀美的容颜。看一眼木然无语的傅长亭,她落下眼,一句句说著不为人知的渊源:「当日,兄长与天机子有约,只要听命行事,就绝不为难我与杏仁、山楂。可是,後来兄长偷换阵中祭物,事发败露。彼时,两仪双生之局已成,无暇再重塑阵眼替换兄长埋在树下的指骨。天机子震怒,便要我远嫁芜州。名为出嫁,实则扣押为质。以防兄长再生异心。」
「托道长洪福,如今天机子受诛伏法,麾下鬼军一哄而散。夫家也不敢再强留我。我这才能赶回曲江,前来当面致谢。」她勾唇,她侧头,她笑吟吟弯下一双黛眉,一眨不眨看面如死灰的他,「道长方才要我谢他。可惜,我寻遍天下也找不著他了。」
「他……韩、韩觇……」双唇颤动,搅扰在心中的疑惑、纠结、愤懑全数烟消云散。
他从未唤过他的名。相识相交相谈,他总生疏地称他一声「韩公子」,看似温文有礼,实则时时刻刻划清著彼此的界限。当那鬼没好气地骂他一声「木道士」时,他以一声「小师叔」作答,语气玩味,犹带三分赌气。
韩觇、韩觇、韩觇……双手死死支撑著桌面,傅长亭紧咬牙关,静如死水的胸膛内心潮起伏,一阵阵胀痛肆意冲撞,仿佛就要冲破喉头。他……韩觇……抬眼便是刺目的烛光,照得他双眼酸涩。两手之间,两张相同大小的纸笺并排摆放,上头是他的字。
傅长亭认得韩觇的字。行为举止漫不经心的鬼,写得一手工整俨然的字。纤长细瘦,却勾画有力。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恰恰否决了「字如其人」这句话。
在後院喝酒的夜晚,他蘸著酒在桌上摇头晃脑地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道者懵懂不解,只当他又在发酒疯,撩起袖子就要去抓他的手:「你又醉了。」
他乖乖被他握著腕子,听话地抬起头来,果真醉眼迷离:「真巧。我们两人的名讳刚好可以凑成一句词。咦?还有初雨。」
趁著道者低头去看,他却挥起左手用袖子抹去了。
鬼魅皱著脸说:「这喻意不吉利。」
傅长亭犹记得他被酒气熏染得嫣红的双颊,在月光下,越发显得白里透红,说不出的清俊秀丽。醉鬼挣脱了他的手,埋首又在桌上一字字写开。傅、长、亭,他的名。一笔笔,一遍遍,写满一桌。
这世间只有两种人会如此重复书写他人的姓名。一种恨之深,一种爱之切。
「贫道……我……」思绪纷至沓来,他陷进无垠的失落里无路可退。圆桌那头坐著眸光宁和的女子。傅长亭的目光越过了她,遥望紧闭的房门。曲江城依旧,客栈内院如昔,他立在满室的鬼雾里遍地追寻,唯独没有了一身道袍飘然而来的他,「他是被迫的。」
「是。」初雨毫不迟疑回答。
傅长亭直起身,两手悄悄在身侧紧握成拳。指甲顺著掌心的伤口直刺入内,尖利的痛楚细细自手掌窜入心房。血流如丝,红线般将他蜷起的手指缠绕。他环顾四周,茫然地扫视屋内的一切,最後,又转回到初雨镇静的脸上,神情落寞:「为什麽告诉我这些?」
「想找个人聊聊他。」女子安然答道。鬼气阴森,花香妖异。茶盅里的茶水凉了。她自顾自提起茶壶,慢悠悠将杯盏注满,「兄长生平知交甚少,想找人叙旧不易。虽然傅掌教贵为一国之师,天子重臣,必然日理万机,劳顿疲乏。难得他与掌教有故,小女子斗胆,望请国师宽恕,哪怕不看小女子薄面,也请看在不在的人的份上,与我闲话几句。」
她口口声声都是谦卑,字字句句皆是恭谨,一句「不在的人」轻轻巧巧一语带过,却是笑里藏刀、绵里埋针,深深扎入他的胸膛。
话音落下,她仿佛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口。赶忙用衣袖掩面,故作一脸惊诧:「道长怎麽了?」
双拳握得更紧,傅长亭强自仰首,不愿再看柔静从容的她:「你还想说什麽?」
她闭口不言,悠然饮一口茶。勾唇浅笑,神情扑朔:「你信过他吗?」
「……」傅长亭颓然後退,衣袖带倒了桌下的圆凳。那凳子轰然倒下,「骨碌碌」一路滚到墙边。
「当日我尚在霖湖边时,常听离姬说起,这尘世中无论凡夫俗子,还是我等草木精怪,来来往往,相识离散,无非脱不了一个『信』字。只有死心塌地信了,才会有不离不弃的情爱。否则任凭情话再缠绵、誓言再动听,终究不过水月镜花,一触即散。人世浮沈,若是连相知相信都是谎言,又何谈相携相守?」看一眼神色怆然的他,初雨啜著茶,一如既往仍是温婉口气,「自古魔道相争,正邪相侵。道长不信他也是应该的。但是……」
话锋一转,她放下茶盅,徐徐扬起脸。始终盈盈淡笑的脸庞上,笑意一丝丝退去,最後余下满眼哀戚:「你不信他,他却信了你。」
「!啷──」迅疾的夜风终於吹开了老旧的格窗,雪花狂乱飞舞,团团涌向房内的道者。半开的窗框禁不住摧残,被风雪拉扯著,一次次「啪啪」捶打墙面。桌上的烛台瞬间被夜色吞没。
举手捏诀,她好心替他把灯盏再度点亮。烛火燃起的刹那,初雨分明瞧见,这位传言中「轮回时忘了带上人味儿」的终南掌教正跌坐在自己对面,所有矜贵与傲气俱都溃败为一地碎雪。
手中不禁一抖,刚点上的烛火再度熄灭。
「你……怎麽知道?」黑暗里看不见他的表情,只有镇定无波的语气失去了一贯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