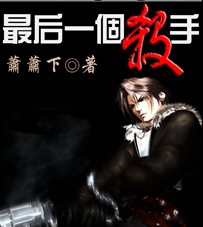最后一个匈奴-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一部分
第四章 那文弱书生是谁?(5)
作者 : 高建群
杨蛾子一直是她的哥哥的崇拜者。哥哥讲那些事情,她一样也没听过,简直像天书里写的一样。以女孩子的心理,她尤其注意到了杨作新谈到的女性。她真羡慕那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可惜她没钱念书,要不,说不定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她当然不是怨父亲偏心眼,只让杨作新没完没了地念书,而不让她跨进学校一步,她是女孩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和哥哥攀比的意思。琢磨完了女宣传员,她又琢磨那些抹着红嘴唇、穿着旗袍的女人了,这时她在哥哥的话中发现了破绽。她说,大冷天的,那些婆姨女子,真的敢精腿把子,在露天地走,她们不怕冷?杨作新回答说,这是真的,他亲眼目睹的。杨蛾子还是不信,说哥哥喧谎。
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
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一部分
第四章 那文弱书生是谁?(6)
作者 : 高建群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人家和杨作新一年结婚的,现在娃娃都满炕爬了。杨作新听了,“嗯”了一声,算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杨作新十三岁上结的婚。在当时的陕北,这个年龄结婚,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一年他初小刚刚毕业。十三岁的他,在村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和他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先后中途辍学,只有他一个上完了四年,因此他可以说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过去村里,没有读书人,逢年过节,大家嫌门上不贴对联,不吉利,要贴,又没有人会写,于是只好在红纸上,用碗底蘸些墨汁,塌上一溜坨坨。自从有了杨作新,一个村子的对联,由他包了。遇到红白喜事,为“上山”的老人写一个“驾鹤西游”,为结婚的新人写一个“天作之合”;春节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为拴驴拴牛的槽头写的“槽头兴旺”,为石砌矮墙上写的“抬头见喜”,为灶王爷写的“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等等,这些,都是杜先生教诲有方,杨作新寒窗苦读的结果。每当杨作新,提笔龙飞凤舞时,站在一旁的杨干大,脸上不觉露出得意之色,心想这学算是上对了,这钱花得不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一部分
第四章 那文弱书生是谁?(7)
作者 : 高建群
杨作新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上学期间,搜搜腾腾,从杜先生那里,从周围村子里,借得不少古书新书来看。那古书中,四部古典名著,不但看过,而且烂熟于胸,名著之外,一些二三流的书籍,《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七子十三生》、《五女兴唐传》、《济公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等,也都能讲出一个大概。村上人们,闲来无事,常听一个瞎子讲古朝。那瞎子自然大字不识一个,只是年轻时走南闯北,凭着一副好记性,从说书人那里,窃得一些东西,再依样画葫芦,加上自己的合理想象,核桃枣儿一股脑儿倒给乡亲们而已。小时候,杨作新便常是这瞎子的听客,如今看了古书,才知道这些英雄美人,演义传说,古书中都有。乡下人听古朝,一为听,二为聚在一起,挤热窝,所以杨作新闲来无事,也依旧常去那里,而且从不显山露水。只是有一次,瞎子讲到要紧处,大约是薛仁贵兵困锁阳城,二路元帅薛丁山赶去解围,一路上接连接收樊梨花、苏金定、窦仙童三个奇女子做老婆的故事,其间一个启承转换的要紧关节,突然讲不上来,正要发挥想象,瞎编,这杨作新在旁边,情不自禁,提示了一句。瞎子听了,知道这小后生肚子里有货,只是碍着人多,不露声色。场合散了以后,瞎子赶到杨干大家,登门讨教,不耻下问。害得杨作新一张小白脸涨得通红,说声“折杀我也”,不肯指点。后来见瞎子确实是一片诚意,只好敷衍一番。从此瞎子说古朝,有了疑难处,便来讨教,技艺自然提高不少。村上人知道了其中原委,想不到他们的无所不知的瞎子,竟然投师到小小杨家小子的门下,从此对这后生,更是刮目相看了。
从此杨作新乡间秀才的名分,正式奠定。杨干大眼皮浅,见了儿子这样,觉得已经成龙成凤,修成正果了,从此便盘算着,儿子初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帮他务农的事。尽管杜先生一再怂恿,甚至不惜亲自到家里为杨作新说情,可是杨干大硬是不给面子。杨干大觉得,为儿子讨个媳妇,便可以把他拴住了,于是便和婆姨商量,乍舞着为他问媳妇的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一部分
第四章 那文弱书生是谁?(8)
作者 : 高建群
话已说出,左邻右舍便都知道了,大家悄悄地张罗,只是瞒着杨作新一人。杨作新上学回来,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常常用手刮着脸,羞他,称他快做小女婿了,杨作新听了,莫名其妙。前面讲过,吴儿堡杨氏一脉,尽出自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因此村上的小媳妇,称他阿叔。按照乡俗,大嫂子可以耍戏阿叔。于是她们当着他的面,常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话。有时候,一个小媳妇骑着毛驴熬娘家,远远地照见杨作新背着书包过来了,于是鞋跟往驴肚子上一磕,一只红鞋掉在了路上。小媳妇“哎哟”一声,撒声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杨作新问媳妇的消息传出,村里那些出了五服的杨门的大姑娘们,也猛然发现身边这个小书生长大了,到了该婚该娶的年龄了,于是纷纷动开了心思。或者纳上一双绣花的袜底,悄悄地塞到杨作新手里,并且逼着杨作新赶快脱下鞋子,垫在里边,免得别人问起。或者从垴畔上用棍子打下一把酸枣,瞅瞅四下没人,塞进他的书包里。生活中骤然起了变化,变化得叫杨作新莫名其妙,他回去问父亲杨干大,父亲说,少跟那些死婆姨烂女子来往,他问母亲,母亲只是笑而不答。
说一千道一万,主意最后得由杨干大拿,而在决定这些家庭大事时,杨干大又总是以婆姨的意见为意见。其实,杨干妈早就心里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任凭媒人跑断腿,踢烂门槛,磨破嘴皮,任凭那些杨门出了五服的大姑娘甜甜地向她讨殷勤,她只是虚于应酬。原来,她瞅下了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叫灯草的。她喜欢灯草本分、老诚和勤快。杨干大见过这灯草一面,他觉得粗糙的灯草配不上细皮嫩肉的杨作新,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起码要人能看过眼才行。杨干大提到灯草嘴唇厚,杨干妈说,嘴唇厚说明她人老实,杨干大提到她脸黑,杨干妈说“黑是黑,本颜色”,杨干大提到她大屁股,杨干妈说屁股大好养娃娃,杨干大见杨干妈是铁了心了,于是也就不再表示异议。
吴儿堡这边打发媒人去说,灯草的父母那边,听了提亲的事,慨然应允。不久后庄传回话来,一切按规程办。按规程办就是要出四十块大洋的聘礼,这在当时是个公价,人们不提钱的事,嫌那搪口,只说按规程办,也就是说要出四十块聘礼了。灯草的父母,提这个条件也不算越外,因为不论是找谁家闺女,都不免要出这一身水,而且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聘礼出得少了,乡下人会有闲话,说这女子不值钱,恐怕是做下什么非嫁不可的事情了,或者是个“石女”①。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一部分
第四章 那文弱书生是谁?(9)
作者 : 高建群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②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