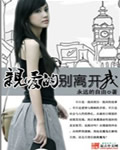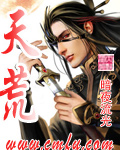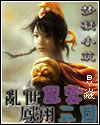�ʻ�����--������-��2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ģ�����ƪ���������۵��ҾͲ�����������ˡ�
��۱�����Ҳ��Ϊ��ʫ�绤�ģ�������һ�����Ϊ�����������������������һ�룬���^�ʫ��������Ұ�ϣ�����Χ�������Ȼ���������������ϴ������ڣ�������Ҳ��Χ�ڳ���������У���ʱ����Ȼ��о���������Ҳ�dz���ģ�������ȥ������������ɤ�ӷ����ģ��ֻ��Ǵӷ������з��������Ǽ���������Ӧ���е���ʶ�ɣ�������������
ʫ�ĺû������ʼ��ǣ����˵ļ�������Ҳ�в�ͬ������������ʫ�Ƿ��������Ƶ����ʡ��������ö��������жϰɡ�
��һ�Ű�����һ�£�
������ע���ڡ��ٻ����ճ����硡����ġ����ʣ������顷���е�ͬ����������һ���֡��������Ƶ����ʡ��Լ����ĵ�д�����ھ���ɾ���ˣ�ȡ����֮������ôһ�λ���
���Ҫ˵һ˵�����Ƶġ������������ڱ��������һ���Խ��ܹ���֪ʶΪ������־�������α༭���������£�һ�Ű�������£�إ���գ������������йط������룬�����·��ʡ����ڰ��£������������ڻع�;�С�
����ǵ�����
���ߣ�������������
������ǡ�������������������ң���Ϥ��۵�С�������������Ʒ��˵��������۵ġ���������ɫ�����������ֻ��̸�������ֵ���ɫ���������ԡ��͡�˼���ԡ���ȫ���������Dz�����ģ���������������ȥ���Ӹ��ɣ���
����Ϊ��������������������ɫ��һ�����¶�������ʵ��Ȼ��������ٵ�ϲ���ÿ��ŵ���д��ͬ���ͺ��䷼������ʱ�����ġ�Ψ�����С�Ҳ��ͬ����ȴ����һ���������֬�۵����ˣ���Ȼ��Ȼ����¶���������ּ��������������������ڹ۲������˲�����д��������Ļ���Χ�ķ羰���ʴ�����ϸ�£�����������ĺ���Χ�ķ羰Ҳ�����л�����ϵġ����������¾���ѧ�����൱���裬�����˵���ġ�����������úܺã���������ּ��ɵ����ÿ�˵���ǿ��Ի������磬������������������ҵ�һ����ɳʯ����
���Ǿ�һЩʵ���ɡ�����һƪ��Ϊ�������ŵ������Ķ�ƪС˵��дһ��������壨��������ţ������ˮ���ˣ�����ij�γ������㣬��ʧ�������ŵĴ����У����ڸ�ĸ˫��֮����Ʈ����ʮ���꣬�ֻص��˹���������죬ǡ�������ϴ�����
�������ŵ�����
�뿴�����������д�������ŵ�������
�����������ڷ���������һ�ڿ��̰�������Χ�š������ǰ�Χ��������Ŀ�ĵ���������Ŀ�ĵ�ѭ��һ����Ļ�Բ����ȥ����չ�ţ������ţ���������ȥȥ���ڵͳ��Ļ�ɫ������´����һ��һ��ذ��������һ��������ܵ�����ż�������˴�����������������˻�ʱ��������������������κ��Ƶģ���һ�رܣ��ƺ��ÿ�һ��·���ˣ����ܿ�أ�����أͻ������Ȼ���˵��˻��ɰ�ɫ�ı��͵㡪���ǿſ����Ͻ����ˮ�㡪������һ�����İ���������������ԭ�ɺ���һ���֡�����������ʱ����������һ�ڿ�������������������ƽ�洦���䣬�������չ����
������˷����������ص����ع�����ѽ����
����ˮ�壬�ӽ����ģ��Ӵ����壬�Ӳ��壬�Ӿ�����ɽ����һ�ߣ������ˣ��������������ŵĺ�Ͽ�ϣ�Ȼ���������ĺ����ų��������ܵ�����������Χ��ÿһֻ���ϵ�ľ����ÿһֻ������ս�������۵IJ��㴬��������Χ��ÿһֻ������Ͷ�̱����ˮdz�ĵط��Ŀ�����Сͧ����ͬ��ԭ����������庣��Ľ��еļ�ֻ��������������
�������е���ʧ��
������֣���������������д��д����ϸ�µ����֣����������Ƿ�дһ������������Ǿ���Ũ��ط�ɫ�ʵ������ŵ�������������Χ�Ĺ��ϵ�ľ����̱����Сͧ���������۵IJ��㴬������������庣��ļ�ֻ���������������������������еľ��Ҳ���������������Ʈ���˰����Ŀ������ˡ�
�������������ڷ���������һ�ڿ��̰�������Χ�š���һ��ͷ���ǰ������˸��˵ģ������������Ҳ��������Ϊ���ǵĻ���ô����������ñ������˵����ǣ���Ȼ���Ʊ�Ũ����Χ�����Ҳ�����·����Ҳ��е����κεġ�������ô��
�ڶ���ȫƪС˵֮�����ǻ���������õ��������֡��������С�����ʧ֮�С���Ʈ����ʮ���꣬�ص��ʵأ��Ǽȸе���Ϥ�ָе�İ���ġ������һ���ϸ���������·����ֻ�ܻ�˵���������Ҳ��֪���������Ǹ����ġ�����С˵���һ��������д�ģ�
����ͷ̧�ø߸ߣ��������Ƶ����������ź�Ͽ���ǻ�û����ȫɢȥ������
������������ȥ��������������ȥ�ġ�������ʮ��������
���ţ����Ǹ����ġ���������㯵��Լ����Լ�˵�������촽���ز����š�
�������м�ʱ��
����ȥ��������������ȥ���ˣ�Ҳ��ȥ��������������ȥ�������ص��˼���Ϥ��İ���ľɵأ����ܹ��������Ļ�����Lj�ͷСͧһ�����ﳪ�ġ���ˮ�衱��
�ճ���ɽ������
�ƿ�����ɢ
���㳪������
��ʱ���أ�����
������ˮ�裬����ĸ�׳���������ʱ��Ů�ѳ�������������Ҳ�dz���������ˮ�������뿪�����ŵġ���ϡ�����Ƶ��ֻ꣬������û��������˵���ƿ�����ɢ����������������뿪��ʱ��Ҫ�������Ƶ�����Զ�������ź�Ͽ���ǻ�û����ȫɢȥ��������
����ʫ�����ס�����һ��֪��д�ġ�����ż�顷������С����ϴ�أ���������ë˥����ͯ�������ʶ��Ц�ʿʹӺδ������������ַ������������ӻ����������飬��Ϊ����ǧ�ŵ���ʫ�������������ġ���Ρ��������DZȽϡ����桱�ġ������ĵIJ�����ƺ������Ȼ��������˵��������Ϊ�����ĵ������Ա�����ʫ���ߣ���������д�ض��������ض��Ļ����ı��֣�����ʫ����д��һ�㡱�����ӣ����ĸ����Ǹ��С������ԡ��ġ�
�˾�ʱ�ս����ڻ�
�������ѧ�о��硱����ġ������ѡ�����������ڡ�ǰ�ԡ���Ҳ���ر�̸����ƪ�������ŵ���������Ի��������ͨ���Գ����̵��������������ˡ�����ʱ���գ��ֳ�����䣬�������ľ����������ڻ���ǰ���Ӧ����Ϊһƪ���˵ij�ɫ��Ʒ��������������Ϊ�Ǻ�ǡ���ġ�
��ƪ��ƪС˵���������һ������������һ����д�ģ���ʱ�����ֻ�ж�ʮ����ɣ����ֵĹ��������ļ������ˡ����Ҫ��ǿ���Ļ�����Щ�����ƺ����ӳ���һЩ���Ҹ����ǰ���ʮ�������ϵľ��Ӿ͵����dz���ģ���������ǵġ����䡱Ҳ��д��������Ȼ������˵�ǡ�����ɳʯ���ġ�
��ʮ����֮��һ�����ģ��������д����һ����ƪС˵��ѩ����дһ����۵ġ��½����ꡱ���½�����۵Ľ�������Ӣ��ı����Ҳ����ϸ��ıʴ���д������ĸ��顣�������DZȡ������ŵ��������Ӽ����������ˡ�
������ժ¼�ԡ�ѩ���е�һ����д�������֣���д�Ǹ��½������ں���������������ľ�ɫ���͡������ŵ�����һ���������д��Ҳ�Ǻ�����������Լ��ľ���ϵġ�
�Ƶ��ƿ顡��ѿ�ײ�
ת�ۼ䣬����������dz�˯�ĺ���ɽ��Զ���е������ƣ����������ǣ����ţ��ƹ�������һ���ش���µ������ӡ�ͯ��ʱ���½�����£������쿴����Ⱥ���ɵ������ҹ���س���������һ����Ⱥ�����ӡ�������һյյ�ҵĻ��͵ƣ��������⣬����ǰ��������ȴ�ڴ�����������ܾúܾö�û��ʧ�䡣
����
������һ���������۾�����������ʱ�����ѽ����ˡ��Ƶ��ƿ���������ѿ��ײ��Ƶ�����Ǧ��ɫ������DZߡ����������Ļ����µĵƹⲻ֪ʲôʱ����ȥ�ˡ�������ȥ��ǰ����һЩ���ι�״��ɽ���ãã���ƺ����������ϼ�ʼ�����ɫ�������ɽ�ͼ����һ��ƽ�Ȼ���������ƺ���ӳ����һ��ѣĿ�Ĺ�ԡ����ţ��������ĺ�ϼ�������Ե��ð�Ҳ�ѹ����ˡ�������簲֮������һ�£�ֻ���Է�������һ����һƬī�ڣ���Щ��������ĺ��Ӽ������½����µ�Ұ��һ��֣��·�ͻȻ������˯���г������Ƶġ���
�к����ֵ����ݴ�
���������֣����ҵ���д�������º��������ľ����������һ��ġ�������������һ���ض���������½����ꡱ�������������һЩ���ر𡯵����ݴǣ����һ����Ⱥ����������Ϊ��һյ�ҵĻ��͵ơ������Ƶ��ƿ飬����Ϊ����ѿ����ײˡ������ð�һҹ��ͳ�����������ĺ�������Ϊ�����½����µ�Ұ��һ��֡��ȵȣ������к�����ض�������ġ�
�������һλ�ж����ܵ����ң�дʫ��дɢ�ģ�дС˵���������Լ��ķ����������ժ¼������С˵�е����֣����ڣ��ٽ�����ɢ���е�һЩ�Ѿ䡣������ƪ��Ϊ��С�������͡��˻�������ɢ�ģ���ʽ�Ƚ��ر������������������һ�֡��������˵��һ������������������ֻ������Ӱ��һ����������һ�������еľ�ͷ������ɢ�ģ����־���ʫ����ζ���Һ�����������ɢ��ʫ����������ժ¼һЩƬ�ΰɡ�
����������
һ
�������ͣ������������������ϪҲ����һ�ѷ��������ࡣ�����罫���������ࡣ
���ɣ�С�ӡ�
��
�Ը��Դ��������ä�˹���
���ѱ�������ñ���������С���ࡣ
��
��վ�ڴ����վ�ڴ��⡣
һƬ�����IJ��������Ǹ������������к��ţ�
Ц�����ˡ�
�Ҵ��˴���
Ȼ������Ц���ڴ��
��
�����ҹ��
��˯��Ⱥɽ����˯�����֡�����
������ҹ���İ���
��į�䣬����������
��ЩƬ�Σ���ժ¼������ǵġ�С�������ġ�����ЩƬ�Σ������Ʒζ����������ֵ�������
�ǻ۵Ļ�
���˻������͡�С������һ���������Ե���һ��ɢ��ʫ��������ͬ���ǣ���С�������ǡ����⡱��ɢ��ʫ�����˻�����������ÿ��Ƭ��֮ǰ����������Ŀ�ġ�����ժ¼���Σ��Լ�����
ɽȪ
ɽȪ��·�����۵ģ���ҪԽ�������ϰ������ߵ�ɽ��ȥ��
�����ݴԣ��ƹ�ɽʯ��ɽȪ�������������۵�·��
�������ɽȪ�ܿ��Խ���ϰ�����ɽ�±�ȥ�����ȥ��
�ٲ�
˭˵���Լ��Ȱ��Ĺ���ȫ���Ը�����һ���ο������أ�
���������ٲ�����
˭˵�������Ķ�̸����һ������е��㾡�أ�
���������ٲ�����
�ഺ
�ഺ��ÿһ���˸��
���ഺ����Щ�Ȱ��������˵������һ�����������
ÿ��Ƭ�Σ�������һ�㡰��������ƪ�����˻�������������������ҫ���ǻ۵Ļġ�
����һ�Ű˶�����¶�ʮ�����¼��¡������̱�����
�Ȼһ������ȥ
���ߣ�������������
����̸����ǵ�ʫ
�����������꣬��������ǵ�һ��Сʫ����ɡ����
��һ��
����������
�ڽ���������Ľ
һ���������������
�����������������
��һ�����ʵ�����ǰ��
������
��˭�ҳ�˯������
��ɡ��������ҹ������
��һ��ˮ�е�˯��
Ŷ���㴩�����µ��ԝ���
ȥʱ��Խ��·�ϵ���Ţ
��ʱ��Я��һ��������
����ʫ�ġ����������硰�����������ꡱ������һ��ˮ�е�˯����������ʱ��Я��һ�������Ρ��ȵȣ����Ǻ����ʣ������С�ʫ�����Ĺ�˼������������Ѻ�ϣ�����������Ҳ������һ�ֺ�г�����У���һ��������ĺ�ʫ��
����ǵĺ�ʫ���С�����֮�ʡ����پ�����һ�ס��ʼ��ϵ�ʫ��Ϊ����
��һ��
Զ���Ĵ��⣬��������
̤ǧ����˶���
�����У�����������ȥ
������ȴ������
˭֪���Ҷ��ϵĻ���
����˶���
�����ź�Ͽ�ij���
������
��ʱ��ңԶ�Ķ���
������ҵƻ�
������е�ʱ��
�ȶɹ�����ҹ������
��������뵽���ҵ�˼��
�����ǹ�һ���ɱ�
����ǰһҹ½����
̧ͷ���ҹ������ǵ��˴ӡ����ϵĻ�������ͻȻ���뵽�������ź�Ͽ�ij����������ơ���Ծ�����롱��������ʫ��������ʱ�ս�������д����
�������д��ʫ��Ҳ��д����ʫ��ѡ¼���������߾����£�
����ë����������ף�
�Ȼһ������ȥ����ѩƮƮ�۵�����
����ǧ�仯����ռ���Ю������
���·ת��ӯ������������ȴ��ͣ��
������ӷֽ��ϣ�������Ծ�����ǡ�
ƹ����
���Ծ������ת��ȥҲ���Ѽ�ǰ�ߣ�
ֱ�����ⱼ�Ƶ磬�ķ����������ס�
д���������һҪд������������ص㣬��������ֻ�÷��������ݴʣ��Ϳ���Ū����ë���ƹ�����ˡ���Ҫд������̬��֮����һ����ԣ�����̬���DZȡ���̬��Ϊ��д�ġ�������������������ı�����������ʮ�����У�����ܹ�����������д���ˡ�������ë��֮�硰�Ȼһ������ȥ����֮�硰��ռ���Ю�������������������صı����������ڡ�һ�������������ϡ��Ȼ�����֣������Ǿ�̬��������Ҳ���Գ�����̬���ˡ���Ҳ�ɳ�Ϊ��Ծ������ɡ����ľ���ʫ��������ʫһ�������Ƿ�����£�ʱ������֮�ʵġ�
̸���ڵ�����ʫ
���ߣ�������������
���������ꣶ�£����գ��Ϻ����Ž�͡��Ļ㱨��Ϊ�����������ɵģ������پ�����ף������������Ϻ����Ļ㱨���Ĵ����ˣ����Ϻ����Ž�Ĺ�ϵ��Ϊ���У���ˡ���ʽ������ף����Ϻ����С��������棬����һЩ���ų��������ѣ�����δ�������μ���ף�������ٳ�֮ǰһ���£��������ڱ�����ʱ�����ϻ���������ۡ���������ǰ�ܱ༭����Ҳ�Dzμӻ�����֮һ������ϯ��ʫ���ɣ�Ϊ����ף�١�
����������ʫ�ӱ���������ۣ���۱�ֽ��ר���������м�λ̸�����������ڴ���֮���Ͽ�����ʫ��һ�������֣�ͬʱ����ʫ���漰һЩ�������Ĺ�ʵ�����˲������ˣ����������꾡����������˴ӱ����������ڱ���ʱ����������̸������Ϊ������ʫ�⣬��¼ԭ����������ˣ���Ϊת����
��˵��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