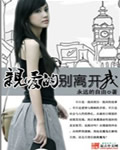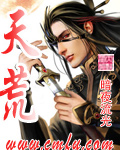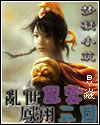笔花六照--梁羽生-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武帝,只好回转少林寺面壁去了。
世俗流传少林寺有两部武功秘笈,一名《洗髓》,一名《易筋》,此两经据说是达摩遗著云云。达摩之所以被捧为少林派武术鼻祖,和这个传说大有关系。其实这个传说非但无稽,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厚诬古人,达摩祖师倘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给这个传说弄得啼笑皆非。原来这两部“经”乃是明代无聊文人的杜撰,满纸淫词,不堪入目,经中教人所练的“内功”,是用来增强性能力的。“挂羊头,卖狗肉。”与其说是什么武功秘笈,毋宁说是更近乎“性经”一类。广州出版的《武林》杂志第二期,有一篇《少林寺与少林武术》的文章,在细说少林武术形成的由来之余,也为达摩祖师的受诬作了辩正。
据那篇文章的说法,少林寺的武术是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有的人为了避难,到少林寺出家,避难者中,不乏本来就懂得武艺的人,也有少林寺的僧人在外面学会了武功回来的。继承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晚年(公元五七四年)时就曾碰上北周武帝的“灭佛”之祸,寺院被占,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僧侣流散。在这种情况下,僧人是非学会防身的本领不可的。有信史可考的是:“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到了宋代,少林寺才渐渐变成了出名的会武场。
说达摩有武学著作是假的,他对佛学有贡献则是真的。最大贡献是“禅宗四圣句”。四圣句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是说禅的本质不需文字解释。“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是重在师徒之间的以心传心,无所谓特定的教学体系。“见性成佛”是在找回真我。总的精神在一个“悟”字。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解释。一说这本是释迦佛祖的“语录”,由达摩加以解释。
(一九八二年五月)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作者:梁羽生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这是我在《白发魔女传》中写的“题词”。在我的想象中,白发魔女是来去如风,在群峰之中出没的“神奇女侠”,但她并不是“神”,所谓“神奇”,只是由于她在旁人眼中那种“超凡”的本领,只是由于她被某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强烈的性格。
这样的“奇女子”,倘若没有雄奇的名山来供给她做活动的场所,恐怕就会减少她的魅力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构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构思”,如今已经成为事实。
长城公司的《白发魔女传》是在黄山拍摄的!
古人有个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岳”,把黄山的位置放在五岳之上,可见这座名山的享誉之隆。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飞瀑……这种种罕见的景物,不正是足以衬托出这位罕见的魔女吗?
“魔女”的导演张鑫炎是曾经和我合作过多次的朋友,《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都曾有过令人满意的成绩,对这部更具有特色的《白发魔女传》,我是有信心他能更上层楼的。
在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也是被改编得最多的一部。曾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国语电影,和长达四十集的电视剧。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廿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
第二个“白发魔女”是李丽丽,她是佳视制作的同名电视剧的女主角。
现在这部正在香港上映的《白发魔女传》,是由长城当家女旦鲍起静担纲的,她是第三个白发魔女。【注一】
注一:八十年代之后,还陆续有“白发魔女”在银幕和荧幕出现。顺序为林青霞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影两部(于仁泰执导);蔡少芬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视片集(共二十集,香港无线电视);黄碧人、黄嫊芳、郭淑贤在《塞外奇侠》电视片集(共廿一集,新加坡国家电视)中分饰的三个白发魔女。(九八年八月一日补记)
魔女三现,各擅胜场。作为小说的原著人,我是十分高兴看到“新魔女”的出现的。
但在喜悦之中,我也有一些伤感。伤感的是,一位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老词人,他也是一位令我获益不浅的老前辈,如今却已是作了古人,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这位老词人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
记得正是《白发魔女传》的粤语电影开始拍摄那年,那时我和刘老尚未则识,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我。这首词已收入他的《沧海楼词钞》,并有题记,不过《词钞》中有几个字和他写给我的原稿不同,现在我照原稿录下:
踏莎行
(题梁羽生说部《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我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我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我感动。
过后几天,他约我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有冷气的。令我惊奇的是,他谈起我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他的《沧海楼词钞》自序中,他曾说,他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代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我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他和我讨论我的诗词,当时实在是令我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怕他只是和我客气,不肯挑我的毛病,那岂不是令我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我意料之外,他对我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和我初次相识而对我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我担心那样,因为我和他词风不同,“漫不叶律”,弹得我一无是处。他一方面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叶音律,但也“有弹有赞”,我那些胡乱填写的词竟也颇获他的好评。我学词不成,正是需要这样一位精通词学的长辈指点,但他的谬加赞赏则还是令我汗颜的。在那次谈话中,他也和我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我大开茅塞。
只可惜我忙于写小说糊口,不能专心学问,那次畅谈之后,我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益,但一曝十寒,自问仍是并无寸进的。相识时,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他就谢世了。
(一九八零年五月)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作者:梁羽生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好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
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欢喜《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著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 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迦茵?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的“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se)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著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末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月)
注:《凌未风?易兰珠?牛虻》一文,最早是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专栏上的,学林出版社曾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结集出版该专栏的全部文章。此文随后又在新加坡《星河日报》的“笔?剑?书”专栏发表过,该专栏的文章已被百花文艺出版社以《笔?剑?书》为名结集出版。以上两种版本的《凌未风?易兰珠?牛虻》结尾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笔花六照》中,该文章却被腰斩两节,在“……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处结尾。
有才气 敢创新——序卢延光的《武侠小说插图集》
作者:梁羽生
延光兄的《武快小说插图集》即将在国内出版,我虽然远在南半球的澳洲,闻此佳音,也不禁和他同感高兴。因为在这本画册里,他画的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对我来说,是分外有“亲切感”的。因此,给他的插图集插文(作序),在我,自也是“义不容辞”的了。
对画,我是外行,我只能说说我的感觉。
我写武侠小说写了三十年,为我作过插图的名画家也很不少。论合作的历史,延光兄是最新的一位;论年龄,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但若问我最喜欢哪一位画家的插图(过去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我答不出来),我现在是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是廷光兄的插图。我这样说,井非认为他已是“后来居上”,每一位成名的画家都是有其特色,很难定出高下,也无须强分高下;我这样说,只因在艺术作品中,我最喜欢有才气的
作品,而他的画,是我觉得最有才气的。论画,总不免是带有主观性的,因此,我说我最喜欢他的插图,当然这也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爱好。
“才气”是很抽象的东西,捉不到,摸不着,它只是诉之感官的,难于具体说明。无已,只好作个比喻吧。我觉得画的“才气”就等于文章的魅力,有些文章内容很好,却不吸引读者,那就是因为缺乏魅力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