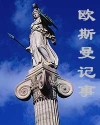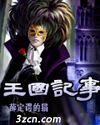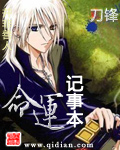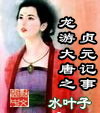庆熹记事 作者:红猪侠-第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苗贺龄在帘外叩头。
隐约见得景优公主点了点头,道:“免。”便要起身内去,苗贺龄连忙跪爬两步上前。
“怎么?”景优公主站住,回首不耐问道。
苗贺龄叩首道:“臣斗胆请问公主起居安康?”
“这里锦衣玉食,与我朝无异,不曾有过半点差池。”
“是。”苗贺龄道,“太后太妃饮食俱佳,圣体康健,公主不必挂念。”
景优公主默然一笑,“我不挂念。”
“皇上亲征于北,不日便即凯旋还朝,公主也不必挂念。”
景优公主笑道:“中原并无我什么牵挂,苗卿过虑了。”
苗贺龄一时无语相对,想了想才道:“是。公主保重。凤体无恙,太后太妃才放心。”
“知道了。”景优公主已然有些烦躁了,提高了声音道,“退下。”
帘内却有内臣笑道:“公主娘娘,苗御使千里跋涉,磕头请公主娘娘的安,一片谨慎忠诚,没有功劳也总有些苦劳……”
“怎么说?”景优公主问。
那内臣笑嘻嘻低声说了几句,景优公主冷笑道:“苗御使从来两袖清风,大理的这些玩意儿还不一定放在眼里。你看着办吧。”
“是。”那内臣恭送公主转身入内,才撩起帘子出来,笑道,“苗御使快请起,快请起。”
苗贺龄让他搀起身来,见他眉目聪慧,一脸和善,正是自己要寻的如意,大喜道:“如意公公,向来可好。”
“好得紧,好得紧。”如意道,“苗大人府上都好?京里还太平吧?”
苗贺龄只是一叠声称好,如意已将一对碧玉扇坠举在他面前,道:“公主娘娘的赏赐。”
苗贺龄连忙伸手接那扇坠,“扑”地将一个小指粗细的纸卷悄悄投在如意的袖筒里。
“臣谢恩。”他又叩了头,起身告退。
段秉在书房外等着苗贺龄出来,迎上前笑道:“说起来,小王正经是太后太妃的晚辈,恭问两位慈驾吉祥如意。”
两人落座,寒暄半晌,苗贺龄的随从将皇帝书简奉在案上,即随太子府中的内臣伴当退得远远的。苗贺龄正了正神色,开口道:“臣谨遵我朝皇帝陛下圣旨,奉中原国书在此,呈大理国王陛下与太子殿下御览。”他站起身,要掀开覆在书简卷轴上的黄缎,却让段秉一把按住了手。
“苗大人,”段秉端坐微笑道,“既然是国书,何不在敝国朝上宣读?”
苗贺龄怔了怔,见段秉眼眸深处黑幽幽精光锐利,知他颇难对付,当即坦然一笑,故意曲解了段秉的意思,道:“太子,何必如此谨小慎微?如今大理国内真正定得下国策决断的,不就是太子一人?”
“哎!”段秉作势嗔道,“苗大人此言差矣,君父在位,儿臣说什么决断国策?”
苗贺龄道:“太子过谦。以太子德行,大理百姓众望所归,就是中原君臣,也要仰仗太子平伏西南苗疆,两国相安,共襄盛世。”
“贵国皇帝陛下有此美意自是两国大幸。”段秉道,“难道苗大人所奉国书便是此意?”
苗贺龄道:“太子容臣据实回禀,臣奉国书所言之事,只怕远超太子期望。”
“小王的期望?”段秉似乎有点错愕,慢慢松开了手。
苗贺龄笑了笑,揭开黄缎,展开庆熹帝亲笔国书予段秉细看。
“川遒三州?”段秉才看到一半,便倒抽了口冷气,猛地抬起头来。
苗贺龄颔首道:“正是川遒、杜门、幽秦三州。”
段秉抿着嘴,将身子更俯了下去,“叮”的一响,扇坠撞在桌角上,他这才觉得有些失态,抬头透了口气。
“不过,”段秉道,“贵国皇帝陛下邀大理精兵入境平苗,恐怕贵国朝内非议者甚多吧?”
苗贺龄道:“也不见得。此事当属机密,我朝中知道底细的大臣却也不多。”
段秉摇头笑道:“苗大人,割地借兵,天大的事,中原朝廷若无人知晓,就算小王说通了父王臣工,还不是一样为你们征蛮龙门白亲王挡在北门关之外?就算是贵国皇帝陛下有一百二十分的诚意,那川遒三州却是我能从中原兵将手中讨得回来的么?”
“太子,”苗贺龄道,“有皇帝的亲笔国书在此,中原谁人不从?”
段秉指着国书末尾“靖仁”朱印,道:“苗大人,要说这是国书,何以不用皇帝印玺信宝?”
苗贺龄慢吞吞将国书重新卷起,交在段秉的手中,低声道:“要说这是皇上给段太子的私函,也不为过啊。”
“哼。”段秉从鼻子里笑出声来,“苗大人,两国相交,作准的,就是印信。若无贵国皇帝陛下信宝,此时不过空口无凭。”
苗贺龄一笑,“段太子,容臣将皇上的书简先放于王府上。太子不妨再多想想,若觉此事绝无可行之机,臣便将国书取回,上禀皇上知道。”
“且慢。”段秉见他竟说走就走,躬身施礼就要退去,连忙将国书放下,上前拉住苗贺龄的手,道,“小王看苗大人此行甚为机密,若苗大人现在一走了之,小王何处寻苗大人过府?”
苗贺龄道:“未听得太子答复,臣是不会走远的。”
段秉见拦不住他,便命人将苗贺龄小心送出府去,自己又将那书简展开,皱着眉细想,当指间轻轻滑触过“川遒、杜门、幽秦”六个字,却再不想掩盖兴奋的颤抖——失地二十余载,竟有索回的一天——段秉的热泪“扑”地打在洒金的白纸上。
正是阳光射入庭院的时候,书房里也是一亮,廊外水渠湍流不息,是上游开了闸将遒江水放了进来。段秉放下书简,坐在回廊的阴影里,掬起渠中的清冽透骨的水,漫声吟道:“三百里遒州国不在,空有冰河天际来……”
似乎有人听到了他的感慨,在远处笑了起来。
“苏先生回来了。”伴当禀道。
段秉忙站起身,向着施施然走近的宋别躬身施了一礼,“苏先生。”
“太子爷。”宋别过了石桥,敷衍着还礼,“听说太子府上来了位贵客。”
段秉笑道:“极尊贵。苏先生想是进门时没碰上。”
宋别此时已然是段秉最倚重的参谋,段秉诸事皆不避他,一如既往摊开了皇帝的书简给他看,静静等他阅毕,才问道:“苏先生觉得可为么?”
宋别也不答话,将卷轴举在阳光下,仔细检视庆熹帝的“靖仁”印信,半晌,点头道:“这印信果然是庆熹皇帝亲自加盖。”
段秉怔了怔,“印信的真假倒也好辨,只是先生如何得知是中原皇帝亲自加盖的呢?”
宋别指着方印右下角道:“但凡庆熹皇帝自己盖的印章,右下角的朱色总比通常淡些,想是他用力的习惯所致。他身处上位,也不必注意修正这些小节,故而还是能分辨的。”
段秉追着问道:“苏先生在哪里见过这好些中原皇帝密函印信?”
宋别摇头大笑:“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足为外人道也。”
段秉腼腆笑了笑,道:“是,先生足智多谋,阅历广阔,我年纪轻,好些事都不懂的。”
“太子爷千金之子,无须万事亲躬。”宋别道,“我草莽之人,谈不上智谋阅历,不过有用之处,太子爷用之,无用之时,容我逍遥自去,也就罢了。”
“苏先生言重了。”段秉目中不露丝毫闪躲之意,认真道,“先生于我,是良师益友。”
“太子爷若如此做想,我苏还定为太子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别叹了口气,撂下庆熹帝的书简,又道:“大理王室英杰辈出,就算是前面二三十年国贫民弱,遭人掠地数百里,到了太子爷这一代,只要励精图治,克复我北国失地,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段秉身子轻轻震了震,微微俯身凑近了些,道:“先生觉得我有指望克复川遒等五州?”
宋别微笑道:“不但是指望,更要紧的是,中原皇帝已将其中三座城池白纸黑字写给了小王爷。”
段秉叹道:“一枚靖仁印只怕做不得准。”
宋别道:“太子爷为什么怕它做不得准?”
段秉被他问得一怔,想了想道:“先生?”
“太子爷请想,这川遒五州现今是谁的?”
“中原。”
“并非如此。”宋别摇头道,“川遒现在不是中原皇帝的,也不是大理王的,这五州现在正是西王白东楼的囊中之物。”
段秉叹道:“我道中原皇帝这封国书就是一纸空文,果然不错。”
宋别摇了摇头,道:“太子爷错会了中原皇帝的意思了。”
“小王愚昧,先生请指教,”段秉道,“中原皇帝的真意究竟是什么?”
宋别道:“太子爷,当年中原发兵南下取大理,大理为何无力相抗?”
段秉道:“大理小国寡民,兵力不过五六万,白东楼率中原大军十万,势如破竹,若非遒江阻了一阻,当年大理便亡国了。”
宋别点头道:“白东楼就此驻守中原西南边境,此后他的十万大军又去了哪里?”
“后几年匈奴南下,大理又无力光复失地,中原无须顾忌西南边境,便调兵北上。西王麾下当时只留有两万兵力而已。”
“现在呢?”宋别问道。
段秉道:“现今西王统兵四万,而大理这些年武治下来,步兵五万,骑兵三万,另有水师两万人,渐渐的也有些抬头的气候了。”
“不错。”宋别道,“我国兵力与中原全境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而比之西王白东楼,不可不说占优了。”
段秉突然“哦”了一声,垂目思索半晌,方才望着宋别道:“苏先生的意思是……”
宋别笑道:“太子爷当说是庆熹皇帝的意思罢。”
“是。”段秉皱着眉道,“庆熹皇帝的意思是,川遒、杜门、幽秦三州均属白东楼封地,皇帝自己也不得染指,若大理愿出兵平定苗疆,这三州便由大理取之自便,中原皇帝的屯兵绝不插手阻挠。”
“正是。”宋别道,“匈奴犯中原北境,乱世里,群雄蠢蠢欲动,尤以东西两王是中原皇帝心腹大患,他想借大理势力牵制西王,早盘算了许久了。”
段秉道:“先生看此事可行么?”
宋别道:“从兵力上看,白东楼一隅之师,绝非大理对手,以一国之力伐一藩之兵,为何没有胜算?”
“若我发兵取下川遒,中原震北军回朝之后,庆熹皇帝会不会出尔反尔,重犯我边境?”
宋别道:“十年之内绝无可能。”
“先生为何有这等把握?”
“中原之患在内不在外,庆熹皇帝待有暇南顾大理时,定已平定藩王。以这四家藩王来看,无论如何也要周旋十年以上方有个分晓。”
段秉点头,“先生说的有道理。”
宋别道:“若此时不取川遒,等中原皇帝从北边分身出来,再取,可就没有籍口,没有机会了。”
段秉忽而问道:“有没有克复全部失地的可能?”
“太子爷,驻守三州,要对付的不但是西王,还有苗人。十万兵马虽有余力,暂时却也不宜得寸进尺。以这三州为根本,逐步平抚西王藩内苗人百姓,招募兵勇,多遣坐探监视西王属地,一旦中原生变,即可发兵取龙门全境。中原藩王最强者当属洪州亲王,若庆熹皇帝与其纠缠日久,大理便可出龙门,夺取瞿州、梧州、巢州,如此便可借寒江、别水天险,与中原划江而治,大理的基业也就奠定得差不多了。”宋别顿了一顿,微笑道,“那时太子面南称帝,又有何不可?”
“皇帝?”段秉语声短促,听起来似乎压抑着的一声尖叫。
宋别安详思索,有一瞬间的神游物外,漫声叹道:“大理国这个名字,届时也不合适了吧。”
“先生说笑了。”段秉低沉地笑着。
“或许吧,”宋别道,“不过要看太子是不是当笑话听呢。”
段秉弯起的嘴角因为瞬间的决心而变得稍稍有些僵硬,“大理人想出龙门,碰到的第一个敌手就是西王白东楼,应趁一切可趁之机予他消耗打击,我看出兵襄助中原平苗,收复川遒失地,势在必行。”
“二十四载失地,由太子一举收复,太子殿下民心所向,定受大理百姓崇仰。”
段秉象是被椅子上的刺扎到了一下,突地一震,“先生说错了,此番若能如愿出兵,收复失地的也是父王陛下。”
仿佛拼了力才能想起有大理王这个人似的,宋别仰起头来,皱了皱眉,“哦,对。”他懒洋洋地道。
就内臣而言,如意在大理太子府内的地位已极为尊崇,撇开中原皇帝钦命的司礼监提督太监、内廷和亲御使的身份不谈,他的聪慧潇洒和谨慎妥帖,就足以博得段秉器重喜爱,更难得的是他为人和气,在府中的人缘极好,因而段秉常对宋别感慨,自己身边为什么就是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你们多和如意学着些罢。”段秉曾当着如意的面对府中的内臣总管王桂道,“今后要多亲多近。”
那总管太监王桂极听话,对如意不住嘘寒问暖,衣食自不必说了,只要如意想出门,都有他巴巴地在角门外备了车轿,请如意登乘。
大理太子府于如意来说,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晚上再无需值夜,能容他隔三岔五地宿于府外。他通常去的,无外乎花街柳巷,今夜虽有正经差事,却只怕王桂备下车轿等着自己带路去寻苗贺龄,只得打定主意先乘轿去吃几杯花酒,再另行脱身了。
他便衣出行,到得角门前,却不见王桂同平日里一般上前询问去向,侍卫们也只是笑嘻嘻同他打了招呼,问道:“公公还是明日一早回来?”
“正是。”如意笑道,“怎么没瞧见王总管?”
侍卫们敷衍道:“公公从里面出来,没有瞧见,我们这些在外当差的,更瞧不见了。”
“说的是,说的是。”如意笑着,在门前四处张望平时坐的轿子。
角门外青石铺的大街竟是人畜全无,干干净净的,夕阳没有丝毫阻碍地照着,一地明晃晃的艳红,看着让人觉得暑气扑面。
如意甩开扇子遮在头顶上,迎着阳光向西行去。太子府也只是段秉从前的府第,并不甚大,一会儿便走到了围墙的尽头。如意想起什么来似的,拍拍脑袋,突然转过身。
数丈开外的汉子,让阳光迷了眼,一时看不清如意的举动,不由怔了怔。如意只一瞬已将他看得清楚,回过头,一笑间悠然转过街角,不动声色疾行出十多丈,顿时将身后那汉子落得远远的,再转过几条街,更是将他甩得不见了。
如意却不急着就行,行人稀少处,仰头望见左边院墙高耸,墙内的树桠浓密,他衣袖一拂间足尖轻点,飘摇荡在枝头,隐身树阴之中,自高处俯视街道。
过了半晌,跟在如意身后的汉子一溜小跑着赶上前来,见街上已空无一人,急忙奔到街口呼啸了一声,拐角处一会儿便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