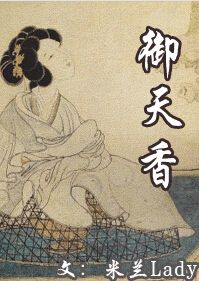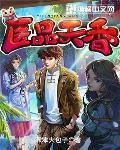天香-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住过楠木楼,她们谁住过啊?荞麦趁了话说:那你还气什么呀?大太太待你不薄,心里并没有分先后高低,要说伦理,大少爷是你的晚辈,他添了女儿,你也当奶奶了。小桃发作一通,心里到底宽敞了些,再看见两个花狸猫,不禁笑一下,这场气就如同先前无数场气,过去了。不过,已经离席,就不方便再回去,两对母子就在水榭里坐着,对了荷影波光,吃着炭烤的荸荠,说些女儿家的心里话。一艘采菱船悄没声息过来,贴近水榭时,忽将一大串菱角连泥带水抛上来,水榭里人吓一大跳,接着就开始剥菱角吃了。
中途离席的还有一人,就是镇海。日里读书读乏了,坐在席上就犯了困,趁人不备溜出来,回宅子睡觉。不料月光下荷风吹拂,忽然无比清醒。这园子里常是欢声笑语,锦绣升华,少见如此静谧,镇海一时倒不想回去了。一个人信步走着,也不辨方向,仿佛走在另一个园子里,陌生而且新鲜。走过山石,又走过桃林,听见有熟透的果实挂不住枝,落在地上,沉甸甸的声响,一落一个坑。再又回到池子,沿池畔走一截,也看见了那艘采菱船,从荷叶底下穿过。池面上像是罩了纱,脚下的青石板则铺了水银,晶亮晶亮,其实是露水。走在青石板,不知怎么上了台阶,新凿的白石头,凿痕历历在目。正惊奇来到什么地方,眼前便让两扇黑漆门挡住,抬头向上,门楣上横了一块匾,写着两个字:“莲庵”。恍然悟过来,这就是近日内修起的新庙,据说里面住着一个疯和尚。静夜里,镇海变得很胆大,伸手推了推门,那门只是虚掩,一推即开。扑入眼帘的先是一潭月光,清水中有一个人,在打一套拳。那人光头,短衣,裤腿扎起,底下一双赤脚。看不出是哪一门的拳路,只觉得分外流利贯穿,四肢身体绵软无骨,任意曲折,却藕断丝连。转移腾挪只在三步方圆,送去收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镇海看得出神,身心似乎随之而动,就看出那线路分明是在空冥中画出一个一个圆,环环相扣,扣扣相连,不知觉中,做了一个收势,原地站住,正在圆心之中,那清水月光如同落潮一般落到了底。
一双炯炯的目光,看着镇海,并不吃惊,反像是意料中。两人隔几十步远,相对而望,停一时,那人做了个请的手势,镇海便上前去了。和尚引镇海穿过东一翼侧殿,殿后有一方天井,坐北一间极小的屋舍,即原先的香堂,和尚便在此起居。屋舍的后窗下有一条河,人称白莲泾。名叫白莲泾,其实并没有莲,而是白芦苇,苇花盛开,一岸数里的银流苏。屋舍里只一张竹床和一个草蒲团,和尚盘腿上床,镇海就坐蒲团。壁龛里点一盏清油灯,豆大的火苗,一动不动,结了灯花,自行脱落,摇曳一下,又止住。镇海想起和尚的传闻,此时并不觉怪诞,反是顺理成章,也是气氛使然。宁静的夜晚,明镜一般澄澈,人迹远隔,惟有一僧一俗。和尚不说话,看着镇海,脸上露出喜欢的样子,似乎就有一种款曲通来。镇海不由发问:师父从何方来?本来不指望有回答,因人们都说和尚是个哑巴,不料却听见有声音响起:从永乐来。镇海一愣怔,以为听错了,又问一遍:何方来?再回答“永乐”。镇海接着问:“永乐”又在何方?就听和尚冷笑一声:读书人连成祖的年号都不知道,书读进狗肚子里了?镇海又是一愣怔。听和尚言语粗鲁,犹如市井里的泼皮,但想出家人行的另一路规矩,不能套用世俗成见,继而则发现回答的有趣。从“永乐”来,是什么意思?不禁一阵悚然,背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可却有一种妙处,令人欲罢不能。镇海颤着声音问:师傅难道是永乐年间的人?和尚露出不耐来:不是告诉过你了吗!镇海不敢再多嘴,按捺住心中的好奇与不安。两人一上一下端坐着,听得见白莲泾里鱼虾跳出水面,那“噗”的一声。
月光如涌,澎湃灌进屋舍,那清油灯的一苗火,就成了一枚黄钉子。方才的惊悚渐渐从后背上退下,镇海静着,不作声,和尚自己说话了:知不知道三保太监?镇海点头。永乐三年,三保下西洋,六十二艘宝船,官兵水手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世人不知道,此外还有二百童子,和尚我就是其中一个。镇海不敢生疑,永乐年距今足有百多年,难道和尚有一百多岁,真的成仙了?和尚双手按在膝上,目光变得深邃,于是幽暗下来,似乎从时间狭道穿过,进入另一世界:听说过“煮海”吗?三保的船便是从万顷煮海上膛过,如同釜中的滚汤;食人树是灌木样的一丛丛,一旦接近,枝权立时伸开,哼都不及哼一声,就掠进去了;食人花是舔虫子一般舔进人去,花瓣是巨大肥厚的舌,布着鲜红的刺,是花的舌苔;还有人,穿草叶和树皮,每一部都有为首的,称作“甲比丹”,由人抬着往来,担架由藤条编成,铺花和草,那花草离了土还在长,从青藤架上淌下来,泥浆一般……镇海已经入神,顾不上分辨真假虚实,也顾不得生疑不生疑,只由和尚一径往下说。
学生!和尚唤一声,镇海答应道:听着呢!学生,知不知道三保下西洋是为什么?同好,和藩!镇海答。和尚摇头。寻惠帝下落?和尚又是一声轻笑:世人之见!镇海不服道:那么师父又如何以为?是找皇帝,不过是另一个,宋朝小皇帝赵昺,世人都说陆忠烈背着投了海,可谁是亲眼见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分明一桩无头案!镇海说:赵昺在琼崖投的海,如何往马六甲寻去了!和尚大笑几声:学生不知道海海相连?还不知道山不转水转?那南洋地方的甲比丹中,不知哪一个就是宋室里的人,有朝一日听说蒙古人走了,江山回归大汉,不定会如何干赶万赶地赶来,终究是个祸根子!镇海如入梦中,竞也觉着很有理,更谈不上要去辩驳什么,于是和尚更加滔滔不绝。白莲泾上忽飞起一只鹤,盘旋几周复又落入栖草中。园子那边的宴席大约已经散了,四下里没有半点人声,只听和尚的声音,黄钟大吕一般轰鸣:万幸的是,三保在南洋和西洋都留下咱们的人,作眼线和接应。听到此处,镇海略醒来些,发问说:一百多年,只怕已与土著杂配混淆。和尚又笑了,这一回笑得很真挚:学生又犯糊涂,汉人自有识别。什么识别?镇海追问。字!和尚说。
汉字!和尚眨眨眼睛,这是汉人的密记。镇海哦一声,和尚接着说:不止是留下的人,还是走散的人,就凭这个,无论多少年多少代,无论怎样混杂,都能找寻出来,最后聚拢——说到此,昂起头,叹道:我们走散多少人啊!怎么散的?镇海问,他按捺不下,不再怕和尚发怒。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简直不可思议。而且,显然是,和尚打开话匣子,关也关不上了。和尚回答:怎么散的?轻易就散了,煮海里藏着一种兽,像龟,但没有壳;像牛,无犄角;像蛇,则有四足;大小如成年的马,特巨的有一座屋脊的长和高,潜在船底,一拱背,船上人飞沫般溅出去无数,有溺死的,有让鱼吞肚里的,逃出一条命的,或复又上船,或上岸自取生路,这止是走散中的一种。说到此,和尚伫住,凝神片刻,眼神变得迷离:好比一场梦,又好比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倏忽间,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正德,历历而过,已到嘉靖!朝廷中不晓得有多少弑父弑君,草莽间又有多少英雄豪杰……镇海看他神志恍惚,唤一声师父,停一停,又唤一声。和尚梦醒了,四下里看看,看见镇海,自问道:身在何处?镇海提示道:莲庵,庵后面是白莲泾,庵前是荷池,我们家的天香园。和尚渐渐回过神:一直在找咱们的人,宝船起锚的码头,叫刘家港,泊了无数大船小船,就是没有当年的宝船,人也不是当年的人,与他们说话,都听不懂。和尚对着镇海,点点头:这位学生,是不是我们永乐的人? 镇海这时看出,和尚确是疯了,是个疯和尚。从蒲团上爬起,诺诺着退出屋舍,再又退出天井,从侧殿与正殿的夹道中跑走。跑过一片空地,拉开黑漆门,下了台阶,迎面看见甬道上灯笼络绎蜿蜒,纵横交错,红火火一片阡陌。原来宴席才散,并没有太晚。镇海紧走几步,追上哥哥。柯海问去了哪里,镇海只说随处走走,一起出园子,过方浜,回宅子了。
满月酒过后,老太太精神又差下来,先生换了几回药,并不见好,后来,连先生都换了。换来换去,无非是气虚,湿滞,热或者寒,说到底是上了年纪,寿数有限。儒世做主,让镇海速娶,是为冲喜。明世不及回家,信中托长兄全权操持。于是,距柯海娶亲只一年多,镇海就娶了。多少是仓猝的,就在镇海原先的屋子,又清出两间偏厦,比柯海少了院子,房间也窄了些。不过镇海生性素朴,并不以为简陋,柯海却不愿意了。因泰康桥计家是富户,嫁妆一定极丰厚,申家不能显单薄,所以极力主张将楠木楼给镇海做新房。儒世本来就觉楠木楼招摇,再让小辈住,就忒过分,都要折寿。无奈侄儿执意,他们的母亲呢,又怕亏待了小儿子,再说,那楠木楼闲置着也是闲置着。老太太镇日躺着,听话都嫌伤神,也没法主张什么,儒世就只好随他们去了。所以,镇海的新房做在了楠木楼上,还有一个人心下反对,就是小桃。本来呢,老爷回来,她还想着住回楠木楼,如今一来,再不能了。难免又生一场气,再让荞麦劝好。那边意见牢骚着,这边忙着办各样事:辞岁,祭祖,过年,人正月,初一初二,紧接着到了初六,就是迎娶的日子。
果然,嫁妆摆了一条街。那领轿子,也是蓝色绸,凤与霞的华盖,底下绣了三面的桃红大花朵。嵌了绿叶,轿帘则是一幅粉绿粉黄满天星,一路叮哨盈耳,原来星星上缀了琉璃。家中人无不咂舌,庆幸新房安在楠木楼,连小桃都服气不作声了。老太太勉强起来,受过新人的叩拜,又躺回去。礼仪宴席照常,一项一项走过。楠木楼贴了喜字,结了红绸,张起红纱灯,碗口粗的红蜡烛,蜡油滚滚淌下来。夜里竞下起瑞雪,窗棂、瓦行,铺一层白绒,映着屋内的满堂红,明丽鲜艳又吉祥。
老太太却一径弱下去。先生说过了立春就有起色,于是过了立春;先生又说过了雨水就转轻,又熬过雨水;先生再说过春分,春分过了,不好也不坏,以为要有起色,不料三天之后突然犯了痰症,急喘了一日,到天黑睁眼看看。床跟前围了一周人,密密匝匝,就缺一个申明世。眼睛找了找,不等众人告诉,自己先说了:他赶不来了!说罢便闭了眼。这一家,办了一串红事,到底轮到办白的了。
宅子里无须说,天香园内如同梨花开一般,枝头草尖全系了白绫子。桃花又纷纷开了,恰有一种是白花,也像是白绫子,粉色的那种,间在其中,应出喜丧的意思。灯罩,桌围,椅套,屏风,换成一色的白,蜡烛改成白蜡烛。传出去,沪上人又当是天香园里一景,题名“三月雪”。守灵,垂吊,入殓,盖棺,停灵在莲庵,等申明世回家后再定日子出殡。先请一班和尚道士,进庵内念经,钟罄声声,香烟阵阵。人都说老太太有筹划,早在事前修了庵子,正用上了。三七这一日,申明世到家了,不顾车马劳顿,直接进了莲庵,重重青布幔子,掩了一具棺椁。想起母亲一贯的宠爱,将自己当个宝,做什么都是天下第一,要拿来夸嘴。虽然没有做过让母亲打嘴的事,也是心心意意要争体面,母子可说是心连心,可最后没能守在跟前,让老母亲合眼,反是添了牵挂,究竟不能算作完孝。心里十分的愧疚,泪流满面。旁人一径地拉和劝,说老太太没等他回家再走实在是因为疼儿子,不想拖延了,借晚辈的寿数。要是一味的伤心,哭坏了身子反辜负老人的意愿。明世听了更加伤感,越发啼哭不止,引得柯海镇海一行人也跟着哭成一片。
择日子大殓过后,七七也过了,申儒世申明世兄弟俩方才能够安宁地说话。先是议论京师里的事,明世压低声告诉,当朝皇帝只顾炼丹成仙,那些年大事小事都由首辅严嵩说了算,后来皇上对他的心渐渐淡下去,终而至于免职,可严党里还有人呢!内阁里的人都不是吃素的,向来与严首辅犯顶,何况那伙武将:曾铣将领、总督张经、兵部员外郎杨继盛,都吃了大亏,或斩或杀,可是各自也有人!严嵩是从礼部出来的,于是都以为他们礼部是严的人,真是百口莫辩。这一年来,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简直苦不堪言。而且北京地方水土粗砺,景色荒凉,内心常是抑郁的,这回一接到报丧,立刻递上回籍丁忧的急请。儒世告诫说:朝中事故万不可与外人道,有人要问,说些花絮敷衍则可,江南这地方,向来超脱,可张士诚起兵割据,本朝方一开元,太祖就不信赖,必夹着尾巴做人。明世道:要说花絮真没什么可说的,做官是百业中最无味的一种,官中又数京官无味,地方上做官还有些风土可以见闻,那京师与蒙古人地方只隔一道长城,实已到边塞了!想想少时苦读,一心求功名,不曾想功名是用来做如此无滋无味的事,可不无聊得很。听到这里,儒世就不能苟同了:读书倒不全为仕途,自有一番人生的乐趣。明世嬉笑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儒世正色说:这种话正是对不读书人说的,不读书人哪里晓得这世上草草木木,风风云云皆有情义呢!明世同意了:不读书人即便张眼望万物亦不过山是山,水是水,读过书了,便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儒世点头:这才是书里乾坤!于是兄弟俩又说了一阵读书。
从读书说到寄居于安亭的震川先生,年已五十多,屡试屡败,又屡败屡试,不仅意志坚韧,读书不辍,还开讲堂授学,又写许多文章。有一篇《秦国公石记》,写的是有一回在陆家浜上,看见岸边坟地蒿草中,藏有一块石头,竟是秦国公的学宫石。秦国公为本乡人,南宋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一人,也有个园子,后来颓圮,园中太湖石流散四处,垒鸡窝垫茅坑,惟有这块学宫石,埋在草丛间,风餐露宿,一点没染污秽,终有一日,为震川先生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