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路,前往各家各户。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一些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
?
。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
。
《代价论》
乌托邦与圣贤郑也夫先生的《代价论》在哈佛燕京丛书里出版了,书在手边放了很长时间都没顾上看——我以为如果没有精力就读一本书,那是对作者的不敬。最近细看了一下,觉得也夫先生文笔流畅,书也读得很多,文献准备得比较充分。就书论书,应该说是本很好的书;但就书中包含的思想而论,又觉得颇为抵触。说来也怪,我太太是社会学家,我本人也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我对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越来越觉得隔膜。这本书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广,还提出一个哲理: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做什么事都要把代价考虑在内等等。这些想法是不错的,但我总觉有些问题当作技术问题看比当原则问题更恰当些。当你追求一种有利效果时,有若干不利的影响随之产生,这在工程上最常见不过,有很多描述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数学工具——换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弃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有多大用处就很难说了。中庸的思想放在一个只凭感觉做事的古代人脑子里会有用——比方说他要蒸馒头,记住中庸二字,就不会使馒头发酸或者碱大。但近代的化工技师就不需要记住中庸的原则,他要做的是测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称量苏打的分量。总而言之,我不以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处,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种偏见。我听到社会学家说过,西方人发明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今后我们要用中国人发明的整合方法作研究;又听到女权主义者说,男人发明的理性的方法过时了,我们要用感性的方法作研究。但我总以为,作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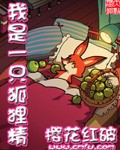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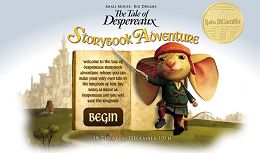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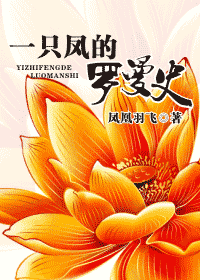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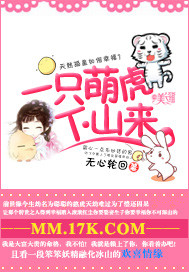
![[剑三]一只黄叽鸣翠柳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19/194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