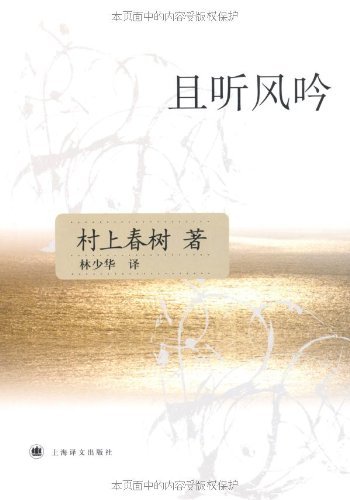且听风吟-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屁股上抹手一边说:
“噢。”
“给你看看?”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原来是女人的裸体照,其中间部位竟插着一个瓶子。“厉害吧?”
“的确。”
“来我家还有更厉害的哩!”他说。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这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18年时间里,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已经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忆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但上大学那年春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却从心底舒了口长气。
暑假和春假期间我都回来这里,而大多靠喝啤酒打发日子。
29
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时,我抓住杰寻风摸底:
“喂,你说鼠怎么了?”
“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为夏天快要完了?”
随着秋天的降临,鼠的心绪总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书,我向他搭话,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事。而到暮色苍茫凉风徐来四周氤氲几丝秋意的时分,鼠便一下子停止喝啤酒,而气急败坏似地大喝冰镇巴奔威士忌,无尽无休地往桌旁自动唱机里投放硬币,在弹子球机前手拍脚刨,直到亮起警告红灯,弄得杰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说。
“是吗?”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单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点点头。”那个女孩呢?”
“不久就会淡忘的,肯定。”
“有什么不愉快不成?”
“怎么说呢?”
杰含糊一句,接着去做他的事。我没再追问,往自动唱机里投下枚硬币,选了几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过了10多分钟,杰再次来我跟前问:
“怎么,鼠对你什么也没说?”
“嗯。”
“怪呀。”
“真的怪?”
杰一边反复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边深思起来。
“应该找你商量才是。”
“干嘛不开口?”
“难开口嘛。好像怕遭抢白。”
“哪里还会抢白!”
“看上去像是那样,以前我就有这个感觉。倒是个会体贴人的孩子。你嘛,怎么说呢,像是有毅然决然的果断之处,……
可不是说你的坏话。”
“知道。”
“只不过是我比你大20岁,碰上的晦气事也多。所以,怎么说好呢……”
“苦口婆心。”
“对啦。”
我笑着喝口啤酒:
“鼠那里由我说说看。”
“嗯,那就好。”
杰熄掉烟,转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进厕所,洗手时顺便照了照镜子,然后又快快地喝了瓶啤酒。
30
曾有过人人都试图冷静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烟,把即将在时间的积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识踢打起来,同时续写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热水淋浴,一天刮两回胡须,周而复始地听旧唱片。此时此刻,落后于时代的彼得.波尔和玛莉就在我背后喝道: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31
第二天,我邀鼠来到山脚下一家宾馆的游泳池。由于夏季将逝,且交通不便,池里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一半是美国住客:
他们与其说是游泳,莫如说是在专心晒日光浴。
这座由旧华族别墅改建成的酒店,有一方芳草凄凄的庭院,游泳池与主建筑之间隔着一道蔷薇篱笆,沿篱笆爬上略略高出的山坡,海面、港口和街市尽收眼底。
我和鼠在25米长的游泳池里竞相游了几个来回。然后并排躺在轻便折叠椅上,喝着冰镇可乐。我调整完呼吸抽罢一支烟的时间里,鼠愣愣地望着一个独自尽情游泳的美国少女。
万里无云的晴空,几架喷气式飞机留下几缕冻僵似的白线,倏然飞去。
“小时候天上的飞机好像更多来着。”鼠望了眼天空说:
“几乎清一色是美军飞机,有一对螺旋浆的双体家伙。记得?”
“p38?”
“不,运输机。比P38大得多,有时飞得很低很低,连空军标志都能看到。……此外记得的有DC6、DC7,还见过赛巴喷气式哩。”
“够老的了!”
“是啊,还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巡洋舰一进港,就满街都是美国军宪和水兵。见过美国军宪?”
“嗯。”
“好些东西都失去了。当然不是说我喜欢军人……”
我点点头。
“赛巴那飞机真是厉害,连凝固汽油弹都投得下来。见过凝固汽油弹下落的光景?”
“在战争影片里。”
“人这东西想出的名堂真是够多的,而且又都那么精妙。
再过10年,恐怕连凝固汽油弹都令人怀念也未可知。”
我笑着点燃第二支烟。“喜欢飞机?”
“想当飞行员来着,过去。可惜槁坏了眼睛,只好死心。”
“真的?”
“喜欢天空,百看不厌。当然不看也可以。”鼠沉默了5分钟,蓦然开口道:“有时候我无论如何都受不了,受不了自己有钱。恨不能一逃了事。你能理解?”
“无法理解。”我不禁愕然。“不过逃就是喽,要是真心那么想的话。”
“……或许那样最好,跑到一处陌生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也并不坏。”
“不回大学了?”
“算了。也无法回去嘛!”鼠从墨镜的背后用眼睛追逐仍在游泳的女孩。
“干嘛算了?”
“怎么说呢,大概因为厌烦了吧。可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就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归,如同椅子被人开玩笑抽走了一般。”
“往后做什么?”
鼠用毛巾擦着脚,沉吟多时。
“想写小说,你看如何!”
“还用说,那就写嘛!”
鼠点头。
“什么小说?”
“好小说,对自己来说。我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才能。但我想如果写,起码得写足以使自己本身受到启发的东西才行,否则没有意思。是吧?”
“是啊。”
“或是为自己本身写……或是为蝉写。”
“蝉?”
“嗯。”鼠捏弄了一会悬挂在裸胸前的肯尼迪铜饯。“几年前,我同一个女孩去过奈良。那是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午后,我俩在山路上走了3个小时。途中遇到的活物,只有留下一声尖叫拔地飞走的野鸟,和路旁扑楞翅膀的秋蝉。因为太热了。
“走了一大阵,我们找一处夏草整齐茂密的缓坡,弓身坐下,在沁人心脾的山风的吹拂中擦去汗水。斜坡下面横着一条很深的壕沟,对面是一处古坟,小岛一般高,上面长满苍郁的树木。是古代天皇的。看过?”
我点点头。
“那时我想、干嘛要建造成这么个庞然大物呢?……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坟墓都自有意义。就是说它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人迟早都是一死。问题是那家伙过于庞大。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说老实话,那家伙看上去根本就不像墓,是山。濠沟的水面上到处是青蛙和水草,周围栅栏挂满蜘蛛网。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说到这里,鼠喝掉泡沫早已消失的最后一口可乐。
“每次写东西,我都要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
说罢,鼠双手抱在脖后,默然望着天空。
“那……你是写什么了?”
“哪里,一行也没写成,什么也没写成。”
“是这样?”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如此说道。
黄昏时分,阳光黯谈下来,我们离开游泳池,跨进荡出曼托巴尼意大利民谣旋律的宾馆小酒巴,端起凉啤酒。宽大的窗口外面,港口的灯火历历在目。
“女孩怎么样了?”我咬咬牙问。
鼠用指甲剔去嘴边沾的酒沫,沉思似地望着天花板。
“说白啦,这件事原本打算什么也不告诉你来着。简直傻气得很。”
“不是想找我商量一次么?”
“那倒是。但想了一个晚上,还是免了。世上有的事情是奈何不得的。”
“比如说?”
“比如虫牙:一天突然作痛,谁来安慰都照痛不止,这一来,就开始对自己大为气恼,并接着对那些不对自己生气的家伙无端气恼起来。明白?”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你认真想想看:条件大伙都一样,就像同坐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诚然,有的运气好些有的运气差些,有的坚强些有些懦弱些,有的有钱有的没钱。但没有一个家伙怀有超平常人的自信,大家一个样,拥有什么的家伙生怕一旦失去,一无所有的家伙担心永远一无所有,大家一个样。所以,早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力争使自己多少怀有自信,哪怕装模作样也好,对吧?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有的不过是能够装出自信的人。”
“提个问题好么?”
我点点头。
“你果真这样认为?”
“嗯。”
鼠默然不语,久久盯着啤酒杯不动。
“就不能说是说谎?”鼠神情肃然。
我用车把鼠送回家,而后一个人走进爵士酒吧。
“说了?”
“说了。”
“那就好。”
杰说罢,把炸马铃薯片放在我面前。
32
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他的作品尽管量很庞大,却极少直接涉及人生、抱负和爱情。在比较严肃的(所谓严肃,即没有外星人或怪物出场之意)半自传性质的作品《绕虹一周半》(1937年)中,哈特费尔德多半以嘲讽、开玩笑和正话反说的语气,极为简洁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向这房间中至为神圣的书籍、即按字母顺序编印的电话号码薄发誓:写实、我仅仅写实。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
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具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的。至于如何辛苦、如何磨损,在此不一一叙述。因为很麻烦。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那么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哈特费尔德之所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为欣赏,原因之一是由于书中对一个人由生至死的过程描写得无微不至、有条不紊;二是由于它是一部长而又长的长篇。他一向认为,既然小说是一种情报,那就必须可以用图表和年表之类表现出来,而且其准确性同量堪成正比。
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往往持批评态度。他说,问题当然不在量的方面,而是其中宇宙观念的缺如,因而作品给人印象不够谐调。他使用到“宇宙观念”这一字眼时,大多意味该作品“不可救药”。
他最满意的小说是《佛兰德斯的狗》。他说:“喂,你能相信是为一幅画而死的?”
一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这样问哈特费尔德:
“您书中的主人公华尔德在火星上死了两次,金星上死了一次。这不矛盾么?”
哈特费尔德应道:
“你可知道时间在宇宙空间是怎样流转的?”
“不知道,”记者口答,“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
“把谁都知道的事写成小说,那究竟有何意味可言!”
哈特费尔德有部短篇小说叫《火星的井》,在他的作品中最为标新立异,仿佛暗示布拉德贝利的即将出现。书是很早以前读的,细节已经忘了,现将梗概写在下面:
那是一个青年钻进火星地表无数个无底深井的故事。井估计是几万年前由火星人挖掘的。奇特的是这些井全都巧妙地避开水脉。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挖这些东西出于什么目的。
实际上,除了这些井,火星人什么都未留下。没有文字没有住宅没有餐具没有铁没有墓没有火箭没有城镇没有自动售货机,连贝壳也没有。唯独有井。至于能否将其称为文明,作为地球人的学者甚难判断。的确,这些井建造得委实无懈可击,虽经几万年的岁月,而砖块却一块都未塌落。
不用说,曾有好几个探险家和考察队员钻进井去。携带绳索者,由于井纵向过深和横洞过长而不得不返回地面;未带绳索者,则无一人返回。
一天,一个在宇宙中往来仿惶的青年人钻人井内。他已经厌倦了宇宙的浩渺无垠,而期待悄然死去。随着身体的下降,青年觉得井洞逐渐变得舒服起来,一股奇妙的力开始温柔地包拢他的全身。下降大约1公里之后,他觅得一处合适的横洞,钻入其中,沿着曲曲折折的路漫无目的地走动不止。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表早已停了。或许两小时,也可能两天。全然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原先感觉到的不可思议的力依然包拢着他的身体。
某一时刻,他突然觉察到了日光,原来是横洞同别的井连在了一起。他沿井壁攀登,重新返回地面。他在井围弓身坐下,望着无遮无拦的茫茫荒野,又望望太阳。是有什么出了错!风的气息、太阳……太阳虽在中天,却如夕阳一般成了橙色的巨大块体。
“再过25万年,太阳就要爆炸,……oFF。25万年,时间也并不很长。”风向他窃窃私语,“用不着为我担心,我不过是风。假如你愿意,叫我火星人也没关系,听起来还不坏嘛!当然,话语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可你是在讲话。”
“我?讲话的是你。我只是给你的心一点提示。”
“太阳是怎么回事,到底?”
“老啦,奄奄一息。你我都毫无办法。”
“干嘛突如其来地……”
“不是突如其来。你在井内穿行之间,时光已流逝了约15亿年,正如你们的谚语所说,光阴似箭啊。你所穿行的井是沿着时间的斜坡开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