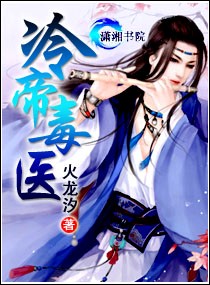我要做皇帝-第8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譬如许行先生当年从墨家脱离,建立农家。
看上去,也就只有一个杂家,因为地处安东之地,只顾着蒙头发展,暂时没有力气内讧和内斗。
粗粗统计了一下,刘彻就发现,现在天下大大小小,有着成员超过一百的学派派系,就起码有一两百个。
其中在一郡或者多郡之中存在影响力的学派,几乎有将近一百个。
主流的学派,林林总总也不少于三十!
任何看到这个数据的人,都会知道,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激烈而影响深远的思想大碰撞和大融合,其实已经近在眼前。
诸子百家,将再次捉对厮杀。
不过,与春秋战国的那一场思想大碰撞和大融合不同。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实际上是因为宗周的秩序崩溃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诸子百家的先贤们,目睹了列国混战,生民涂炭的惨状。
为了救亡图存或者再造太平,而纷纷各抒己见。
孔子认为世界的问题根源,在于成周礼法的崩溃,于是主张复古,克己复礼,认为只要回到宗周时代,天子执掌天下,礼乐秩序井然的时代,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而孔子的学生子夏先生,游学天下,目睹了秩序混乱带来的可怕现状,于是在魏国讲学,结合了子产先生等先贤的经验和理论,进行汇总,从而诞生了法家。
法家主张大一统,一切唯上,用法律和秩序约束人民,管理人民,尽地力之教,最终富国强兵!
而与此同时墨翟先生,高举兼爱非攻等大旗,站到儒家的对立面,开始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
自儒法墨之后。
以齐国稷下学苑和列国的学官老人为首的先贤们,在管子、尸子等先贤的基础上,以黄帝和老子为旗号,宣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这就是黄老派的诞生。
自是之后,又有名家、杂家、小说家、兵家等无数个学派崛起。
一时间神州尽人杰。
曾子、子夏、孟子、李悝、吴起、商君、韩非子、吕不韦,纷纷粉墨登台。
还有张仪苏秦,靠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天下人,风光无边。
至此,其实,先秦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建立健全了中国的思想派系的脉络和大方向。
后人基本上都是要围绕他们的成果而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进行阐发。
而如今,却又不同。
现在,诸子百家的巨头们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天下形势,与他们的祖师爷完全不同。
今日的汉室,虽然还说不上四海升平,九州道路豺狼。
但却也是安稳和平的盛世时光。
商贾势力大兴,各地的工商业越发兴盛,由此带动了天下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
特别是安东的屯垦移民以及淘金潮的到来,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各个学派,于是不再局限于某地。
而是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天下延伸。
这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也带来了许多新挑战。
这迫使诸子百家中的聪明人和有远见者,不得不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鲁儒就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而在近几年,不断衰落,如今甚至连老巢都要公羊派和谷梁派给端了的悲剧。
正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其他人看到鲁儒的惨状,但凡有些危机感的,都不得不加快强大自身的进程。
于是,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学派巨头,都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蹲下身子,仔细审查民间民情和天下变化。
而不能再跟过去一般,高高在上的谈着什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不顾实际和现实,非要谈论遥不可及的三代之治。
这样做的家伙,肯定会被时代淘汰!
而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肯定会出现不同想法和不同思考方向的人。
而这些人提出来的思想理论和应变之道,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渐渐形成一个个看上去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南辕北辙的派系。
譬如,思孟学派和重民派,都在高举孟子的旗号,主张仁以爱人,义之所在万死不辞。
但实际上呢?
思孟学派,宣扬的是‘仁义礼智善’,讲究的是诚心诚意的对待学问,有些类似苦行僧一样,认为只要心诚,自然学问做得好,学问做得好,自然是君子,君子自可治世。
总的来说,还是儒家的那老一套。
但重民学派则不同。
他虽然也主张仁以爱人,将孟子视为祖师爷。
但它彻底摒弃了个人道德和行为对天下造成的影响。
重民学派认为,只要有利于百姓,有利于民生,有利于人民,哪怕是小人,做的事情,那也是好的。
反之,道德水平再max,也可能误国。
对此,这两派口水仗已经打了无数回。
彼此都宣布开除了对方‘孟子传人’的身份。
而从绣衣卫的档案和报告里,也能看出这两个学派所依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
思孟学派是兴盛于梁国和三河地区一带,主要依托地主和士大夫阶级的学派。
而重民学派的大本营则是在当世商人氛围最浓厚的雒阳,其主要支持者和金主,是雒阳、睢阳、荥阳以及关中的某些大地主、大商人和大贵族。
这自然就决定两者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
将所有的这些,在心里过了一遍,刘彻走出自己的御书房,来到外面,望着这繁华的世界,璀璨的世界,道:“制诏:朕闻,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今天下有诸子,或曰孔子之学,或曰申韩之士,或曰黄老之长者,或曰墨翟之门徒,皆博闻多识,有治世之才!
今朕夙兴夜寐,愿与宇内之士,臻于圣道。
其于石渠阁,备酒三樽,静候天下名士,与共稽参政务!”
立刻就有尚书郎领命,录诏,然后稍加润笔后进献刘彻案前,刘彻在检查完后,随即在上面加盖自己的天子印玺,然后将它交给一位侍中,嘱托道:“下御史,颁布天下!”
这不是国政,也不是政策的发布命令。
只是一道对天下诸子百家各大学派巨头的征集令。
自然根本不需要御史大夫衙门讨论,然后交由廷议商议。
皇帝一言可决!
所以,接到诏书后的御史大夫晁错几乎没有怎么考虑,立刻就在诏书上附署名字,然后将它交给御史监,嘱托道:“贴于露布,更令传骑,布天下郡县!”
而自己则急匆匆的抬脚出门,去找自己的老师张恢。
去干什么?
当然是抢走所有人前面,先给自己的派系,在即将举行的石渠阁会议中,多占几个位置!
天子诏书上说的很清楚‘敬备浊酒,恭候石渠阁之殿,与天下名士,稽参政务,共论国策’。
石渠阁才多大?
晁错是很清楚的,哪怕是司马谈和司马寄主将他们的办公阁楼让出来,再腾出石渠阁外围的阁楼,撑死了也就够同时容纳四百人与会,甚至,很可能最终只能容纳三百五十人左右。
而在这其中,天子、贵戚以及两千石大臣还有将军列侯,起码要占走五十席。
留给诸子百家的席位,很可能只有不过三百席。
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少得可怜。
旁的不说,以黄老派跟东宫的关系,最少有三十席要被黄老占走。
另外墨家跟天子的关系也足以保证,是个墨者就能列席。
这就又起码少了三四十席。
而这次天子忽然要召开的这个石渠阁会议,很可能将决定未来诸子百家的兴衰。
这样的重要会议,自然自己这边列席的人越多,其他派系的席位就越少,发言权就越低。
别看现在,儒法之间如胶似漆。
但,遇到这个事情时,晁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给儒家报信。
对晁错来说,儒家与法家现在的合作,其实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若有可能,法家当然是希望在儒家头上踩一脚,背上插一刀。
全本欢迎您! t1706231537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节 合纵(1)
当华灯初上之时,董仲舒乘着马车,停留在自己的师兄胡毋生的府邸外,望着胡府高大的门庭,犹豫了一会。
早在今上即位之前,董仲舒与自己的师兄在对公羊学的理论上就出现了分歧。
而且这个分歧已经大到了两人从此形同陌路的地步!
但那个时候,两人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
而现在?
两人实际上就差撕破脸面对喷了。
私底下,谈论对方的学问,更是毫不客气。
两人的弟子门徒见面,也肯定不会给对方好脸色。
究其原因,还是现在两人彻底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一个主张我注春秋,另外一个主张春秋注我,在立义、思想和学术方面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而且,两人都身为太学教授,各自门下都有着一个学苑,彼此相互争夺影响力和学生。
这更使得两人之间的恩怨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若非必要,董仲舒是不愿意来见自己的师兄的。
但……
“未央宫有传言,天子要在此番石渠阁会议之中,厘定某些纠纷,清理某些‘不合时宜’的理论,至少要将之逐出太学的课本和考举的考试范围……”董仲舒在心里想着这个刚刚得到的了不得的传言,心里面也就顾不得面子了。
毕竟,当今天子的脑回路异于其父祖,更类似高帝。
而高帝是什么人?
天底下头号的仇儒帝王。
自打他起兵那天开始,就瞧不起儒生,更看不上儒家的学问和理论。
在儒生帽子里撒尿,当众痛骂儒生,这都是小kiss。
人家做的对儒家伤害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当年在陈留城外,那一句‘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和其后的‘延客人’,至今仍然是天下诸子百家耻笑儒生的口头禅。
一句‘吾高阳酒、徒’,足可让任何派系的儒生掩面而走。
至于当年,叔孙通戴儒冠,高帝不喜,其后改戴楚人冠,高帝大悦,更是无比深刻的反应出了这位汉家的开国之主,对于儒生的态度除了讨厌和厌烦之外,没有其余感观了。
这也就难怪当年项王乌江自刎后,鲁地儒生要举兵反抗,还披麻戴孝,声称要为项王尽忠了。
实在是,汉天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会优待儒生的君王。
甚至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比他更尊重儒生。
最起码,秦始皇没有在儒生帽子里撒尿……更不曾一脚将儒生踹到泥潭里去喝泥水……
好在,今上还只是类似高帝。
对儒生和儒家,只有提防和警惕,而没有厌恶和厌烦。
不然的话,董仲舒估计自己能回家种田,都已经是老天保佑了!
而如今,类似石渠阁会议这样的大事。
自然容不得半点闪失。
公羊学派,即便不能在石渠阁之上,一鸣惊人,天下知名,至少也得守住自己的基本盘和基本要义。
决不能让谷梁派翻盘,更加不能让荀子学派骑到脑袋上拉屎屙尿!
这样的场面,仅仅只是想想都恶心死了,更别提万一变成真的该怎么办了!
想到这里,董仲舒终于放下心里的芥蒂,对自己的门徒道:“去,递拜帖,言我欲拜问师兄!”
“诺!”那门徒犹豫片刻,还是领命而去。
不久后,胡府的大门洞开,董仲舒看到自己的师兄胡毋生,领着他的几个弟子门徒,亲自出迎。
“师弟……”胡毋生长揖道:“许久未见,师弟依然风华如初……某却已经老朽拉……”
董仲舒连忙下车,敬拜道:“仲舒不才,竟蒙师兄出迎,受宠若惊!”
而董仲舒的随行弟子门徒,也都恭敬的对着胡毋生拜道:“见过胡子!”
胡毋生的门徒也纷纷回礼:“见过董子……”
胡毋生笑着上前,挽起董仲舒的臂膀,说道:“师弟来的正好,吾正有些事情,与师弟分说,今夜,你我师兄弟当痛饮彻夜,谈论古今……”
“唯!”董仲舒连忙道:“敢不从命……”
然后,他的眼睛就在一位站在胡毋生身侧的中年官吏身上停留许久。
那人,董仲舒很熟悉。
就是现在胡毋生的头号得意弟子,同时也是儒家目前在官场唯二的两个天子亲信之一,主爵都尉公孙弘。
望着这个外貌俊朗,据说能力非常出色,屡屡得到天子赞许的男子,董仲舒在心里叹了口气。
谁又能知道,仅仅在七八年前,这位当今天子的宠臣,心腹,还只是薛县山陵之中的一个放羊人,靠着牧羊维生。
穷困潦倒,甚至被人悔婚,几乎成为了世界的弃儿。
当年,公孙弘曾经到处拜师。
甚至,只要有人教,便是做牛做马也愿意。
但包括他董仲舒在内的许多人,在考察过后,都放弃了他。
因为他年纪很大,已经过了求学的黄金年纪,更因为他自学过《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著作。
对于儒家而言,杂家虽然说不是敌人,但也属于异端。
儒生们读过吕氏春秋的人很多,但从来没有人会主动去教导一个读过吕氏春秋的人。
只有胡毋生当时顶着压力,收下了这个当年衣冠破旧,潦倒穷困的男人。
而现在,事实证明了,这是一颗璞玉,而且是大器晚成的璞玉。
此人这几年,几乎成为了胡氏公羊学的活广告。
无数的列侯贵戚和大地主,都挥舞着金钱,死也要将一个子弟塞到胡子门下教导。
至于商人们,更是跪舔都来不及!
因为公孙弘,就是主管天下工商秩序和税收的最高官员!
想到这里,董仲舒就不禁有些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