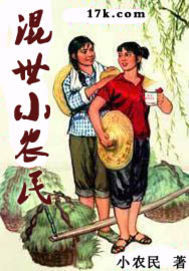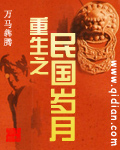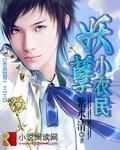吾国与吾民-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语言与思维
中国文学的媒介(亦即汉语)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汉语中像“jing”、“chong”、“zhang”①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进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性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性。
『①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具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于没有一个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00个作为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声调不计在内),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每一个新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scraped”、“splash”、“sc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这种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种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物或行为的时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种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乱,直到汉代书写体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符号(称“部首”)来表示各种不同意义的“包”。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确定的。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些字,它们的发音都是“bao”或“pao”,在现代汉语里声调不同,每个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
抱、跑、袍、饱、泡、炮、鲍、胞、炮、咆、刨、苞、雹,这样,“包”加上“手”表示“围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长袍”,加上“食”表示“吃饱”,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鱼”表示一种“鱼”的名称,加上“肉”表示“子宫”,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进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ped”“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pe”与“scape”、“scape”与“scrape”、“scrape”与“scraped”,以及“scra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其结果就必然需要有符号字母来指示“s、r、ed(t)、p、ch”等等。要是中国人做到这点,他们就会有字母,他们中有文字能力的人也就更加普遍。
然而,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这个事实本身就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学习的特性与地位。由于中国文字本身的特点,其字形在口语中同样反映不出来。一个语符在各种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就像基督教里的十字架在英语里念作“cross”,在法语里读成“croix”一样。这与老大帝国统一的文化有紧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汉字的使用,人们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多年之后尚能阅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孔学的经典如果在公元六世纪时就不为人们读懂,那么孔学的崇高地位又将发生何许变化呢?
确实,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经受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如今连孔门学者部分为两大阵营:一派相信古文经学,研究孔宅壁缝里免遭劫难留存下来的书籍,另一派则相信今文经学,研究那些年老学者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经典,这些老人在短命的秦朝幸免于难。然而始自公元前213年,持续出现了不少儒学著作,其形式相对来讲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革。这些著作要为儒家经典作用于中国人心灵的催眠力负大部分的责任。
只要符合孔学早期著作,也就合乎整个文学传统,汉代以后尤为如此,一个中国学生只要能读懂一百年前的著作,也就能使自己读懂13世纪、10世纪乃至2世纪的作品,这种方便程度如同一个现代艺术家能够像欣赏罗丹的作品那样欣赏维纳斯。人们会纳闷,如果过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末古代传统的力量还会如此之盛吗?中国人的心灵还会这样保守,这样囿于过去吗?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文字的使用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学语言,称文言,它与口语全然不同,因而也远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对口头语言的记录自然要随活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言由于不太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在习语和语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口语规则的束缚,并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结构规律和大量的习语,这些都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积累下来。于是书面语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过多多少少也随着不同文学样式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语言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文言与口语两者的句子结构规律也大相径庭,因而仅仅把现代汉语的词句换成文言的同句,还远不足以称为文言文。比如“三两银子”,就必须在句法上能换为“银三两”,又如现代汉语中“我从未见过”,就必须写成“余未之见也”,宾语通常放在否定动词的前面。现今的中小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常易犯习惯用法上的错误,正如初学法语的英国学生会说“je vois vous”一样。如同学习外语需要大量接触才能真正掌握其习惯用法,同样,文言写作也需要把名篇佳作反复背诵多年(至少十年),然后才能写出像样的文章,也正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掌握一门外语一样,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能够写出真正符合语法习惯的文言文。事实上,现在只有三四个中国人能写出符合周代语言习惯的文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忍受那种连外国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充满书卷气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失却了母语的真味。
中国式文字的使用使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而且,文字与语音的脱节又加强了文字的单音节性。事实上,口语中的双音节词在文章里是可以用单音节字来表现的,因为字体结构本身已经使意义十分明确了。于是,我们在口语中需要讲“老虎”,以区别于其他超过一打的发音相同的字眼儿,但在书面语中一个“虎”字也就足够了。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口语,因为其背景是阅读而非口头发音。
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炼的风格,在口语中很难模仿,因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它却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音节的标准诗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语白韵诗两行的内容,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绝难想象的。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散文中,这种词语的凝炼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其中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如同那些一丝不苟的诗人,中国的散文作家对每一个音节也都谨慎小心。这种洗炼风格的娴熟运用意味着词语选择上的炉火纯青。先是在文学传统上青睐文绉绉的词语,而后成为一种社会传统,最后变成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这些文学技巧造就的困难,使得中国识字的人极其有限,这一点无需详述。识字人的有限又反过来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气质。人们有时会想,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语,那末中国人对他们的上级还会如此温顺和谦恭吗?我时常感到,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其语言中多保留一些词首或词尾的辅音,那末他们不仅能够动摇孔子权威的基础,并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结构,让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出现长期的承平气象,并在其他方面得以稳步前进,发明更多诸如印刷术、火箭之类的东西来影响这个行星上人类文明的历史。
学术成就
我们有一种非经典性的文学,也就是由那些敢于打破经典性传统的无名作家所创作的想象的文学。他们直抒胸臆,为创作所带来的欢乐而进行创作。
在讨论这些构成西方意义上的优秀小说和戏剧之前,也许应该先考虑一下经典文学的内涵,考虑一下中国文学的特性,考虑一下众多的文入学士们的生活与教养。他们靠人民养活,主要从事道德说教,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创造。那末,这些学者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学者的国度,文人学士是统治阶级。至少在天下承平之年,十分提倡对学术的崇尚。这种对学术的崇尚甚至已经达到一种普遍的迷信程度,任何写有文字的纸张都不可随意丢弃或派其他不适当的用场,而是应该收集起来焚于学堂或寺庙内。战乱年代,情形稍有不同,兵丁常常闯入文入学士家中,不是把古本珍本藏书用来饶火,就是用来擤鼻子,或者干脆连房子一股脑儿付之一炬。然而这个民族的文字活力过于旺盛,兵丁们书烧得越多,人们藏书的规模却越大。
在公元600年左右的隋朝,皇家藏书已达37万册。到了唐朝,皇家藏书计有20万零8千册。1005年的宋朝,编就了第一部类书,共计1000卷。接下去一个御览版本是《永乐大典》,由永乐皇帝(1403~1424)召集人员编成,计有22877卷,装成11995册,收集了经过编选的古代稀有著作,清朝,乾隆皇帝最具有政治家风度之一举,乃是诏令彻底清查尚存的书籍。其表面目的是要将其加以保存,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是销毁那些对满族统治流露不满的著作。他成功地收集了36275卷册,全书缮写成七部,定名为《四库全书》。但他也同样成功地或部分或全部销毁约2000部书籍(其中有的部分罹难,有的则是全书遭到厄运)。这次运动造成的文字狱约达20起之多,作者或被革职,或被监禁,或被鞭打,有的甚至丧命,有的宗祠遭毁,有的家人被卖为奴——这一切都仅仅因为一字之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所收书籍,都是依照正统标准认为值得加以保存的。有不少书籍仅在提要里简略介绍了一下,却没能收入《四库全书》以期永久流传。这些准备永久保存的书籍当然不会包括像《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名符其实的独创性著作。不过其中包括大量的“笔记”,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从历史考据到香茗名泉,以及狐仙、水怪、节妇的小品,都是中国学者的兴趣所在。
那么,这些书里讲些什么呢?考察一下由《四库全书》统一流传下来的中国国书的正统的分类系统是十分有趣的。中国的书籍分成四个大类:(一)经,(二)史,(三)子,(四)集。经部包括经籍及其注释书籍,这浪费了中国学者的大部分光阴。史部包括断代史、专门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记或名山志)、行政体系、法律、法规、书目文献和历史批评,干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诸子,后来包括中国各种专门技艺和科学(正如西方大学里的哲学),有军事、农业、医药、天文、占星、巫术、算命、拳术、书画、音乐、房屋装饰、烹任、草木鸟兽虫鱼、孔学、佛学、道学、参考书籍,以及许多上面已经提及的“笔记”,记载了杂乱无章、未经筛选、道听途说、未曾分类的资料,内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现象,尤其偏爱那些怪诞的和超自然的现象。在流行书铺内,小说也划入此类。集部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了学者的文集、文学批评,以及专门的诗歌集和戏剧集。
科学的分类总比其内容显得更加仪表堂堂。事实上,中国并无专门的科学可言,只有系统解释古籍经典的小学和史学确实是经过确切分类的知识的分支,也给人们提供了煞费苦心去钻研的领域。天文学中除了那稣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与占星术极为接近,动物学和植物学十分接近烹任法,因为许多动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一般书铺里,医学通常与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个书架上;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和政治经济学都蕴藏在笔记之类的书籍里,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划入子集的动植物学和史集的杂录之中,他们获此殊荣是因为他们笔记的专门化性质,但是他们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韵和技巧上,与集部的那些笔记并无根本区别。
大体上,中国学者有三条造就天才的途径:真正的学术研究,科举仕途,还有经籍意义上的文学。我们可以照此把中国的读书人分为三种类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