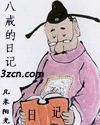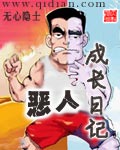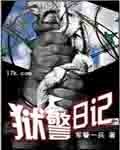北大考研日记-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诗歌中也会有阳光灿烂的文字出现?我相信这种假设的确有实现的可能,爱情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根据西渡等人的调查,事情的发生可能是这样:9月22日下午,他约了女朋友在某个汽车站会面。但她没有赴约。23日他给女朋友家打了电话,但她显然在躲他,晚上他到女朋友家附近再打电话,对方父母冷淡地拒绝了他。他见事已无可挽回,便回到了花园村宿舍,这时大概已经相当晚,因为没有人见到他。他收拾了诗稿和一些朋友间的来往信件,装进他平常用的一只黑包,便离开了。他大概走到了北大,将诗稿和信件连包扔进了未名湖北边朗润园的一间公厕,然后出北大向北至万泉河边。他的遗体是在清华园中发现的。他的遗体也许是随水漂进清华园的,但也可能是在清华园直接入水的,也许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深夜的清华园一定静谧无人,很适合一个人完成最后的行动。
一颗没有得到爱情的心孤单地回归了天国,但愿在那里他可以找到真的爱情……
骆一禾
骆一禾,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他是海子短暂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而且是海子诗歌的坚定捍卫者。海子死后,他为海子的丧事四处奔波,为海子诗集的出版奔走呼吁,积劳成疾,在海子离去后的第49天(5月14日)因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大面积出血,经医院全力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于1989年5月31日下午1点31分,多脏器衰竭而死,年仅28岁。骆一禾的绝笔,是5月13日夜写成的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诗人大都死于脑疾,海子在遗书里说他的思维混乱,头疼耳鸣,间有吐血和烂肺的幻觉,骆一禾也同样为身体中最为活跃的大脑所负累。骆一禾生前发表过小说、散文、诗论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主要是诗歌,身后留下大约近二万行的诗作。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了向日葵与太阳的深沉联系,海子与骆一禾发现了麦子与生命的对应关系。人们称他们俩为“孪生麦地之子”。骆一禾早期的诗歌大多是温暖的,注重细节和场景,且以亮色为主,在语言上表现为平易,在内容上表现为青春。他对生命是热爱的,如同在海子离去后,他多次对人说:“我拒绝接受他的死亡。”他认为活着可以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来,但他终于无法拒绝自己的死亡。留恋这个世界而不能瞑目。
1985、1986两年,是他深入思考诗歌的两年。后来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诗歌创作,写下了分别长达3000行和5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诗《世界的血》。骆一禾的诗雄浑壮阔,尤其是《世界的血》的最后一章《屋宇》更是将他开阔的视野表露无遗。骆一禾和海子在当代诗歌中非常奇特地营造出幻觉般的浪漫主义的回流。他们的忧伤也许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却永久地归属于心灵。
有人说,海子想死,因此他死得圣洁,天国是他的归宿;而骆一禾拒绝死,因此死得遗憾,他多么希望从天国的风景里走回来,告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海子在那里很快乐……
与诗人无关
在北大我耳闻目睹了三次死亡,他们的离去和那些诗人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且已经被人们所淡忘,但生命总是相似的,差别在于后人的评价而已。
几年前,北大发生了一个博士杀死同宿舍的另一个博士并自杀的血案,有关报道提到最多的是学业的压力。但几乎所有报道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知情者所透露的信息:他30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而那个同宿舍的另一个博士,却是一个出自科大少年班的小伙子,不乏追求者。面对这样一种状况,他的心理怎会平衡?由嫉妒和失落所带来的恶的力量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在两个人不断有矛盾的时候,所有的对于自己的失望和对对方的由嫉妒而生发的愤恨搀和在一起,后果自然难以预料。这虽然是我对其心理的一种猜测,但我想应该有一定道理,一个生活中充满爱、充满温馨的人,是不会做出那样决绝的举动的,洋溢在爱情中的人对生活的态度也一定是五颜六色的,因为他爱这个世界,这世界上还有他所爱的人和事。
那天,我们在阳台上亲眼目睹身穿黑夹克的博士在阳台上呆呆地张望地上的人们和被高楼遮挡而无法极目的远方。几个小时能否将过往的历程全部追忆?他想起了谁?也许是为了减少这种思考带来的折磨和对于无法躲避的宣判的畏惧,他终于下定决心上路了……
周是我的大学同学,加入山鹰社之后刻苦训练,但她身材娇小,本来她不该参加攀登雪山的活动的,也许是组织者出于考虑这次攀登路线坡度缓、难度低,以及她为社团做出的贡献和正担任炊事员的职务,最终她还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却再也没有走出皑皑雪山……
勇是我的老乡,接触并不多,最近的一次是他还钱给我,而此后不久,便传来他被害于圆明园公园的消息。有猜测说他是酒后落入湖中,也有人说尸体被发现时是裸体的。后来没有听说警方如何结案,所以事情的真相对于我来讲只能是一个谜了。
死亡,是一个太过沉重的话题,而生者亦无法预想彼岸世界的有无。也许是为了安慰别人和自己,我们假定天国的真实,希望逝者终归可以到达那个充满人类最美好幻想的乌托邦,而天国风景的美丽却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们。
一场对于诗歌和凡人的缅怀沉重至忧伤累累。与诗人们对关乎生命与爱情之永恒命题苦思不解的绝望相比,考研的所谓苦痛卑微到了虚无。在诗歌忧伤的映照下,我正在和即将面临的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现实与理想主义相互碰撞的比较中,自己才会更清楚生命与奋斗的意义。
我与导师的亲密接触3月17日
第6节:与导师亲密接触
无论是出于侥幸心理还是的确需要辅导,对于跨专业考研的我来讲,除了独自摸索中文入门的路径之外,我需要从所要报考专业的老师那里获取更多资讯,关于如何学中文、如何备考等等。和很多考研人一样,我动用各种可能的人脉资源寻找老师。除了老老实实备考之外,我希望获得任何有可能的帮助,而这种诚惶诚恐的寻找和接触,会不会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从决定考研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动用所有人际关系试图联系到所报考专业的老师。我像乱投医的病者一样,只要有微弱的可能就去和老师见面。傍晚要去见一个老师,独自一个人。从此开始没有长辈陪伴的日子吗?应该是吧,不再是一个总要让别人搀扶的孩子,在学着自己走路的时候,蹒跚的样子是否有些笨拙和可笑?没有什么吧,即使摔倒了至少也还能让我知道,意料之外的和大地的亲密接触是痛的,让自己多一分小心吧,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告诫自己。
我小心翼翼地和老师联系,在每次通电话之前都要心跳加速的在电话亭前酝酿许久,设想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组织说话的内容。而在拨通对方的电话而无人接听时,竟然还会有某种释然: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紧张延缓一下了……
虽然并不习惯求助于人而低头走路,但为增加考研天平上的胜利砝码,我必须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去面对可能的嘲弄。当你生活在你极不想生活的状态里,而你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的时候,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是如此令人心碎而无奈。
对将来没有把握的悬浮感,让你做任何事情都弄不清到底有没有用处、有多少用处。这种不可能预知结果的事情,好像是一场红眼赌徒将未来做筹码的赌博游戏:可能满载而归,也可能血本无归。
经人介绍能够和老师见面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在北大几乎没有老师会因为特别关系而告诉你试题的。事实上,只有在考试前一两周的时间出题人才能确定,这一切又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利用和老师见面的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是必要的,所要争取到的是在能够进入复试的情况下先给老师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分。而考研初试成绩仍然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点上,相对于招生过程不透明的某些小院校而言,北大等名校的考研反而是容易的:你与他人的较量是在一个公正、公开的环境中进行的,胜负分明,并不会被人暗算却无从知晓缘由所在。
由此可见,考研期间和老师的接触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说有作用的话更多也只是心理安慰而已。这是目前我所认为的。
与导师见面的“谋略”3月20日
下午再次到中文系的一名老师那里,所希望的无非是自己在学习上的困惑能够解答。作为在考研路上迷惘前行的人,能够有机会得到所在专业老师的辅导是最好不过的了。
晚上回到图书馆,遇到同在考研的一个朋友,问起找老师的事情。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有朋友帮他介绍了老师在后天见面,他很早就开始手足无措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是一个考研北大的学生在复试的时候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许是多了几年的阅历,竟然也好为人师地传授起自己与老师见面的经验来。
北大的老师大多是勤恳做学问的,对于社会上所惯用的送礼请客一类绝对嗤之以鼻。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否则很容易惹得老师难堪,最终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如果是第一次上门,空手似乎也有不敬,带上一些水果之类也就可以了。礼轻不成敬意,也容易让人接受而不至于有收取贿赂的内疚之感。如果是家乡特产之类的东西就更好了,原则还是不能贵重。无论是第一次见面还是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原则都要把握好。毕竟老师不想因为这类事情而令自己内心不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打扰这份清净。
见面自然要谈学习和读书的事情,除了平时知识储备之外还要专门针对所拜访老师的研究领域做特别的了解,因为老师肯定是要就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你做探讨的。在交流气氛上,两种态度不可取,一是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一是沉默不语;前者会令人反感,后者不能让老师了解你的学术功底。认真倾听,并在需要表达观点的时候阐述自己的思想,不偏激、力求中正是适合的态度。
第一次见面,穿着是要得体的,不要过于成熟的装束,也不要像在宿舍中一样邋遢,穿着整洁是必要的。运动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记得一般情况下进门是要换拖鞋的,破袜子和臭脚就要注意了。总之,给老师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以后的造访和交流都会容易得多。
除了见面交谈之外,你的散文、随笔、论文等等都是可以体现你的学术功底的东西,通过电子邮件或打印出来放到老师信箱吧。老师们最看重的还是你是一个可教之材、可雕之木,其他的也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人说我不认识任何一个老师,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如果老师在开课,你不妨去听听,并在下课的时候直接找到老师说你要报考他的研究生。没有哪个老师会对愿意从师于己的学生不屑一顾的,这个时候你能要到老师的电话或E…mail就最好了,即使要不到你也能通过其他同学问到(那些没有开课、无法当面交流的老师的联系办法,也能通过其他同学获得)。接下来,将能够表现你的学术修养的文章发给他,这种见面之缘或邮件来往的零星印象,或许会在复试或其他方面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冰冷的知心爱人4月12日
回到宿舍,习惯性地打开电脑,似乎有很多话要写出来,更确切地说是“手谈”………这原本是围棋对局的别称,二人对弈,用手说话。这也是一个围棋程序的名字,“手谈”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计算机对弈软件,著作人为大陆陈志行教授。一项竞技性很强的脑力抗争游戏,被赋予一个平和淡泊的名字,更加融汇了一种高境界和生命真意。
手谈,与键盘交流,和自己对话。
我喜欢键盘啪啪声中一个个整齐的汉字出现在屏幕上的那种畅快感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了记录而记录,还是本来就有一种表达心情的冲动,总之,这种习惯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
1995年高一下学期,电脑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初关于电脑的印象,来源于《电脑爱好者》对一个名为《三侠五义》电脑游戏的介绍,我调动自己全部想象力都无法清晰感觉那个虚拟世界的样子。而拥有电脑的梦想就此扎根,先是1993年父亲单位买电脑之后我经常去玩,然后就是1995年将那台售价为13000元的奔腾75搬回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电脑游戏占据了我几乎全部业余时间,我不知道此后对于电脑游戏的没有感觉和高考的落榜是不是和这段疯狂玩游戏的经历有关。1997年来到北京上学之后,在北大计算机中心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弹指已是四年过去……
第7节:知心爱人
数日前因ghost系统的误操作,本来应该在恢复系统时选择partion覆盖却选择了disk覆盖,结果导致整个硬盘数据丧失殆尽。其中最为心痛的是丢失了记录我和女友的《青岛游记》………考研路上的不确定使得对于感情生活的依恋格外强烈起来。
电子文档存储于电脑中的不稳定性,使得其消失与毁灭几乎在瞬间完成,科技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若干年以后,我们是不是会怀念那种以笔绘心的手稿年代?
但我依然愿意用电脑记录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过去………这样一种方式,让我更容易写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因为意识的流动使我“言不尽意”,我需要不断地将所写,在屏幕上任意修改成我愿意使用的任何文字和语句方式,虽然笨拙的笔也许更能准确地表明我当时本真的状态………一种习惯一旦养成,要想变动便成为不容易的事。
在无数个考研的日日夜夜里,电脑将成为我倾诉内心世界的亲密爱人,虽冰冷却善于倾听,伴我度过无数个悲壮前行的日子。
北大18楼3054月21日
每到图书馆闭馆的音乐响起,我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