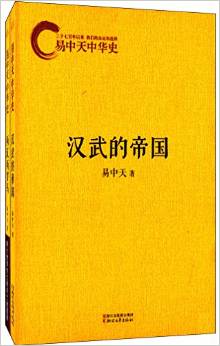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