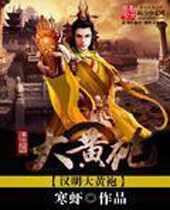汉明-第6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慢。”吴争皱眉道,“失去土地的雇工?为何失去?孤没有记忆……大将军府显然没有颁布过雇工需要收回土地的政令吧?”
莫执念惊愕。
一边张国维解释道:“王爷或许……不知,随着大将军府的开设和松江新城的建造,加上如今已经修建完成的铁路,二地的地价,已经翻了数倍,甚至十数倍……恐怕没有人可能抗拒这种诱惑。”
吴争明白了,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这,怪不了任何人。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
当一笔原本几辈子都无法得到的财富,放在面前时,谁能不动心?
吴争懂这个道理,在发布新税令时就,吴争选择的不是零和,而是将利益的馅饼做大,在不损害大户、商人的同时,提高贫民的利益。
譬如,以江南商会和银行前身钱庄的抱团,去争夺北方商人的份额和市场,用高额的关税去贴补财政司的岁入和商人的利益。
这个方法很有效,也是直接导致江南商人不再视吴争为“仇人”,反而视为利益趋同者的真正原因所在。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随着这张终有尽头的利益的馅饼到达可以扩张的极限,穷人和富人、商人和雇工、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等,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确实怪不了任何人,每一道政令,不管是“善政”还是“恶政”,终归是成就一伙人,剥夺另一伙人的,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成就人的数量多少罢了。
原本不肯卖地的农民,因江南工坊遍地兴起,眼馋于雇工的日薪,卖出了土地,学着开办工坊。
他们不是无产者,相反,他们拥有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卖地财富。
但,这些人的抵抗力是最差的,因为他们无所长,不,他们所长的只是种地,而不是经营。
那么,在开办工坊的顺风潮之下,他们确实可以生存,可到了逆境,首先死的,也是他们。
这,更怪不了大将军府和“始作俑者”吴争。
“让孤想想……再想想。”
第一千五百十三章 我儿威武
绍兴府,连接山阴、会稽二县的舍子桥桥畔。
时值正午,桥畔临河,有一家名叫“老郑记”的酒肆里,人头簇拥、宾客如云。
尤为显眼的是大厅里十数桌联席,更是热闹非凡,让本来就不是场地很大的酒肆更显拥挤。
显然,有人在办喜事。
人声吵杂之中,突然传出一个男声,“诸位乡亲父老、诸位亲朋好友……托祖先庇佑,小儿得携微薄之功安然还乡……今日黄某设宴答谢诸位亲友高邻,不醉无归啊!”
场内一片哄然,尤以男人的奉承声为最。
一个白发老者颤巍巍地起身,擎杯道:“抵抗外族、复我河山……此次国战,绍兴有无数好儿郎弃家舍业、前赴后继,虽血洒疆场,亦无怨无悔,幸甚!老朽与诸乡党深觉荣焉……来,为那些回不来的好儿郎们……敬一杯酒!”
这话一出,瞬间安静了。
众人收敛起脸上的笑意,无声地起身,举杯遥祝。
更有不少妇人们,突然就抽泣起来,渐渐地哭声大了起来,最后男人们也加入了,变成了一场嚎哭。
白发老者的手在摇晃,他满是沟壑的老脸上,一样挂着两行浊泪。
“哭什么?”老者大喝道,“历朝历代,热血男儿死于国战,应当应份,莫让人笑话……莫惊了儿郎们在天之英灵!”
哭声渐渐少了起来,老者扫视了一圈,大声道:“老朽已经与各族长商议了,此战中没了男丁的孤寡老幼,皆由同族族人一同抚养……。”
此江北一战,绍兴府不说原本已经从军的,仅新征青壮就高达一万三千余人。
战后统计,阵亡者高达四千多人,伤者近三千。
可以说,大将军府辖下十三府半之地,绍兴府担上了总伤亡人数的近四成。
战后班师之日,绍兴城内,一片白色,几乎家家挂孝。
可谓悲壮至极。
然而,悲恸之后,百姓们强忍心中之痛,为那些得胜回来的孩子们庆功。
今日,“老郑记”酒肆里,也确实是在办喜事。
庆贺黄家独子受封三级县子爵位。
这时,酒肆外,府河中,一条乌蓬船飞快而至。
从船上跃下一中年男子,始一进门,便拱手道:“谭某来迟了,妹夫莫怪。”
之前自称“黄某”的男子赶紧迎了出来,拱手道:“兄长能来,便已是不易……。”
这说着,泪水就涌了出来。
谭姓男子紧抿着嘴唇,忍着已经出现在眼中的水影,强笑道:“外甥论功受封之庆功宴……做舅舅的怎可不来?来……给我倒三碗酒,我自罚三杯。”
这一声之后,酒肆内泣声再起。
白发老者再也没有气力去阻止众人的哭泣,他拄着拐杖上前,用形如枯枝的手,按在谭姓男子拱着的双手上,颤抖着拍拍道:“谭老爷啊……谭家家风,当为世人楷模,若人人、家家皆如谭家,何愁鞑虏不灭、江山不复?”
谭姓男子眼中的泪终于落下,他涕泪横流地捧住老者的手,道:“黄老痛失爱孙,却依旧前来为谭某外甥贺,谭某……谭某……。”
话未出口,泪已满面。
都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一刻,全府同悲。
一个少年从里面冲了出来,他扑通跪在谭姓男子面前,大哭道:“甥儿无能,眼睁睁地看着表兄倒在眼前……请舅舅责罚、打骂!”
谭姓男子松开老者的手,转向少年,低头问道:“你表兄怎么死的……可有面向敌人?”
少年泣声道:“表兄英勇,凡战皆冲在甥儿前面,只是当时江都城外强敌数倍于我……表兄胸腹中了三箭,倒地前,还奋力向城下敌人扔出手中……。”
谭姓男子听完,仰头长吁了一口气,大喝一声,“我儿威武!”
闻者皆掩面悲叹。
谭姓男子将少年扶起,强笑道:“能从你口中得知你表兄的死状,舅舅就放心了……来,舅舅敬你一杯酒之后,还得赶回去,你舅母……哎,不说了这了……。”
少年惊讶地问道:“不对啊……表兄战死江都,按理大将军府该赏赐、抚恤才是,怎么舅舅会连表兄死状都不知道呢?”
谭姓男子强笑道:“为舅也不明白,所以一直担心你表兄是怎么死的……也罢,如今听你一说,我就放心了。”
少年急道:“这怎么行,该向大将军府申诉才是。”
谭姓男子微微迟疑了一下,道:“除了你,见你表兄殉国的还有人吗?”
少年愣了愣,好一会轻声道:“……当时甥儿那一连一百多人,没几个活下来……而后再转进仪真,就更没人了。”
谭姓男子愠怒道:“那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少年急道:“仪真城头,敌人数次攻上城墙,到最后,连陈都指挥使都率亲兵上城墙御敌了……要不是有个老兵为甥儿挡箭,甥儿怕是也回不来了……。”
说到这少年眼眶一红,痛哭出声道:“可我,竟连那老兵叫什么都不知道……。”
黄姓男子,也就是少年的父亲,厉声道:“受人滴水之恩,尚须涌泉相报,你受人活命之恩,岂可不问清楚?”
少年哽咽道:“孩儿问了当时在城墙上的史团长,可史团长对孩儿说,老兵替新兵挡箭,那是沥海卫的传统,如果我想报恩,那就在日后战场上,为新兵挡箭……!”
白发老者大呼道:“壮哉我江东儿郎!”
谭姓男子慢慢收敛起脸上怒意,和声对少年道:“是舅舅错怪你了……也罢,既然无人可证明你表兄如何死的,咱就不申诉了,咱自己知道就成……为国战死,不冤!”
说到这,谭姓男子接过黄姓男子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向在场众人罗圈一揖,“谭某今日失态了……来日再与众乡党告罪……先走一步,告辞。”
说完,谭姓男子转过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泪,径直朝外,向还在酒肆外等候的那条乌蓬船走去。
而这时,一个声音,从酒肆右侧方向的角落响起,“这位谭兄台,可否暂留一步?”
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1518。第一千五百十四章 适逢其会
吴争并非特意来绍兴的。
他确实是微报私访,但目的地并非是绍兴。
相较于治下十几府,绍兴、杭州二府是吴争的根据地,尤以绍兴府为最,政策的倾斜不言而喻,官民的拥护和合拍程度,自然也是非常高的。
对于民众是否接受农税彻底减免,私访对当然不能在绍兴、杭州二府进行,至少不该仅仅只是这二府进行调研。
吴争是路过。
人嘛,总是在以为已经操控了一切的时候,有一种如孩童般地窃喜,希望自己躲在暗处,去发现一些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正好到了吃饭的时候。
正好边上有一家酒肆。
正好酒肆中特别热闹。
许多的正好,让吴争进了“老郑记”。
温一斤老酒,切二斤牛肉,上一碟茴香豆。
吴争与鲁进财等人就围着一个八仙桌,默默地进着餐。
可剧情的演变,绝对不是吴争能预料到的。
刚开始,吴争是高兴,之后是欣赏,而后微恼。
但吴争无意去干涉府县,一个士兵的阵亡,也入不了吴争的眼睛。
大将军府及各卫在评功论过之时,并无过错,赏功罚过的根本在于,功必赏、过必罚,如此,方可令行禁止、军令如山。
虽然吴争觉得,按黄家娃儿述说的情况,谭家儿子该论功行赏,至少应该抚恤,因为此次吴争已经责令大将军府对此战中阵亡的抚恤、赏赐破例拔高一级。
譬如,黄家娃儿此时受封的是三级县子,那么,其实黄家娃儿原来的受爵应该低上一级,为一级县男。
谭家儿子死在江都,除了表兄弟的黄家娃儿,再无可证明之人,功如何赏?赏到何种程度?
如果赏了不该赏的人,如何面对二十万北伐军将士?
所以,吴争一直做为一个旁观者听着、看着,哪怕场面确实感人,但律法是律法,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去破例,这一点,与“慈不掌兵”是相同的。 feísuΖwcо
可到了最后,吴争意识到有些不对了。
谭姓男子在听完外甥述说,知道自己儿子是殉国,而不是临阵溃逃死于意外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申诉而是息事宁人,这就有些怪异了。特别是他外甥还提醒他向大将军府申诉的情况下。
要知道,他外甥如今已经是三级县子,按律是可以越过府县,直接向大将军府申诉的,这是他的特权。
当然,吴争知道,如果找不出第二个证明人,这申诉很可能泥入大海,拖个三、五年不了了之。
但做为一个父亲,得知儿子为国战死,且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和抚恤,不该如此淡定。
事有反常必为妖,于是吴争出声阻止了,因为吴争想到了此事带来的另一个后果。
……。
“这位大叔,可否暂留一步?”
这一声,让吴争一桌四人,成了屋内的焦点。
谭姓中年男子转过头看了吴争一眼,原本他无意与陌生人纠缠,正如他说的,家中妻子因长子的死悲恸欲绝,需要赶回去。
可久居上位者身上,总有一股子慑人心魄的气势,虽然无形,但事实存在。
特别是象吴争这样一个从战场上滚过来的上位者,说句夸张的话,连目光都可以杀人。
谭姓男子无意识地回身,拱手道:“敢问这位郎倌是在与谭话说话吗?”
吴争拱手回礼道:“正是……敢问大叔怎么称呼?”
“鄙人姓谭,名奇。”
“谭大叔有礼。”吴争微微一揖。
谭奇揖身回礼。
“方才听谭大叔说到不想申诉……敢问,为何?”
谭奇眉头微微一皱,停了停道:“这是谭某私事、家事,不劳郎倌动问……谭某犬子新丧,你若无它事,谭某告辞了。”
吴争平静但执拗地道:“观谭大叔言行,该是读书人?”
一边黄家娃儿上前一步,代答道:“我舅舅是崇祯九年举人……。”
“失敬,失敬。”吴争淡淡道,“不过按理说,既是举人,谭叔为何不想申诉呢……?”
谭奇有些烦了,他冷冷道:“郎倌休管他人私事。”
边上黄家娃儿也道:“敢问兄台是何人?”
二人语气已经不善,要不是吴争身上有这股无形的气势,和身后鲁进财三人牛高马大的,怕立马就会被驱逐出酒肆了。
也对,谭奇好歹是举人,哪怕无官职在身,那也是有功名的人,只要这方土地还是明地,那么,他的功名就无法被剥夺。
而黄家娃儿刚受封三级县子,见官大一级,就算知府当面,那也得给三分面子。
吴争神色依旧平静,他没去理会黄家娃儿,看着谭奇问道:“谭大叔别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是好意……既然令郎为国捐躯而没有得到应有赏赐、抚恤,就该申诉。”
谭奇皱眉不耐道:“谭某说了,这是我家家事……!”
“不!”吴争一口打断道,“这虽是你家家事,但更是公事、国事!”
不得不说,能象吴争这般说话的,确实给人的感觉,非同常人。
谭奇神情也变得慢慢严肃起来,“敢问……此话何意?”
“大叔以一己之私,使得军令名存实亡,岂是家事?”吴争严肃地说道,“令郎是功是过,自有军法评判,若人人都象大叔一样,以家事度之,则功必赏、过必罚的军法就形同虚设……试问功不得赏,过无须罚,那战端再开之时,还有多少人甘愿与敌血战、效命沙场?”
这话听起来有些荒谬,可却是事实。
士兵处于劣势,无法与上官争,那么,所受的委屈慢慢积累,最终使得军令无法畅通,毁掉的就是一支军队、一个国家。
谭奇可以因自身原因,不向官府申诉儿子的赏赐和抚恤,但这事如果传了出去,坊间就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