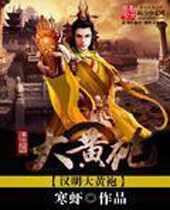汉明-第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地三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帝做了让步,下旨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免税达三百多万石。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省份,从此之后,每年朝廷岁入的最高额,就一直保持在二千七百万石上下。”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说,从洪武帝确立了赋税总额之后,朝廷对此后的赋税只有减少没有增加?”
“正是此理,对于耕地,地方官员在给朝廷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呈报额,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赋税与实际耕地数脱离。自古以来,赋税定额前所未有,不管唐、宋哪朝,也从来没有象我朝这样僵硬、死板地执行这一赋税政策。”
“说到人口,各地新增长的丁口需要成长的时间,很难直接有助于赋税的增加,而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更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这些人口进行登记和评定,当地官府也不愿意如实上报,因为担心上报的人口增加数,会促使朝廷重新调整当地每年的赋税定额,从此增加当地需征赋税额度。他们最多是重新调整人均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这样就使得税收容易征集,同时当地衙门官员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并对日后他们的考评起到好的作用。”
吴争大概已经听懂了,虽然对莫执念说赋税失控致使大明灭亡的说法半信半疑,但对于莫执念的博学强记,有了新的认识。
看来,这个所谓的杭州富商,应该不只是富商那么简单吧?
第一百九十四章 真他X的有些道理
“自此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商贸繁荣几何?我朝的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二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就使得近二万万人的所征赋税,几乎与一万万人持平的结果。老朽与伯爷讲几个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钱钞三万九千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此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时任御史黎贯言,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至万历年间,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绢二十万六千余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
伯爷想必已经明白,越往后,人口、土地越多,赋税却反而少了。从永乐朝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年间,和洪武年间相比,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表面上看,减少得并不多,可如果结合人口、田地增长来看,人口多了赋税却少了,这就相当可怕了。”
吴争问道:“那难道朝堂重臣们,就不想办法解决此弊端吗?”
这话问得在理,虽说贪官污吏每朝皆有,不也从不乏清官、诤臣。
没有道理百年之间,就没有人去点明这件事,去纠正它。
莫执念苦笑起来,“伯爷真是血气方刚,可任何朝代,一旦过了鼎盛时,都会形成陈规旧律,这些陈规旧律往往会成为一些人保守利益的工具,谁要去改变,那就得与祖宗作对。不用说臣子了,恐怕先帝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伯爷说得没错,百年之中自然有象伯爷一样血气方刚的诤臣进谏,但往往都没落个好下场。阻力来自两处,首先是文官对皇帝的掣肘,其次是当地官府的地方保护心思。伯爷恐怕不知,当年崇祯帝为抗金加派三饷,满朝文官同气连枝,向皇帝上疏,言道,增收赋税将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凡是向崇祯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向皇帝建言增收三饷的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
当时皇帝加派三饷是顶住文臣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而最后还是没有顶住,所以才有周延儒上任,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的指示向皇帝建议,首请释漕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皇帝终究是允准了。这就令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依老朽看来,之后大明在不足二年时间灭亡,与崇祯帝听从这些建议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至于说到当地官府的地方保护心思,这就不难理解了。之前老朽说起过江浙各地拖欠朝廷赋税之事,被朝廷豁免了三百万石。这里老朽再与伯爷说个例子,先帝刚登基时,尽管有人提议增加赋税定额,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据三百四十县呈报,税收拖欠达到了五成,甚至更多。这三百四十个县占到了大明掌控财政税区的三成。而其中的一百三十四县事实上当年没有向朝廷上交过任何税收。从这两种阻挠上而言,就算皇帝想励精图治,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莫执念叹息起来。
吴争听得心情非常沉闷,觉得嘴唇干渴,取茶碗一饮而尽。
一杯好好的明前茶,生生被吴争当成了路边茶摊的碗茶,有些牛嚼牡丹的意思。
莫执念忙让人为吴争更换茶水。
吴争问道:“可百姓生活贫苦,因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生计之言,不绝于耳,难道这也是假的?”
莫执念惊讶地看着吴争,许久才反问道:“伯爷杭州城中可有见过真正贫苦的百姓?或许真的有,可那所占不过百一。况且,历朝历代,贫苦百姓何曾少过,为何就到了我朝,贫苦百姓倒成了灭亡之因了呢?”
吴争确实有种被莫执念洗脑的感觉。
他的这一番话,几乎是颠覆了吴争对这个历史的认知。
大明灭亡的原因竟不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些,而是一个字——钱!
他x的,这是钱能解决的事吗?
这让吴争想起了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但吴争确实有些信了,什么政治昏庸、贪官污吏、官商勾结、赋税沉重,这些哪朝哪代没有?
不管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后世共和,这些情况都有伴随。
虽然都是弊端,但真要追究至灭亡的根源,似乎都欠缺些说服力。
从吴争这一年时间的切身体会,明军的溃败,不是清军战力强大,明军战力不足的原因,而是由上到下一致地不抵抗、消极抵抗所致。
就象当初陈胜一百人被几十鞑子追得一路溃逃一样,不是打不过,而是不想打,不愿意打。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上官闻风而逃。
那上官为何逃跑,无非是贪生怕死、心中没有战胜希望,连潞王都献城投降了,他们算个屁啊?
如果这只是个例,每朝每代都有,可如果大部分将领都这样,不败那才叫见鬼呢。
所以,当吴争将切身的体会与莫执念的说法相互印证起来,才发觉莫执念说的,还真他x的有些道理。
想到这,吴争的眼神反而微缩起来。
第一百九十五章 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你今日与我讲这些,究竟何意?”
莫执念沉吟了一会,答道:“伯爷麾下已有大军七万之众。若杭州、嘉兴两府在以前或许还堪堪负担,但此时二府刚刚光复,尤其是嘉兴府,想要筹措七万人的军饷、粮草,非常困难。老朽忝为伯爷麾下参议,理当为伯爷分忧。”
这话说得没错,照理两府辖下合计四、五百万人口,养活一支七万多的军队确实不难,但现在就呵呵了,当然吴争还是可以去嘉兴府故伎重施一回的,象杭州城那样再捞一把。
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就算再整个百把万银两,对于一支大军而言,那也就一年半载的粮饷,救急可以,长持以往却是下下策。
“说了这么多,想必你已经有了办法?”
“是,老朽确实想到了一个办法,只是……伯爷未必能肯。”
“说来听听。”
“这……伯爷可曾听闻过洪武朝沈富其人?”
吴争想了想道:“不曾。”
莫执念古怪地道:“江南籍人,鲜有不闻听此人的。”
吴争皱眉道:“这人有何本事,非要使人耳熟能详吗?”
莫执念答道:“此人没别的本事,只有一桩本事,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传奇。”
“什么本事?”
“赚钱的本事。”
“呃……他有很多钱吗?”
莫执念的眼睛眯了起来,仰首喟叹道:“他究竟有多少钱,老朽也不知道,世人传说,他至少有二千万两以上的家产。可老朽知道,远远不止此数。伯爷既然不知道此人,那总该知道南京城有一部分便是得他捐助修筑?”
吴争听闻前几句时,已经心中一动,到最后一句,吴争已经悚然,“你说得可是沈万三?”
莫执念悠悠一叹道:“果然,伯爷也是听闻过此人的?”
吴争急问道:“沈万三不是被太祖流放滇南了吗?怎么莫老可是知道他的后人在哪?”
莫执念摇摇头道:“老朽不知。”
吴争大所失望,这老头耍人玩呢?
说话尽吊人胃口。
“那你为何说起他?”
“老朽想要告诉伯爷的是,天下赋税,除了农税,还有商税。”
吴争闻言点头道:“没错,商税应该是朝廷岁入大头才是。”
这话基本上后世人都知道,后世农税几乎尽被减免了,国家的税收大都来自于商税。
可在莫执念听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伯爷果然是天纵之才!”
这下吴争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莫老谬赞、谬赞了。”
“伯爷过谦了,虽说天下能知晓此事的不少,可真正如伯爷这般言之凿凿的,怕是不多见了。”
“哦?这是何意?”
“伯爷可知,崇祯十六年,朝廷岁入中,商税多少?”
吴争哪知道,摇了摇头。
莫执念叹道:“盐税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酒税尚不足万两。”
吴争大惊,这不是开玩笑吗,偌大的明朝,商税加起来竟不足三百万两?
“你……信口开河吧?”吴争疑惑地问道,“这点点银两,恐怕杭州一府也不止于如此吧?”
按吴争的记忆而言,杭州在后世仅一地的税收,那也以数十亿计的。
折合成银子,怎么也在千万两以上吧?
可大明朝全国的商税岁入,才不到三百万?
这确实刷新了吴争的认知。
也让他怀疑起莫执念是真知道,还是唬弄自己。
莫执念微叹道:“莫说伯爷不信,这天下人恐怕也不信。可事实就是如此,伯爷可以去绍兴府问问曾经在崇祯朝任职的朝臣,便能印证老朽所言非虚。”
吴争半信半疑道:“那按你的说法,大明的商税岂非形同虚无?可这天下传言赋税沉重之说,从何而来?”
莫执念苦笑道:“看来伯爷是真不知道,从太祖洪武朝起,就明文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老朽举例与伯爷听,便可知道其因。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记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吴争听了张大了嘴巴,这种事,他还真没有听说过。
公民纳税,不是光荣的义务吗?
莫执念继续道:“永乐年间,又进一步降税,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呈报皇帝,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我朝对商人的保护和宽仁,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等等,但凡想得到的,皆在免税之列。就算有征收的,如盐、茶、酒等,也是三十取一,超过者按违法论处。”
吴争已经被莫执念的话说傻了,关于明朝灭亡,自己听闻的不是应该是阉人干政、宦官专权党争倾轧、政治腐朽、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等等吗?
甚至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在后世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还有什么小冰河期造成的粮食减产,还有大规模的瘟疫等等。
在吴争的观念中,明亡一直是寿终正寝才是。
可现在,吴争疑惑了,照这么看来,自己显然是意识错误了。
“莫老丈,这么说来,大明治下是非常宽仁的了?”
莫执念反问道:“伯爷也是朝中重臣,你以为呢?”
第一百九十六章 莫执念主动投效
吴争愣了,至少从自己的记忆和切身体会中,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初自己一个从七品哨官,在张国维家中,当着三人的面,就数次妄言了“大逆不道”的话,也没见被治罪。
而朝堂之上,象张煌言一个区区七品御史,也敢屡次指着朱以海的鼻子顶撞,也没见他被治罪,这时的政治不可谓不宽和,至少没有听说以言获罪。
从始宁镇百姓的生活,和吴庄的过往,确实也没有听闻谁家被赋税逼迫得活不下去。
难道,这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