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山般的巨浪重重击打着海岸,狂风过处,大树被连根拔起。
狂风也吹打着清海镇的镇营,张保皋不听谋士于吕系的劝阻,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坐在军营所在地将岛,倾听狂风暴雨的声音。对于生于海边,自小便与海为伴的张保皋来说,狂风肆虐、大浪滔天反而是他喜欢的境界。
清海镇营在猛烈的台风中仍坚如盘石。奉兴德大王之命,在清海设镇已有八年。八年岁月,不过弹指一挥间,清海镇却已发展成连接唐朝与新罗以及日本的三角海路的航运中心。它不仅是三国间的物流要冲,也是一座关隘,任何船只,不经过清海镇,便不能去唐朝;任何商船,不经过清海镇,便到不了日本。
“清海镇呀,”于吕系朝独自坐在帐篷里的张保皋笑着说,“真可谓鼓腹击壤。”
鼓腹击壤。
意思是拍着肚子,跺着脚,很兴奋的样子,用来形容太平盛世。上古时的圣天子尧帝到民间体察民情,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拍着肚子,敲着大地,高兴地唱着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
这支歌后来被称为《击壤歌》。当时的清海镇真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武陵桃源。
当时的新罗朝廷昏庸无能,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致使政治紊乱,百姓涂炭,只有清海镇还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地方。
自张保皋麾下一万人的强大军队抓捕了阎文以后,海盗也好,奴隶贩子也罢,在海上再无容身之处,大海彻底地恢复了往日的和平。张保皋的船队带动起来的商业蓬勃发展,当地经济空前繁荣。
著名的学者、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莱莎渥(1920~1991)在他所写的《从唐朝开始的圆仁旅行记》论文中评价张保皋为建立商业帝国的“贸易王”,那时张保皋的清海镇是商业帝国的大本营,他本人则是建立这一伟大帝国的海上王。
如果说兴德大王只是管理新罗国政的君主,那么张保皋则是统治着连接唐朝、新罗、日本的海上帝国的帝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保皋是韩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际人,是超越国家和民族,视全人类为一体的世界主义者。
“您去哪里?大使大人。”
本来坐在空帐篷里的张保皋突然起身向外走去,于吕系赶快阻拦。
“不能出去。外面风疾雨大,很危险。”
但张保皋不听,他走出狂风骇浪包围中的帐篷,独自伫立于台风中。
帐篷外面便像于吕系担心的那样,风雨交加。
据记录,清海镇一带年平均降水量达1700毫米,雨季为处于东南季风影响下的六月至九月间。东南季风每年从太平洋西南部带来吹向东北亚大陆的台风,而完岛即清海镇正好位于台风正面侵袭的海岸边上。对生于海边长于海边的张保皋来说,暴风雨非但不可怕,而且还是亲切的令人欢喜的朋友。
惊涛骇浪似乎要吞噬掉将岛,汹涌咆啸而来,激起的水花漫天飞溅;狂风似乎要卷走张保皋,呼啸着横扫而去。狂风暴雨中,张保皋虎目圆睁,注视着卷起白色泡沫的波涛。
哗,哗,哗。
听着气势凶猛地冲向岛边岩石的海浪的咆啸声,张保皋霎时感到了全身被海水浸透般的喜悦。
今年他四十八岁了。四十岁时被兴德大王封为清海镇大使,回故乡不过八年,他便建设了梦想中的海上帝国。按莱莎渥的表述,张保皋建设了伟大的商业帝国,成了贸易帝王。
从历史的记录中查不到张保皋的出生年代,但是从前后情况综合来看,张保皋大约生于公元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在完岛一带长到二十多岁。
助音岛。
现在张保皋将军营所在地叫将岛,但他小时候这个岛叫助音岛,是他从儿时到青年时玩耍的地方,也是养育了他的地方。
张保皋独自伫立在猛烈的暴风雨中,睁大眼睛凝视着惊涛骇浪,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我去唐朝大约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于是,到唐朝去的一幕一幕往事开始在张保皋的脑海里一一掠过。
入唐后的十余年间,张保皋历尽千辛万苦,加入唐朝的军队立下不朽战功,当上军中小将。
据历史记载,张保皋参加了讨伐高句丽遗民李正己建立的平庐淄青藩镇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表现突出,任武宁军军中小将,当时他正值三十而立之年。从当初怀着出世之梦,到在中国立身扬名,仅仅用了十余年。那之后,又经过波波折折,张保皋结束了军旅生涯,但仍留在唐朝,结交并组织滞留唐朝的新罗人,从方方面面为日后从商打下了基础。做这些准备,张保皋大约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由此算来,张保皋在唐朝滞留了漫长的近二十年时间,在那悠悠岁月里他多么思念故乡。
张保皋出神地盯着澎湃而来似乎要吞掉自己的波浪,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二十年时光里他没有一天忘记故乡。
草根树皮。
张保皋离开故乡前往唐朝时,正是新罗百姓缺吃少穿,以草根树皮裹腹的年代。
依《三国史记》的描述,中国当时是梦中的理想大陆。
那时,年轻一代在新罗这种彻头彻尾的等级社会里觉得束缚和限制,很愿意漂洋过海到更开放和富强的唐朝去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
张保皋便是当时满怀希望到唐朝去的那批年轻人中的一员。
他能选择的惟一的出路便是加入雇佣军。
当时高句丽遗民李正己建立起来的藩镇统治着地方,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李正己的藩镇名称叫“平庐淄青”,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地方足足有55年了。
张保皋到中国时,藩镇已由李正己的后人李师道世袭了藩首。李师道派刺客到长安,暗杀了宰相武元衡,朝廷视之为心腹之患。
唐朝皇帝宪宗在此事上摒弃了议和观点,宣布派兵讨伐平庐淄青。那时是公元815年12月。
唐朝与平庐淄青军间的交战持续了三年,直到公元818年7月才结束。当时武宁军是唐军骑兵的先锋部队。
因此,武宁军中需要武艺超群的士兵,只要武艺超群,不管是异邦人,还是囚犯,甚至是海盗,都可以当武宁军的士兵。
于是,身手了得的张保皋随即成了唐朝军队的雇佣军。
轰隆隆。
暴风雨中电闪雷鸣,不知道是不是雷劈到了附近海岸,霎时间地动山摇,火光窜起。
在雷声大作中,似乎一种熟悉的喊声像霹雳一样在张保皋耳边回荡。
“大哥。”
张保皋立时环视了一下周围,明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谁呀?”
张保皋向周围寻找着,但是四周漆黑一片,只有猛烈的暴风雨。
“到底是谁呀?”张保皋喊起来。
张保皋马上醒悟到那不是人的嗓音,而是天上的雷雨声。可是对张保皋来说那明明是熟悉的声音,是了,那是郑年的声音。
郑年是张保皋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他俩都出生在完岛。
据唐朝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记载:郑年比张保皋小十岁,称张保皋为大哥。实际上郑年并不比张保皋小十岁,但的确比张保皋小,称张保皋为大哥倒是事实。
两人从小便一同在助音岛上生活,后来盟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结义金兰。
不久,两人胸怀壮志,于同一天一道起程前往唐朝。对两人的关系,诗人杜牧在《樊川文集》第六卷中有如下记载:
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郑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保皋以齿,年以艺,常不相下。
张保皋和郑年成长于同一故乡,又一同前往中国,他们无疑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张保皋比郑年年长,郑年管张保皋叫大哥的说法符合事实。
张保皋和郑年这对结义兄弟平生共同经历过波澜万丈的生活。有张保皋的地方常常有郑年,有郑年的地方也常常有张保皋,两人常如影随形,简直不是结义兄弟,而是一心同体的一个人。
张保皋获得了如此成功,像莱沙渥所形容的是“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帝王”,这些成功多亏弟弟郑年的帮助。而郑年小小年纪便当上武宁军军中小将,扬名于世,也多亏哥哥张保皋的帮助。果然之后两年,张保皋毫不犹豫地对义弟郑年委以大任。
轰隆隆。
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雷声紧接着破空而来。短暂的闪电光中,过去八年间张保皋一手建立的清海镇的风貌一闪即逝。
“啊,”张保皋雨中叹息道:“如果现在郑年在我身边,是啊,只要郑年在我身边,郑年便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然而,郑年人在哪儿呢?
狂风中如马鬃般立起来的波涛击打在岩石上,张保皋迎着迸溅过来的海水沉思着。
郑年弟弟现在在哪儿?做什么呢?
“大哥,大哥走大哥的路,我走我的路。”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最后一次见到郑年已经是十年多前的事了。那时张保皋辞去军中小将之职,退役当起了老百姓。他开始团结在唐朝的新罗人,满腔热血地筹划经商。两人分别之时,郑年说:“自古经商便是卑微的贱民所从事的,我不喜欢经商。我虽然生于海边,但希望能死在马背上,而且,虽生于海边,比起撒网捕鱼,我更喜欢背着刀枪去打仗。所以,大哥走大哥的路,我走我的路。”
郑年选择的路是继续做一名军人。但是唐朝已经完全消灭了平庐淄青的藩军,不再需要官军了。相反,过分臃肿的军队已经带来了新的问题。
“古话说得好。”那是张保皋最后一次劝郑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鱼捕筒弃。你我不过是唐朝雇来讨伐藩军的猎犬、弓箭、竹筒。如今兔已死,鸟已尽,鱼已捕,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没有战争的时候应该熔化刀枪,铸犁耕地播种。”
但是郑年却瞪着眼睛说:“古语还这样说,武臣不惜死。做军人不会像大哥说的那样熔化刀枪去铸犁,即使是饿死,也要磨好刀,擦亮枪,时时刻刻做好争战的准备。这不正是军人应走的路吗?”
那时,张保皋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叫法华院的寺院。这是一座新罗式的寺庙,离开军旅的张保皋以此来团结生活在唐朝的新罗人,使他们有一个凝聚之地。
按圆仁的记载,在由张保皋发起建造的寺庙赤山法华院中,每年冬夏举行两次讲经会。讲经使用的是新罗语言,并以新罗方式进行。
张保皋与郑年最后一次见面便是在一次主要由新罗人参加的讲经会上。那是825年,张保皋归国前三年的事情。
当时赤山法华院正在举行夏季讲经会,夏季讲经会主要讲解《金光明经》,那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新罗高僧。
被邀的法主法号朗慧,他于三年前,即宪德十四年(公元822年)借派往中国的使臣金昕之力到了唐朝。
朗慧和尚虽然年轻,却是新罗最具水平的高僧。有关他的传闻,张保皋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张保皋亲自到法华院来参加讲经会,礼拜十方佛,忏悔罪过,倾听朗慧和尚的讲解。
此时,朗慧已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三年,开始受具足戒,跟着高僧大德修行。
朗慧之所以会先到至相寺,是因为他曾在义相大师创建的浮石寺学习过,而义相大师是智严的俗家弟子。由此说来,浮石寺的佛家思想与智严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然而即便是在至相寺,他听到黑脸老人所说的马祖的“心即是佛”,猛然醒悟,随即去找禅宗思想的大师,马祖的弟子如满。
马祖禅师。即马祖道一,是中国禅宗思想集大成者。
据说马祖学禅时,禅师怀让为了能使整日坐禅一心希望早日成佛的马祖醒悟,便从马祖身旁拿起一片瓦片,对着石块研磨起来。马祖看了不解,问禅师:“您磨瓦片干什么?”
怀让答:“做一面镜子。”
“磨一磨,瓦片便能成镜子吗?”
听了这话,禅师不紧不慢地反问道:“磨瓦既不能成镜子,那坐禅又岂得成佛呢?譬如牛拉车前行,车子若不肯前进,是打车好呢,还是打牛好?”
听了禅师的话,马祖顿悟到“心即是佛”,之后马祖倾毕生之力宣传“平常心即是佛”。当时马祖弟子之一如满便住在长安。
在如满那里,朗慧开始将眼光由教宗转向禅宗。
那么,朗慧到张保皋所建的新罗寺庙法华院讲经大约便是在宝彻圆寂,他云游四方,普施善行的时候。
因为他自师父离世之后便开始头戴黑巾,被信徒们称为黑巾僧人。
赤山法华院原来像圆仁写的那样“夏季讲解《金光明经》”,但朗慧在主持赤山法华院期间,却从未讲过一句《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是赞叹佛寿命无量的偈颂,自古被尊崇为守护国家的经典。张保皋等数十名新罗人邀请他去讲经,在对教理经文进行问答讨论时,无论他再三发问,其他人竟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因此朗慧只好带领信徒拔草,或补修被洪水冲毁的桥梁,以众人合力,其力断金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讲解。
每逢赤山法华院有重要法会时,都会请和尚讲经,并作忏悔礼佛。每次朗慧都想去听,只是他认为,身体力行修补坏桥远比为忏悔罪过礼拜十方佛更重要。他总是亲自搬运沉重的石块,只对信徒们淡淡说道:“身为仆役,心为君王。”
朗慧每日只吃一餐,身体瘦削干瘪,眼睛却炯炯有神。他虽然比张保皋小十多岁,但全身气韵神圣,凛然不可侵犯。
正是在那期间,郑年来法华院见到张保皋,那时他们已经分别三四年了。当时张保皋正热衷于经商。
虽然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张保皋已成为拥有庞大的新罗船队的大商人,而郑年仍身在军营。
张保皋力劝郑年一同经商,但郑年总认为经商是贱民所行之事,自己更适合从武,并没有听从张保皋的劝告。
轰隆隆。又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雷声大作。
张保皋从怀里掏出一件小东西,借着闪电的光,他呆呆地看着。
那是一尊小佛像。
一尊坐姿的禅定印的新罗佛像。这是朗慧和尚送给他的礼物,一个极其特殊的佛像,因为它的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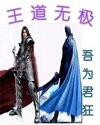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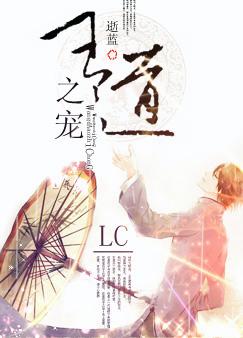
只有你能听见的声音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