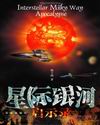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南非其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十多年,但是我的这组文章仍是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天则所的那次讨论中,我国著名的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就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在此前十多年关注曼德拉时就读过她的著作,受到不少教益。我知道她对曼德拉及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很崇敬,对种族隔离制度很痛恨,对新南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高度的评价。她觉得新南非的十几年经济发展成就很大,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之处,认为我应该多介绍新南非。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如此?作为一个并非专业研究南非出身的学人,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反思后看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南非可以大增我们推进转型的信心,当然也是我的希望。我在曼德拉传的末章对新南非初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写新南非,也是期待一个符合这一愿景的繁荣景气。
十多年来新南非确实在很多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应该承认,我期待的繁荣愿景至今尚未出现。相反,新南非的繁荣之路比人们预想的要坎坷,1997年我为曼德拉传写的末章“前路迢迢”,倒成了这19年的写照。《从南非看中国》这一组文章发表后这几年我一直听到两种反映:一是习惯歌功颂德的朋友对我搬来旧南非这面镜子不高兴,认为“不可比”;二是觉得可比的朋友就会接着问:那么改了又会怎么样呢?你为什么不讲讲后来这十几年?
当然,对这十多年我也可以只讲成绩斐然的一面而对作为“代价”的坎坷一笔带过。不过我们必须面对民间,十多年前南非与东欧其实属于当时全球同一波民主化,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消息却形成有趣的对比:正如我书中提到的,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官方“主旋律”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但民间对“新欧洲”的观察却正面得多。而同一时期我国官方对南非不多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但中国南非建交后这些年急剧增加的旅南非同胞却经常传回来一些负面的民间观察,诸如治安恶劣、城市衰败等。
经过思考我还是觉得应该遵循那句老话: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而且作为严肃的学者,我越是倾向于民主化,越应该侧重于“问题要讲透”。所以就有了讲新南非的《“彩虹”的启示》这一组文章。它是从2008年“排外骚乱”这一负面事件开始分析的。
我从负面开始分析,并不是由于我对民主化的方向有什么怀疑,相反,我对曼德拉在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上“圣雄”式的贡献深怀敬意,对南非民主化实践所蕴含的启示意义也是高度评价的,我认为这些意义不亚于东欧、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等人们谈论很多的民主化案例。而且我对新南非长远的预期实际上也相当乐观。
但是我一直认为,为民主辩护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要在比那些指责民主制度的人对民主化过程案例中的负面现象看得更透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回避这些负面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的。有个宋鲁郑先生仅以新南非供电不能保证为由,就得出了“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的结论,如果他看了我这本书对约翰内斯堡旧中央商务区变成“鬼城”的叙述又该说什么?
其实在新南非的种种“负面”中,供电不足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了:旧南非的确人均用电水平相当高,而且电费低廉,供电充裕,有段时间还有余电出口。但是那时主要是白人用电和工业用电多,黑人地区却有很多是不通电的。新南非发电量增加了,但黑人用电的增加却快得多,于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供电紧张,这当然也不好,但是这就可以狂言“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如果他看了本书下面这段话又该如何?“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供电不足就可以不要民主,这样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就连奴隶制都可以容忍了?希特勒德国在其点燃的战火返烧自己之前上述问题倒是一概没有,是不是也很令人羡慕呢?
我直面上述问题当然不是为了给宋先生这样的人提供反民主的炮弹。其实这样的炮弹也不难找,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中国兵荒马乱,很长时期比清末“新政”时的秩序更糟,但是忧患中的国人只能向前求索,有几个人希望清廷复辟、重返帝制?世界上很多前殖民地独立后发展都上不去,今不如昔之处甚多,但又有几个人希望重返殖民时代?人类有些追求是不可抗拒的,有之并非万能,无之万万不能,问题需要解决,倒退绝非出路。民主化就是这样。而且平心而论,世纪之交的这轮民主化的“负面”(所谓转型危机或过渡期阵痛)比起过去法国大革命,比起清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专制瓦解后的混乱要小得多了。人们常提的东欧(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和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除外)、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等都比较顺利地迈过了这个坎,而相比之下南非这个坎算是迈得比较艰难的。但是由于南非的民主化是冲着白人统治者来的,相比冲着别的一些人,在我们这里似乎就更无争议些。分析南非的转型危机在我看来因而就更有意义。这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转型本身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而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远大于转型危机的负面。即便南非那样比较严重的转型危机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严重的“约翰内斯堡变成索韦托加桑顿”而言,我们旅南非同胞时常提到的“约堡沉沦”也不应当遮蔽索韦托的前进和桑顿的繁荣。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降低他们对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像宋先生那样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这些“负面”更凸显了人们为追求光明而义无反顾克难前行的志向。
第二,对这些“负面”形成机制的分析也表明它们,至少是它们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宁说是旧制度的后遗症。南非的过渡期危机其实在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甚至约堡主城区的失序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滥觞。它们证明旧制度的“增长奇迹”已明日黄花,旧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续。尽管新南非没能很快结束这些后遗症,甚至很多过去种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从而以转型危机的形式变成了新南非的“负面”,但是也正需要人们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些现象,才能把这些形成机制剖析清楚。
第三,也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负面”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足取,但是相反的逻辑: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就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种逻辑肯定也是不对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逻辑恰恰是导致很多转型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后人不应被“负面”吓唬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避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民主化应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比前人做得更好。这也要求我们对负面不回避,而是要正视。南非转型期的“负面”有的如前所述,本是旧体制的后遗症,但在民主化中如何克服这些后遗症仍值得研究,还有一些负面属于南非特有因素的产物,不具普遍意义,厘清这些也可以避免用它们吓唬人。另外有的是个案性的决策失误,可以单独引以为戒而不必把它与转型绑在一起。最后,有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民主化过程逻辑上会伴生的,那么后人也要尽可能改善应对,减轻其影响。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下这组介绍新南非转型的文章。我相信,“问题讲透”之后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新南非。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愿望,限于我的浅陋学识,“问题”找的准不准,讲的透不透,实际上很难说,还期待方家的教正。我的这些文字,尤其是“从南非看中国”那些分析性的论文在单行发表时就引起了不少商榷和批评,我希望结集后也能继续引起讨论。
最后还是要感谢有关的朋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黄孝阳先生;还有我的妻子金雁和女儿秦蓓蓓,她们不但在家务上呵护我,也是我讨论问题的伙伴。更应该感谢那些直接对本书有贡献的朋友,特别是“编译”的那部分本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前面提到姓名的那些当时的青年朋友(现在都已是中年)应该与我一起分享,但是事过15年他们都已与我失去联系,如果他们看到本书后能与我恢复联系,那就太好了。
秦 晖
2013年夏于蓝旗营
?
————————————————————
'1'?G。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第一部分】南非之魂:曼德拉传
第一章 好望之源
第一章 好望之源
我是一只鹰,在云端翱翔,
我极目张望,也看不见我家乡。
——南非茨瓦纳民歌《恩瓦托》
第一章 好望之源
一、乡村童年
在青山环绕的一片狭长的谷地之中,坐落着一个黑人村庄——库努村,清澈的河水绕村而过。村里只有几百人,住在被称为“让德威尔”的小房子里。房子是用泥和茅草建的,地板是用拍扁后的蚂蚁窝拼成的;唯一的出口是一扇矮矮的门,高个子必须躬着腰才能进去。姆巴谢河流过玉米田和种满金合欢树的农场,一望无际的草地一直向东流入印度洋。村里没有公路,有的只是赤足的男孩和女人们在草地上踩出的小路。女人和孩子们都披着染成褐色的毯子,只有几个信奉基督教的人才穿着西方化的衣服。土地本身归白人政府所有,非洲人没有土地,而是像佃户那样每年向政府交纳地租,只有很少几个部落例外。在这个地区有两所规模很小的小学,一间普通的商店,和一个可以让牲畜免生跳蚤和疾病的消毒池。玉米、高梁、豆角和南瓜是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吃不起更好食物。村里一些富有的人家可以偶尔吃些茶、咖啡和糖以做调剂,但是对于大多数库努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种田、做饭和洗衣服的用水必须用桶从河里运回来。头顶水桶行色匆匆的女人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实际上,库努是女人和孩子的村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男人在遥远的农场和瑞福山上的矿山工作,瑞福山在约翰内斯堡南郊,山中有含金的石头和页岩。他们每年大约回来两次,主要是为了耕地、锄草。播种和收割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事。村里的人绝大部分是文盲,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得近乎原始的地方,一个日后成为南非叱咤风云的黑人领袖的小婴儿安静地诞生了。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生于1918年7月18日。也许这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几个月后——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和平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这是否预示着,这个黑人的孩子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呢?
曼德拉出身的家庭属于滕布人中高贵的克拉尔家族,他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族长,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南非军队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方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班加”,是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协助比勒陀利亚政府处理地方事务。亨利·曼德拉共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一般称作诺赛卡妮)是一位很有性格、高贵的女人。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母亲负责三个“让德威尔”,那里总是挤满了亲戚们的孩子。依非洲的传统,叔叔或阿姨的子女被视为自己的兄妹,而不是堂兄妹。母亲的姐妹也是母亲;叔叔的儿子也是兄弟;兄弟的孩子也是子女。在曼德拉回忆中,库努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吃的一切都是自己生产的。女人们种植和收割玉米,收割以后,女人们用石头将玉米粒碾碎。一部分用来做面包,剩下的晒干后存在罐子里,玉米有时不够吃的,但牛奶和羊奶是充足的。
“母亲负责的三间小屋分别用于烧饭、睡觉和储存物品,纳尔逊兄妹们睡觉的小屋中没有西方人所说的家具。他们睡在草垫上或坐在地上,直到上学后纳尔逊才知道了枕头是什么。”曼德拉说,“从很小开始,我就与村里的男孩们一起在草原上玩耍、打闹,这用去了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待在家里、围在妈妈身边的男孩子会被视为女孩子气。晚上,我与这些男孩共享食物,同盖一条毯子。我开始放羊的时候不到五岁,我发现科萨人对畜群着迷似的喜爱,不仅把它们视为食物和财富,还把它们看成是上帝的赏赐,是幸福的源泉。我能用弹弓射下天上的小鸟,能采集野蜂蜜、水果以及可以食用的草根,能直接从牛乳头上喝到热乎乎的甜奶,能在清澈冰冷的溪水中游泳,还能用几股拧在一起的尖头铁丝捕鱼,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野地中学到的。我学会了非洲农村的每个男孩都掌握的棍战知识,并精通它的各种技巧:避开击打,声东击西,快速逃离对手。从那时起,我就爱上草原,爱上了这广阔的天地、质朴的自然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
除了用幼稚的眼睛开始领略大自然神奇的美之外,小曼德拉还和小伙伴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让自己开心。——无论多么穷困贫瘠的生活,也不能抹煞孩子们快乐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