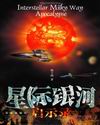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的怀中。你具有一个妈妈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生日快乐,亲爱的妈妈!我爱你!”
1974年间,由于政府指控她触犯禁令,温妮·曼德拉在克龙斯塔辛监狱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时光。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觉在那里自己更加解放,肉体上与自己的信仰一致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更令人满意。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于她家来说,她的囚禁令孩子们不安。津姬听到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哭,我哭豺狼笑”。泽妮回忆起学校星期天放假时,她和妹妹津姬在监护人哈瑞大叔(恩塔托·慕特拉纳博士)带领下看望母亲的情形:在半小时的会见时间里,她们隔着一块玻璃板和母亲谈论学校的事情,谈论她们的零花钱,以及她们和谁在一起玩。温妮总是看起来很好。孩子们发现朋友不敢去家里看她们了,因为安全警察会把他们带走去审问。
很长时间以后,曼德拉回想起他那时的感受:“尽管我总是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我从来没有习惯你坐牢。”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几乎没有事情能像这种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折磨似乎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辛度过的6个月中,我们所遭受的极度痛苦。”
温妮·曼德拉不断被捕、受到指控、被判刑、上诉、缓刑和不时的坐牢,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难以掌握。在她看来,长期的反抗揭露了南非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千千万万的男女成为牺牲品。在同警察发生冲突时,她无所畏惧,如果他们对她进行粗暴的侵扰,她就进攻式地进行反击。但是,对于一系列阴险的暗算,诸如对她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往她的房子里扔汽油弹,她毫无办法。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呼吁联合国敦促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袭击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埃莉诺·伯利把泽妮和津姬从修道院不愉快的生活中救了出来。埃莉诺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过去是伊顿公学的校长,现在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客座教育学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特,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得到政府允许,可以见她们的父亲。温妮理解她们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她们会不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崩溃呢?还是会因为这种经历而变得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呢?
从曼德拉的照片上泽妮看到他“非常高大,很胖”,但见面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对她触动最大的是她父亲是多么的幽默,如果当时或在后来的探视中他有过什么忧虑的话,他也掩饰得很好。
津姬也发现他幽默而热情,很让人安心。“事前,我很生气而且有点恐惧,”她对一个记者说,“我发现他很有办法,很有魅力。他设法使我不去想那里的环境,让我想起更舒适的环境。他说,你知道,我能想象在家里你坐在我腿上,全家人一起吃星期天烤肉。尽管不能看他站起来,因为她们被领进小屋时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了,但她后来设法看到他离开时的样子,他看上去那么健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轻捷。”
第二次探视父亲时,两个孩子是单独去的。开车把她们送到开普敦港码头的那位朋友,看着她们同一队身穿橄榄绿制服的狱吏们上了渡船。这种场面真令人伤心——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同那些唱着阿非利卡歌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问里,温妮和丈夫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从对方那里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各自的斗争环境中后,曼德拉以其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不分政治派系地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温妮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斗争。索韦托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黑人聚居区,那里的斗争正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在温妮看来,它“使人民更充分认识到自身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培育了人民的自立精神”。黑人变得为自己的黑色而自豪。
出人意料的是,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后没再延长。12年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77名被拘留的人,她还向人描述了她自己几年前所受的苦难,那都是因为《恐怖主义法》第6部分。她说,第6部分“打算彻底摧毁对南非极权政治的一切形式的反抗,它是一种以毁灭一切个性自由为目的的精神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方法,使那些敢于斗争的人丧失人性”。
“我们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在一次公众抗议大会上,温妮·曼德拉说,“我们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们不是在请求实现多数人统治,那是我们的权利,为了得到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几周内,包括温妮在内的许多成人、学生都被拘留,这一次是根据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国内安全条例》。他们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达5个月。
罗本岛的犯人们之间,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但仍然完全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及这些。可是,这时候曼德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园子里有一棵番茄,他不小心给碰伤了,现在正在特别地照料着。他描述了它是如何美丽,如何不停地生长,他又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去时,他怎样把它从土里拔出来,用水冲洗干净根部,回想起生命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明白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情形:父母把一切能给的东西全部给了他,把他抚育长大,然后他在少年时被杀害了——曼德拉的感受与那些家长在成百上千的儿童惨遭扫射时的感受一样。温妮解释说:“如果他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每天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回忆友谊和被捕之前发生的事情。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各自的来信中的新闻。有时他们哀悼逝去的朋友,有几个40年代以来的老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雪和莉莲·恩戈仲。费雪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刑第10年时,于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政府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回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因癌症去世,享年仅50岁多一点。在多年的监禁后,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见相左的索布克韦已经同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获释后,他住在金伯利,一直遭受软禁。
1977年5月16日清早,20多名警察来到温妮在索韦托的家中,命令她收捡一下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影响学生们。另外,她和曼德拉不知道,政府这次如此强暴、专横地把她从她唯一的家里赶出,离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预计访问索韦托只不到一周。
警察开车带着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了300英里,到达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上的布兰德福特村。警察把她们母女两人放在门牌号码为802的房子前,这是政府所能找到的温妮最不熟悉的环境了——这里是阿非利卡人政治、文化精髓所在,当地语言温妮她们一窍不通。
“福尔特雷克”大街被称为“干道”,它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这些设施包括教堂、两家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卖报纸杂志的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及一所阿非利卡语学校。一条弯弯曲的小路,路旁就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被人称作“帕特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在阿非利卡语中,“帕特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名记者说它特别适合于新搬来的人。那里,3000名黑人拥有的全部福利设施只是一家班图人商场和一个啤酒馆。
那三间水泥房子,温妮叫它们“我的平房”——没有天花板,没有水,没有电,屋外一个厕所是放便桶的。她的房子与所有周围的人都一样,除了住的地方外到处是瓦砾。警察让她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搬进那么窄小的门去,只好送回奥兰多。
她只能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禁止外出,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不允许会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人以上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位面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界的汽车里监视温妮,当她外出时就跟踪她。按照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他是“致力于扰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认为,把温妮流放到那样的环境——白人都对她充满敌意,黑人又没有文化——中去,即使她不会消失也应该屈服了,那么政府的如意算盘就打错了。这位经验丰富、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像沸水般闹开来。那些地方是黑人从不敢涉足的禁区。在一家“时装”店外面,黑人们在排着队等候,温妮和津姬不但进了那个“时装”店,而且试了服装,结果发生争吵,店方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举动表明他们本性是害怕的,过去阿非利卡人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队中把自己困在里面,现在也是这样,真是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曾受到警告,不得与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渐渐地他们鼓起了勇气,因为他们难以总是拒绝她的热情和慷慨。温妮眼见他们被剥削得一无所有——贫穷、饥饿而且卑躬屈膝——深感震惊,她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但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就把她带上布隆方丹法庭。原因很可笑: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去什么地方买煤;她在邻居那里时,有位男子带着一只刚买的鸡经过那里,温妮询问了鸡的价钱。检察官在起诉书中称以上行为构成了“三人集会”,因而违背了对她的禁令。他们还指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因为她穿着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驳斥道:“在留给我的可怜的自由权利中,我还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权利。”地方法官认为她有罪,判她缓期服刑。法庭外面,人们向她发出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用遭禁令的人发表的言论,但温妮对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讲出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简直是疯了。我是指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作为证据来用”,上诉后温妮无罪获释。
不久,她又重返法庭,被控接待访客。这期间,曼德拉曾写过一封信,说:“我会念着你,尤其是你站在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胡言乱语的时候,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深地知道,你所受的磨难是因为你热爱我和我们的大家庭,并忠诚于它。这种爱与忠诚在不断增加……”
政府为这些案件花费了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让温妮觉得可笑,而人们气量是如此狭窄,反应如此迟钝又使她惊讶不已。但这些事情对津姬的影响使她感到愤怒。普林斯卢在暗中监视她们,逮捕了从索韦托一起来看津姬的朋友,再加上布兰德福特生活压力大,生活水平很差,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厉害的时候,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去看精神病医生。在曼德拉向最高法庭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津姬才有了接见来客的权利。温妮不能提出这种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令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她正在向作家的目标迈进。他赞扬她说:“你已经收到了你的第一笔稿费。以你这样年轻的年龄来说,这是不小的成就。”他又忠告她说:“作家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他把人推上世界中心。为了保持在峰巅之上,你就必须真正地努力工作,目标是你的文章主题好而新颖,表达方式通俗易懂,词汇使用要准确。”
津姬曾写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真难以置信,你母亲几乎失去了全部家产。她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农场帮工,或替人洗衣服。她只能生活在贫困状态。她已经告诉我你们现在必须要住那种房子,以及你们不得不使用的那种厕所或自来水设备。……”
“尽管如此,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并且设法活得很快活。当我读到‘毕竟是个好地方’那句话时,我感觉好极了。只要你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能变不幸为有利,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假如不是这样,那你妈妈如今早该彻底毁灭了。”
津姬发现写诗是发泄的好办法,在沃特福德上学时她就擅长这个。她通常把写的诗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而她母亲却善于把这些诗拾出来。1978年她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有他们的老朋友彼得·马库拍的一些照片。津姬把这本诗集献给她的爸爸妈妈,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父亲的: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落了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家庭。
那树干,是我的父亲,
全部枝桠,都靠他支撑。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们,
是他珍爱所在。
他们该有多么美味,
多么可爱,
可都落在地上,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代表幸福,
被割断了联系。
在首次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津姬的诗集获得了1000美元奖金,该奖颁给那些描写作为无私与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政府拒绝给她发护照,经办人只好由马克巴内在纽约代她接受奖金。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一位波兰犹太人,他是小儿科医生,因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与孩子们一起死在纳粹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
曼德拉在1962年说:“南非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之斗争,其核心和基石在南非内部。”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越过边境渗透进来,真正的武装斗争开始了。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从索韦托到新布赖顿,到兰加的黑人城镇战火的洗礼,成长起来了。现在,他们跃跃欲试,准备自我牺牲。此举被人们认为是用以表明他们坚定的决心——要彻底推翻他们所称的“那种制度”。
在返回南非后不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