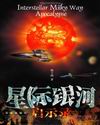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以表明他们坚定的决心——要彻底推翻他们所称的“那种制度”。
在返回南非后不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就遭逮捕,按照《恐怖主义法》而被拘禁的人中包括所罗门·马兰古。他从未开枪杀过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甚至牵连到他的那件谋杀案中的白人遗孀都呼吁、抗议南非政府此举,他仍然被绞死。另一名年方二十的新成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与曾在罗本岛上服过刑的一些老成员一道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监禁。他说为自己的理想作出牺牲,他心甘情愿,他丝毫不怀疑那些理想会成为现实。
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们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同警察和军队交战,他们把零星的信息拼凑在一起,知道斗争正向前发展。1977年间,有95件审判案是根据保安法令进行的,政府的指控包括补充军事训练所需人员,组织行动小组,私运武装、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活动或游击战争。
津姬出席了对索韦托“学生代表会议”的审判会,该组织被指控筹划了1976年6月暴动以来的抗议活动,那些抗议活动连绵不断。从此,她开始代表她那遭监禁的父亲和被流放的母亲。
此时,泽妮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查的儿子图姆布穆齐·德兰米尼王子结了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对曼德拉进行“接触式”探视,这将是他被囚禁以来第一次同自己的亲人进行正常的人类接触。1978年6月,泽妮同王子带着一岁大的孩子从姆巴巴内去了罗本岛。当他们一起进到探视室时,泽妮担心父亲会抑制不住感情。她向父亲跑去时,几乎把孩子扔了,幸亏她丈夫抓住了孩子。泽妮和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曼德拉抱过孩子。他们坐下说话时,泽妮发现父亲完全知道该干什么,尽管从她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从未抱过孩子。“他注意到什么时候该给孩子换尿布了,甚至知道让她打嗝,然后他和她玩,哄她入睡。”
曼德拉已经有了五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有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还有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他给泽妮的女儿取名“扎基韦”(“希望”的意思),两周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给她举行洗礼仪式。政府允许温妮从30英里外的布兰德福特前去,但中午以前必须返回。“扎基韦”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的密友,全家人都十分喜欢她。温妮提到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重她”,长期以来她成功地反抗了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的历史的真相”。教父与教母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禁令不允许。73岁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了两周的牢,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她去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1978年7月,曼德拉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举行活动进行庆祝。《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很可能将来会领导一个黑人南非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能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日贺卡,所有卡片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802号。全家人团聚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的探视,你给我的信和爱,许多年前我就崩溃了。”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她,每天早晨他都小心翼翼地拂去她的相片上的灰尘。现在他接着说:“我在这里停下来,喝点咖啡,然后我掸去书架上相片的灰尘。我从最外面泽妮的相片开始,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三、劳燕分飞
“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刚刚遭受的痛苦经历。”
1992年4月13日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曼德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一天他宣布与妻子温妮分居。对曼德拉一家来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对全体黑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刻。两位南非最著名的人物间的婚姻终于破裂了。当初,奥利弗·坦博的妻子阿蒂莱蒂于1957年把曼德拉介绍给温妮。现在坦博以及曼德拉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西苏鲁都支持他做出这一决定。曼德拉的声音极少有颤抖的时候,但那一天,当他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时,他的声音的确在颤抖。约翰内斯堡各电视台纷纷出动,他们记录了这一期盼已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大家早知会有这么一天,但一年多来它一直蒙着面纱。
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她对事业的执着令我对她更加敬佩,更加爱她,我对她的爱与日俱增,”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关系变得“紧张”。曼德拉并没有详细解释,但在场的每位记者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突然,曼德拉从桌子旁站了起来,说出开头那句话,然后步出大厅,新闻发布会就在这种尴尬而沉寂的气氛中结束了。没有人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于涉嫌绑架四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尽管如此,她也承认这些指控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陷于一种“尴尬境地”。
对于他们分居这件事,很少有人同情诺姆扎莫·扎基韦·温妮弗来德·曼德拉。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纳尔逊流下泪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压倒多数的人以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落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而正是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在他刚刚获释时甚至把她作为偶像。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比家庭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1992年10月下旬,在参加女儿津姬的婚礼时他对宾客们说,著名的自由主义战士似乎注定要亲眼看着家庭生活“完全陷入动荡”。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如此。
曼德拉和温妮于1958年月6结婚,那时他正接受第一次判国罪审判。自那以后,他们两个除了作为斗争的神话和象征外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1961年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工作,1962年间被捕坐牢,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因此,在他们俩34年的正式婚姻中,他和温妮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4年,其中两年是在他被监禁前,两年是在他出狱后。这是以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战场、作背景的婚姻,而他终于成为这场斗争的另一牺牲者。如果不是温妮,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泽妮和津姬,她俩也是一样。在津姬的婚礼上,他仔细思考了令人心酸的家庭生活,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我们眼看着孩子们在没有自己的指导下成长,而当我出狱时,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会回家。我们的父亲回来了,但令我们沮丧的是,他天天离开我们,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之父。”曼德拉说他常常考虑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代价,但最后他总是得出结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应做出的正确决择。”
1991年春季和夏季,曼德拉的权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他的妻子在政治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他失去了对非国大的控制。在这一对“孪生兄弟”问题面前,他显得形单影只。只有对事业、使命的信念支撑他挺了过来。德克勒克已经让他大为失望,与南非白人领导建立一种密切、特殊的关系的希望被粉碎了。现在又轮到他妻子和非国大,他们也滑离了他的控制。
重获自由的曼德拉面临各种挑战,但没有哪种挑战比对付自己妻子的挑战更令人劳神费力。温妮不仅是纳尔逊感情上唯一致命的弱点,而且她已经成为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逐渐失去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如何处理温妮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就像曼德拉释放前在民主联合阵线内部一样。它把曼德拉推向另一种领袖能力的考验,对这种考验他反应迟钝,因为长期把温妮一个人留在家里应付各种危险使他对温妮负有很强的内疚感,这一感觉使他看不到真相。最后,只有纳尔逊能够解决温妮给他和非国大制造的这一“两难问题”,但是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温妮的阴暗面并最终把自己从负疚感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温妮毫不留情地利用他的负疚感来复活她自己的事业,给他和非国大在政治上造成极大损害。曼德拉不知不觉卷入温妮的阴谋中,她想把自己变成南非的女皇。他甚至对她的性丑闻保持谨慎的沉默,而此时全国人民都在谈论她。直到温妮毫无节制的不良品行令他都难以忍受时,他才屈服于狂怒的非国大官员施加的压力,这些官员担心她正在使整个非国大领导层陷于崩溃边缘,而且她正在毁掉“妇女联盟”。
从曼德拉出狱的那天起,他的婚姻的命运就成为全国人民谈论、猜测的话题。1990年2月15日,《约翰内斯堡星报》采访了几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们预言曼德拉前面的路还很崎岖。曼德拉与温妮共享的时光太短暂了,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夫妇两人分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发现自己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温妮的爱是那种“尊重型的,而不是激情型或渴望型的”,她这种感情与一个虔诚的教徒对“圣人殉道者”的那种感情类似,这是心理学家大卫·刘易斯的观点。大卫还预计,温妮的国际声望会被曼德拉更高的声望所遮蔽,她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退到一旁做配角,而这对她来说感情上要经历剧烈调整来适应。时间证明这些预测是对的。温妮对这种“调整”或其他调整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随着她的所做所为越来越偏离正轨,非国大和黑人民众普遍认为她应该为曼德拉的婚姻破裂而受责,尽管对任何女人来说,与一个同样是人的神话般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温妮并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差得太远了。即使在曼德拉释放之后,她仍把自己看成是政治上高不可及的人物,不仅凌驾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法律之上,而且凌驾于自己所在组织的纪律和规章之上。因此,在他们分居前我们一直看到这种丑恶的景象——她操纵、利用纳尔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给纳尔逊造成了巨大的感情痛苦,也在政治上破坏了非国大的形象。她对权力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她甚至把曼德拉作为她的计划中的人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她更谨慎地实施她的计谋,不那么露骨而无耻,她很可能会得到她想要的一切。温妮拥有成为黑人统治的南非的第一位“第一夫人”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位置将确立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曼德拉死后,如能利用公众爆发出的对她的同情这股力量,她甚至有可能成为总统,但她毁了这一切。
温妮控制不了自己的邪恶的冲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性问题上她都要得到立即满足。她在城镇里的崇拜者称她做起事来就像一头母象。但她更像一头离开母牛的小牛,决心用犄角撞翻挡住去路的任何障碍物。她对权力、地位、在非国大的特权胃口大得惊人,如使自己当选为六个委员会的委员。总的看来,温妮已经形成了一种分离的个性。有时她慷慨大方、彬彬有礼,对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关怀备至,她常常是第一个——有时是唯一地——奔赴现场的非国大官员,抚慰那些在最近的事件中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人。她个性中阴暗的一面是脾气极坏,毫无征兆地为一点小事对朋友和敌人大发雷霆。她可能会向所有人发脾气,没有人能幸免。她甚至打过非国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坦博·姆贝基一个耳光,因为他藐视她。1991年早些时候对她的审判显露出她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顽固,而且显然是津津有味地沉浸在非法的在城镇谋财害命当中。大量证据表明她同意,甚至可能是命令谋杀了不计其数的真实和假想的敌人、对手。在她周围聚集起一帮城镇暴徒、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和拍马屁的人,而那些品行良好,打算帮助她的人通常会发现自己“近墨者黑”了。
对温妮的不良品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精神分袭症、酗酒、长期遭受迫害或夸大妄想症。国外新闻界已经把她塑造成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化身,在全世界树立起她殉道者的形象。当这些媒介越来越多地报道她在城镇里的所作所为时,她又毁掉了自己塑造的圣人形象。在媒体面前荣耀丧失殆尽会不会对温妮的精神产生影响呢?我相信类似的经历影响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在他1981年10日被伊斯兰狂热分子暗杀前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