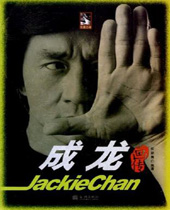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丰庭的家,到处寻衅复仇。母亲怕这种仇杀株连扩大,便到“青云堂”带上两个孩子,头上包一笼帕子,挎个提篮放些糖果,装成一般老百姓,混过刘的岗哨,到南塔梁子后面林伯琴家藏身。林为人仗义,平时与陈红苕无任何私怨,他把怕受牵连的李丰庭家的同宗,也都藏在家里,白天照常上街与那批复仇者周旋。
一个多星期后,郑慕周拖起一、二十人到罗兴场住了一阵子,又托秀水的大爷向浑写信向何鼎臣救援。何与陈过去不和。何从绵阳开来队伍,又从西南乡秀水、桑枣等场上招来袍哥,共一千多人攻入县城,赶跑了刘世荣。
那天,何天王亲自在南河“滚钱坡”附近的一座油坊里指挥攻打。这里离林伯琴家很近,杨朝熙特意跑去观看。何鼎臣长得魁伟异常,只是已入老境,风采不如青年时代了。何得胜后,朝熙一家就又搬回城里。这次事件使得他的书更读不下去了。母亲担扰对方复仇,对于他跟着郑慕周也就不加阻挡。他开始了到处跑码头的近两年的“跑滩”生活。所谓“跑滩”,主要是跟着舅父在桑枣、秀水、何家沟一带游荡。有的时候,一天挪一个宿处。回城住些日子便又溜到乡下。很多次,城里一有动静,母亲半夜叫他摸出城去传递消息,好让舅舅紧急转移。不久,张凤梧旅长带兵进驻安县。张的侄子张绍武,借住在朝熙家,进出乘红豆木杆杆的轿子,生活比一个副官阔绰。原来他暗地在做军火生意。有一天,张妻主动问母亲,有没有人要买枪支的?郑慕周既要防刘世荣一伙报仇,防官府的追捕,也要防被驻军吃掉,几十人的队伍正急需枪支配备,便通过张绍武的妻子,出高价买过好几次武器。这送枪给舅父的任务,便落到少年杨朝熙身上。
总是母亲给他准备好个篾篼,把手枪放在最底下,蒙上帕子,上放挂面、猪肉、糖,象是一宗礼物。只要大着胆子骗过城门的卫兵,就能平安送到乡下舅舅手里。朝熙从小与他哥哥不同,他胖胖的(“我只有小孩时胖过,成人后就变节排骨了”①),见生人脸不红,说话从容,调皮,敢闯,非常喜欢经历这种冒险生活。他给舅父送枪支、送消息。那时舅父住在下河坝那边,挨近何家沟,一个很背静的院子里。有时遇到郑已不在,去了石梯子、萧家堰等地,他也就跟着去找。
张绍武与郑的枪支生意越做越熟。张看他舅父精明能干,将女儿拜寄给他认做干爸,并送给郑一匹坐骑。有了枪,有了马,郑的情况便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朝熙便敢学骑,很快能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所以,后来他在解放区行军骑马,比何其芳骑得好,就是因为从小训练的。这种生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他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坐茶馆,看杀人,旁观舅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地方封建性割据的黑暗,社会上人与人搏斗的情景。他不知不觉成人一样进入社会生活,虽然不能全部懂得,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备。他人小阻大(当了文人后胆小起来),连绵竹、什邡各处有名的袍哥头目都知道。
他们见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叫他“杨二”。(你由分家看到家业衰败,由母亲和舅父,看到“中兴”。这“中兴”癒不靠辛勤劳动,而是靠传奇般的闯荡,靠掌握实力。权势社会的变动内幕及其种种病态,很早就坦露在你面前)1918年,郑慕周招募了“垦殖军”残兵一百多人,便想正规地成军。他派黎少农去金堂拜见吕超,吕超委郑做预备营长。郑让位给谢象仪,自己做了连长,属何鼎臣十八团部下,驻中江县。从此,“杨二”结束了跟随舅父流动的生活。
操袍哥?从军?
杨朝熙回到家里继续读书,情况却同过去有了变化。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在这之前,他经历了母亲那场哭诉,说她如何苦,拖起他们读书不容易,而他们只会顽皮、睡懒觉。他原来从不惧怕母亲,这时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羞惭之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因为他已到了稍稍更事的年龄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朦胧到开始懂得考虑自身、审视自己的时刻,只是结局不同罢了。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如果不是舅父的思想改变,杨朝熙这些袍哥子弟的第一个前途本应就是操袍哥。但是川西北的军阀们,尽管自己一个个是袍哥、土匪出身,偏偏特别地看重读书人。在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崇拜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怪。这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郑慕周有了队伍,马上表示不准他的弟男子侄加入袍哥。连朋友的子弟也劝阻。他与吕超的侄儿拜把,吕某也是连长,这个人读过书,对郑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帮助青年人出外求学,举办各种文化事业,都很舍得花钱。
1919年,何鼎臣病故,谢象仪升任十八团团长,郑慕周为第三营营长,驻茂县。舅父要求朝熙好好读书。他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游的修金很贵,一年需一百银元,还要供给全部的食宿。他的脾气大,架子大,教书很严,朝熙吃了他不少戒尺,母亲也帮不上忙。但教了一年便走了。
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教他们两兄弟。谢是朝熙二婶母的兄弟,论起来应当叫舅舅,是个秀才。他在城关一个“师范讲习班”教国文,他们兄弟俩白天去讲习班所在的南门自治局寄读,晚上回家再读。谢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他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
(在我十六、七岁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进茶馆跟袍哥大爷混,读书相当用功了。天明即起,晚上读到深夜。读《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癒开始与本县高小学生或在成都、中坝(江油)上学的中学生接触。哥哥这时结了婚。——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十七岁那年,安县城关一批知识分子,这之中有小学教员,做文牍工作的,小学卒业后经商的,约二、三十人,成立了一个“会文社”。发起人是李心泉。大家合伙开了个文具店,朝熙跟哥哥都入了股。本来相邀每年春节时聚餐,但只举行了一次便散了。这是他最初的社会活动。
除了谢、刘两家的学友子弟外,其他塾外的朋友与他过从较密的是陈克玺(宝章)、杨承祺(寇斌)。这两人加上谢荣华(兆华),曾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与朝熙换了帖,结拜为兄弟。
陈、杨两位读书好,有学问,也能写字。他是因为学字才认识他们的。曾有一个时候,他受本县前清知县武生辉和蒋品珊老师的影响,一心学习黄庭坚字,到处求教。他认识陈、杨以后,才知道读《史记》。就象他在青云堂避难时才读到《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捩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沙汀传……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盐道街省一师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人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①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卑视的和诽笑的眼光。②(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在皇城内。宣统二年(1909)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1919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换成新式楼房。①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1921年的省一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