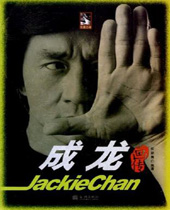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①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诨名“萧神仙”,因他喜爱撇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①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沙汀传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级友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没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称他为“播种者”。
张君培的脸似乎永远没有洗净过。牙齿洁白,鼻子和眼眶周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麻子。穿了不合身的又旧又破的斜纹制服,蓝布袜子和火麻草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张的独往独来、爱好争嘴、直言批评旁人的性格。他经常发出朝熙听来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怪论。
“你们只觉得娼妓很无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浮上一个挑衅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训的紧接着说,“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①
他还说分娩是“某一器官的天然责任”,虽然没有亲眼看过生孩子,“可是哥白尼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我们能说没有亲眼看过,就不相信它吗?!……”②为了找一个同学温习自己几乎要得零分的英语,杨朝熙鼓起勇气向这个班里英语学得最好的同学请教。张君培认真地教其识字,解释文句,领着他读。但是自尊心使他隐瞒了自己真正的英文程度,教过三次仍不能懂得,于是遭到张君培的率直批评。朝熙对他是又想接近,又怕接近,两人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程度。
这天,乘着礼拜日别的同学去少城公园喝茶,张君培去高等师范看老师,杨朝熙溜进自修室,偷看了张的一个抄本,发现里面摘录了《学灯》、《觉悟》和一些流行小册子里的文字,懂得了张那些新奇谈吐的来源。他热切地读下去:人生观是甚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呢?越读不懂,求知的欲望越强烈。最后索性将这个抄本偷出,想拿回寝室细细地看一遍。事也凑巧,他拿着窃物穿过天井,正跨上那条联接几间教室的甬道,却意外地撞见了张君培。张见他忸怩的样子,先发了话。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大约我那天把你得罪了吧?”“哪里呵,”我说,更为混乱的把头勾下。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想要侮辱你呢!”他接着说;并且两手插入制裤的岔包,两足微微张开,有如讲演一般的说下去了,“我这个人么,你不来找我算了,既然找到了我,我是决不肯敷衍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怕缺了席扣分数才来的,我也不是想拿点钟点费,只求混过完事!……”①
张君培打着“为什么呢”的口头禅,接着嘲笑起班上混事的同学。朝熙为他们的国文根底辩白了几句,却遭到了“这些破铜烂铁再多装些,又有什么用”,只能“当秘书,拟通电,说些自己并不真心要说,别人也不真心要听的假话”的批评。凝想了一会儿,张接连向朝熙问起新文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的名字,可他却连一个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的呵!”他突异着,又叹息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告诉了他,忽然间兴奋极了。
“这个县名,你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我接着说,“四面是山,风气蔽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上一年还在读私馆呢。从七八岁起,我母亲每一年就拖钱借债,都要接个老先生教我的,但她自己从未受过教育!……”
……“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悲愤的结束着;“又聋又瞎,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就好办了。”他忽然同情的说。
他挨近我,在我肩上放上一只抚慰的手掌。
“我从前又懂得甚么呢?”他继续说,竭力想瞅牢我,“我小时候才读过四五年书!你没有听到说吧,我原先是在高等师范当小工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求学呢。我起初只希望有事情做,不会饿死就万幸了。像我都能够奋斗出来,在你们更容易啦!……”①当朝熙无意中暴露出他私自拿了这个抄本,原以为会使他们刚刚建立的关系破裂时,张君培却非常高兴。以上便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幕。对于他,张君培的思想放出异彩,照耀了他,这实际就是“五四”的魅力。而张君培却显出一个寻找自己思想伙伴的成熟态度。
以后杨朝熙才知道,张君培是涪陵人,家境贫寒,流浪到成都,在高等师范当过校工。因此,认得了比张秀熟还高一班的刘砚僧先生。刘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很赏识张君培,有意培植他。接着,高师学监王右木先生又来帮助他进夜校学习,成绩斐然。这样,张终于考入了省一师。
王右木是四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者,江油人,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等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在高师任教,指导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进而1921年在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右木生活简朴,经常吃几个锅魁当一顿饭,把大部分薪金都拿来资助贫苦学生,或者印刷革命宣传品,以至于夫人在家连菜金都发生了危机。这个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开会,经过贵州时不幸失踪的,估计是牺牲了。
张君培每次与杨朝熙谈起王右木的道德文章,总自然流露出敬意。他经常到王右木那里借书看,都是一些谈妇女、劳工、社会制度问题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朝熙又看张借来的一些铅印、油印、手抄的禁书、刊物,两人互相切磋讨论。通过这些,朝熙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动。“五四”给予他的影响虽然迟了两年,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整个换了脑筋。他开始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以后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一生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