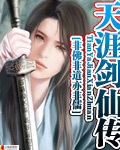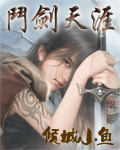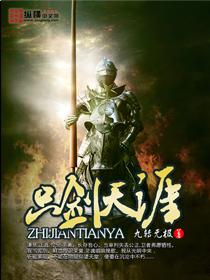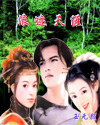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读北大,大概是一九三三、三四年前后吧,」张先生仰起头,勉力想了想,「我总是记不清年代、时间和地点,但查一查就清楚了。沈先生性格乐观,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张先生又是那样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路远,我过去看他,有时候就在他那里吃午饭。其实在他们家,给我管饭,也负责招呼里外的,是一位姓金的女士,叫金南萱,我们叫她金小姐。」
一九四○年代张充和昆曲扮相
沈尹默在重庆时以小案桌写字的场景,是张充和常常提起的。
「她是沈先生的什么人?」
「她是沈先生第二任太太褚保权的好友。呵,这位金小姐,可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哩,」张先生的笑容里隐隐带着一种调皮,「金小姐是学艺术的,在北平学画、教书,好像是买航空奖券中了五万块的大奖,就不教书了,回到江苏水乡。那时候,驻守江阴炮台的一位将军看上了她,张罗着要大办婚事,派出轮船接她去结婚。那时候,正是七七事变之后,和日本人的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江阴炮台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人报告了老蒋(蒋介石),结果接金女士的轮船还没上岸,那将军就被老蒋下令给枪毙了。她从船上走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寡妇。夫家一家人自然都不喜欢她。她竟然就在那个其实没有真正成亲的『婆家』里守了几年寡。她再也受不了啦,就是这样,投奔的沈先生。那时候,沈先生正在与他的第二任太太褚保权谈恋爱,金小姐是褚保权的好友,沈先生愿意收留她,就一起跟过来了。」
我很好奇:「那位金女士漂亮么?」
「挺漂亮的。她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风度很好的,」 张先生脸上现出一种殊异的神情,「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女士还有一位姐姐或者妹妹,跟一位好像是建设厅的厅长好上了。那位厅长已有妻室,厅长太太就到蒋夫人那里去告状。那是战时,老蒋一生气,又把那厅长给毙了——两姐妹的男人,竟然都被老蒋毙了!据说到了重庆,两姐妹还不能见面。那是金女士亲口告诉我的故事,听得我呀,头皮都麻了!」
「那位金女士,后来再婚了么?」
「她后来跟重庆政府里一位官员结了婚,但还是住回到歌乐山来,帮沈先生管家。她照料沈先生的生活起居,非常仔细体贴。沈先生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纯吃素。战时吃肉本来就难,怕他营养不够,她就把肉丝打碎了,做成肉汤。沈先生眼睛不好,不知那是猪肉,喝那肉汤,倒是很喜欢的。」
我笑道:「这又是关于沈尹默的掌故中,另一个善意的『骗人』故事。」
张充和也笑起来:「说起来,我跟金南萱还有同床之雅呢。那一年——大概是一九四一年,四川一位杨姓乡绅请沈先生、金女士、乔大壮和我一起,到他们在歌乐山以外的一个叫杨家花园的山庄去住两天,一起吟诗、写字、作画。那两天,我和金南萱同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她就跟我细讲了她的身世来历。那个未成媳妇就先成寡妇的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听得我真不好受。」
「这位金女士,后来还一直跟着沈先生么?」
「沈先生一直善待金南萱。在重庆时候,金南萱开过画展,沈先生还帮忙为她操持,写诗题字的,很尽心。我记得金南萱的先生姓张,婚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抗战胜利以后,我结婚、出国,就和金南萱断了联系了……」
窗外,夏日的长街有车声远去,一若时光消逝的远影。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记于康州衮雪庐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张寰和提供)
绿腰长袖舞婆娑
张充和与沈传芷及昆曲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三)
和充和老人聊天,常常都是从茶几上的书本引出即兴话题。
那天去看她,小几上摆着一摞跟昆曲有关的书。有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报导结集,还有一本由俞振飞题名,名为《姹紫嫣红:昆事图录》。翻到其中「张家四杰」一节,正收录了他们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与昆曲结缘的故事,还有姐妹们各自在昆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照(据张先生说:三姐兆和其实没有唱过昆曲,戏倒是懂得很多,只是各种谈昆曲的书里都爱这么写——「张家四杰」)。看着那些蛾眉淡妆、婀娜多姿的身段姿容,陈年的黑白图片上似袅起一缕缕兰菊的馨香,我便和张先生谈起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东西——昆曲。
张先生喝一口淡茶,慢慢说道:「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家中女孩子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我笑了:「又是一个『沈』——张先生你注意过么?你生命中有好几位『沈先生』,都跟你最重要的经历有关。」
张先生眼睛一亮:「哎哟,真的哟,他们都是姓沈哟!」
「哎哟,又有鬼哟!」我几乎忍不住就要学着她的口气,可是我把话咽住了。
她微笑着又沉入了回忆之中:「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我问:「那时候昆曲的演出,很兴盛么?」
「其实也不。那年月,上海舞台上唱昆曲的,只有传字辈的一个班,在『大世界』演出。战前那几年,就开始不太有戏唱了。苏州离上海近,我父亲就请他们过来教曲。沈老师先在苏州教,后来又到青岛去教。我有两个暑假就专门跑到青岛去,跟沈老师学戏。先学唱,再学表演。一个戏要学好几个礼拜呢。那时青岛唱昆曲的人很多,第一年我跟我弟弟张宗和一起去,他也学戏,住在太平路海边一座别墅里。第二年跟青岛的曲友熟了,就住在一个孙姓朋友家里。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沈传芷(1906—1994)
张充和试妆
抗战前张充和小生戏装
我说:「我记得从哪一篇文章里读过——有一段时间,你夜夜坐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
她笑笑:「是孙康宜的文章吧?有意思的是,战前那几年,我常在拙政园那条船上唱戏,战后呢,我又回到拙政园,却是在那里教书——那时候的『社会教育学院』设在那里,我是代我弟弟宗和的课,在那里教书。」
话说到这里,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像是一个越洋长途,张先生拿着话筒和手里的纸张,眯眼辨识,向对方娓娓细道。原来,这是另一位「沈先生」——沈尹默先生的儿子,越洋打来的电话,请张充和帮助读校刻在古棺上的一段沈尹默墨迹的拓片。拓片的复制件,显然是从计算机网络里传来的,我接过来,和张先生一起辨认:
《题王晖棺玄武像》
沈尹默
昔闻巨蛇能吞象,今见蛇尾缠灵龟;
四目炯炯还相像,思饮怨□孰得□。
物非其类却相从,蛇定是雌龟是雄;
相与相违世间事,悠悠措置信天公。
沫若老兄嘱题
张先生帮着辨识出了好几个漫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是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 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
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褚保权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是她的侄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后来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地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抗战前张充和在苏州狮子林留影(张寰和提供)
张充和的昆曲扮相(由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的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了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乐益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太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是么?」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员。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绍裘,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四九年后,我继母在苏州的博物馆做事,听说她一直很受当地政府的尊重。我的小舅也是地下共产党,一直在学校里教书。那年我见到日后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父亲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散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一九四一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左)王泊生在京剧《宝莲灯》中的扮相 (右)俞振飞与程砚秋合演《春闺梦》剧照
「你跟俞振飞配戏,是哪一年?」
「那大概是一九四五、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的事了,在上海,很大的一场演出,唱《断桥》,他唱许仙,我唱白娘子,我大姐唱青蛇。」
我提出要求:「再讲一点跟昆曲有关的好玩事儿。」
她朗声笑道:「嗨,好玩的事儿多啦!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省立剧院院长,当时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江,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冀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不然这戏,可真就唱不下去啦,呵呵呵……」
张先生轻声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蹒跚着脚步——老人家腿脚已经不算太灵便,走到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一个由蓝灰印花手帕包裹着的小本,慢慢向我展开——
(左)陈礼江(1896—1984) (右)卢冀野(1905—1951)
「这个小本子哪,抗战那些年一直跟着我,跟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叫《曲人鸿爪》的咖啡色硬皮小册页,翻开来,巴掌大的尺幅,内里却乾坤浩荡——原来,这是各方名家曲友当年为张充和留下的诗词书法题咏和山水、花鸟的水墨小品,简直可以用「精美绝伦」名之!
张先生翻到其中一页,「喏,这就是卢冀野——卢前,当时即兴写下的诗句——」
鲍老参军发浩歌,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吾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